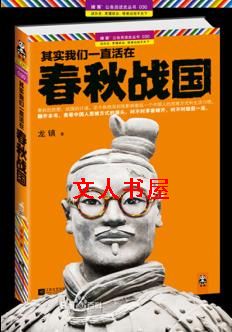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5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张了几张嘴,刚要把什么说出口,狄阿鸟又补充说:“我知道。”
狄阿鸟环顾了一周,两只眼盈亮,确偏偏只有一道缝,几乎所有的人都打内心中身边:“和我没有关系。”然而,这时他又以陈元龙那种官员才有的无须置疑的口气说:“交给官府,官府?!”
他问到官府,自然得有人代表官府。
陈元龙一伸手,又要说话,但是他没停,自己有给一个结论说:“没用。”只感到自己无话可说,憋得格外难受,同时还带有一丝心虚,暗道:“难道他都知道了?!”一咬牙,硬生生往外挤一句:“你要相信官府。”安县长走出来,“啊哈哈”几个冷笑,阴阳怪气地说:“是呀。狄小相公,你怎么不相信官府呢?!官府干什么吃的?!我干什么吃的?!监狱受人投毒,会查出来的,穆二虎怎么造反的,也会查出来的,为什么邓家老往外抬死人,也是要查出来的,怎么,你们都不信么?!邓校尉呢,邓校尉呢。”
“安县长?!”邓家的人觉得他话味不对,给了他一声警醒。
安县长这就玩味说:“怎么?!你们不信?!你们当让不信,我却相信,要不是下官尸位素餐,早查出来啦。”他平伸了前脚,看似要迈出四平八稳地一小步,却同时抻抻袖口,继而,放下那只抬起来的脚,将两只手伸往头顶,一点、一点把纱帽取了下来,弯腰放在雪地上,直起腰,扭开袍扣,把袍子脱了,上下整饰,叠了一叠,再晚下腰,放到帽子底下,笑着说:“该滚蛋咯。”
至今为止,邓校尉还没出来,他人呢?!他的不出现,有点不同寻常,狄阿鸟猛地扭了一回头,两眼陡射寒光,往邓莺旁边看了一眼,旋即弯下腰去,旁若无人地托起妻子的头,轻轻用手,轻轻把污垢抹去。
这一刻,他把周围的人都忘掉,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来赴宴之前自己还搂在怀里的柔软身体;此刻;身体变得僵硬无比,已经开始冰凉,肌肤因坠地淤积的大片紫血,触目惊心,掰也掰不开的手指中握着一把匕首,就那样在脖子上扎了个洞,就像有时固执起来,一定要用细伶的拳头捶自己一下一样;伤口里头流出的血液结成一片凝血,凸起的地方有板筋那么大,延伸到缭绕的头发上,把头发粘住了,竟然给粘住了;脸上更是青紫狰狞,钉着两行带血的鼻涕,赴宴前敷上的胭脂和薄粉被汗冲洗,五颜六色,她以前,可是最温柔不过的人了,连个凶恶的表情都没有做过,此刻却是如此凶狠与丑陋;两只失神的眼睛还在往上看着,盯着自己,盯着自己,好像她只是做了个噩梦,只是被吓到了,好像她一翻个身,就能爬起来,要把好些、好些的话说给自己说,一时情不自禁,眼泪鼻涕就要一起往下掉,吼吼往腹腔里吸一吸这些液体,要张嘴说句什么,却又感觉着这些液体想从嘴里出来。
他忍着,忍着,脸上的肌肉却越发不受控制,撕裂了一般疼痛,不停往四处抽抽,还是“荷荷”地哭了出来,说:“你怎么就这样去了,让我怎么给你的哥哥交待,他刚刚把你交给我,一眨眼,你就不在了。”
他在心底痛苦地大喊:“他不就是垂涎你的美色么?!你为什么这么傻呢,为什么自尽呢,你和他睡一觉,我也不会嫌弃的呀,你的人还在呀,你的人还在呀,可现在;却断气多时,灵魂都飘散了。”
他迅速地惊醒,强行掐断自己的哭泣,最后干嚎几下,取下帽子,拔出腰间的短刀,揪住一把辫子,割了下来,放在妻子的鼻子下面,呼喊两声,终不见那一声叹息,只好别在她的衣衫上。
旁边出来哭声,狄阿鸟扭头看一看,是路勃勃在哭,就搂一搂他的肩膀,站起来,往四周看一看,找到那件虎皮大氅,一步一步走过去,在众人的退却中,把大氅拿到,打净雪末,回来遮盖到妻子身上,弯腰将她抱起来,感觉到她好轻好轻,好像一丢手,就要飞了一样,便用力地搂着,挨近自己的脸颊。
史千斤一晃一晃来帮忙,和陈绍武一样无忙可帮,因为觉得要做点什么,就捋了袖子破口大骂,把邓北关的娘往死里蹂躏。他也不知道人家的恩怨,也不知道自己骂的对不对,干脆逮上安勤的乌纱帽,发泄式抵补上一脚,看它射到高空。
陈元龙鼻子生烟,扭头正问这人是谁,狄阿鸟回过头,看着他说:“叔父大人,失陪了。”说完,搂着妻子,往远处走去。
陈元龙知道他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嘴角勾了一勾。
第一卷 雪满刀弓 一百一十二节
在邓艾的陪同之下,陈元龙带着陈敬业,退入到内宅中去休息。他不是真的酒困力乏,也不是贪恋邓家高规格的额外款待,而是知道一个兵户造了反,邓北关搜捕反贼同党,很快会名正言顺地逮捕狄阿鸟,自己不回驿馆,是为了向邓北关的行动让步,脱身出来。一路上,外头多出许多的仆人,四处走动,像在寻找什么,使他的脸色很难看。到了栖息地,他给卫士、幕僚一挥手,带着儿子进去,把门掩了。
屋中只剩二人,陈敬业便毫无忌讳地说:“想不到呀,他妻子为别人殉情,他还难过成那样儿。”
陈元龙找到一张阔背椅子,按在扶手上坐下,轻轻呵责说:“你知道什么?!你以为他妻子真的不贞,为别人而死?!我的儿子呀,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看一看外面,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吗?!这一家人好像是在找什么,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在消弭证据,你要记住,姓邓的不是什么善类,狠着呐,狠得让我想不到,背着我就下手了,真他娘的可恶!”
陈敬业小声说:“昨晚,你不都答应他了吗?!难道您变卦了,不想让他们要博格阿巴特的性命?!”
他压低声音说:“我答应他什么?!我从没想过要博格阿巴特的命,只不过是想让博格阿巴特把‘千里眼’主动献给我,带着他的人投靠我,我那时再出面救他,反手清理他的仇家,那时,他不但给了我想要而张不开口的东西,还会感恩戴德。你要记住,我和阿鸟的父亲同袍同泽,而与他们,不过一些金钱交易,身在朝廷,少不了自己人,倘若收了一些金钱,就什么亲戚朋友都不顾忌,就没法在朝廷立足?!
“何况,陛下也宠幸着他呀,曾毫不讳言地说,孤一见他,就喜欢上他,想收他为义子,可他不肯。”
陈敬业大吃一惊,问:“陛下曾说过这样的话?!”
陈元龙说:“你们都不要忘了,陛下和皇后所生的女儿在战场上被博格阿巴特俘虏的时候,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说他与公主有了肌肤之亲,所以才肯投降。流言可畏呀,陛下要收他为养子,是戳穿流言的一个办法,而后,他却不肯,陛下也没有杀他,内情不就值得玩味了吗?!据有人讲,皇后想把女儿嫁给他,几次与陛下提起,要把他召到宫里见上一见,可他闪电般成了亲,一娶就是四房,毁了皇后的脸,皇后一生气,要杀了他,陛下便着人把他给流放了,这话,会是空穴来风吗?!陛下的女儿岂能嫁人做小?!流放他,会不会是先逼他一个妻离子散,再把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呢?!”
陈敬业嫉妒地说:“这也太便宜了他,陛下究竟怎么想的?!”
陈元龙笑了笑,说:“究竟怎么想的?!这样的事,往朝也是有先例的。”他娓娓地说:“安德公主,也就是当今陛下的九姑姑,也是亲姑姑,自第一任丈夫喝酒暴毙,生活过得很孤苦,先王就有意成全她,上朝时带上她,让她隔着帘子,选自己中意的朝臣。安德公主选中了文学殿祭酒宋祁,给先王说,就是他。先王当天散一朝,就找去宋祁谈话。宋祁已经有了妻子,夫妻很般配,也很恩爱,委婉拒绝了先王,几天之后,他就犯了君前失仪之罪,被流放到南疆去了,还没有到流放地,妻子病死在半路上。先王就跟人说,这是天意,把他召回来吧。于是就召了宋祁回去,给宋祁说,你娶了安德公主,就是我的妹夫,我们都是一家人,自然没有什么失仪不失仪的。宋祁不堪流放,无奈答应。陛下追赐了他先夫人的名号,一个夺情,放他儿子一个外任的缺,免了丧孝,促成他们尽快完婚。这就是天子家的家事,没什么办不到的。这一次赶赴上任,临行之前,陛下还召见我,托我说,你和博格阿巴特的父亲,关系不错吧,你就顺道看一看他,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乐不思蜀了?!被流放的大臣,每年都会有几个,然而能让天子记下的,都有谁?几年一过,他把你这个人都忘了,某年某月某日,他经人提醒,都会问,这人是谁呀。别人一说此臣子的往事,他‘哎呀’一声,说,我怎么把他给流放了,召回来。哎,人就回去了。如果没有人提起,他有可能,一辈子也想不起来,当年流放了一个不该流放的人。可博格阿巴特呢,陛下不但记着,还托我来看他,谁敢说,他就没有出头之日,老死于此,病死于这儿。”
说到这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过他妻子这一死,怕是要坏事了,这个时候,邓被关把他抓起来,他还会冷静地想到我吗?!我现在忽然觉着,这或许是邓家的阴谋,往我身上系绳子,让我也脱不开干系,且观后效吧,要是施恩不成,反成仇家,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杀了博格阿巴特。”
说完这些,他闭上了眼睛,约莫说:“时候差不多了,该动手了吧。”
※※※
离开那些靠在两路的宾客,周围越来越静,最后,只剩下几个自认为是亲友的人跟随而踩发的脚步。夜色深深笼罩,让鬼和神一起现了身,一起探了五颜六色的爪子,无声地施虐,无声地狂笑。狄阿鸟的心灵沉寂到一片死亡般的平静中,感到两路一切都静止着,然而,慢慢的,慢慢的,狂暴的灵魂在遥远的天边晃动,细小的哀乐刮在他的耳朵边,让他眼前续幻出传芭(传香草用的舞蹈)的人影,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歌唱: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注:偷自《九歌&;#8226;礼魂》自译为:礼成了,鼓点密集。手执香草,更迭起舞吧。美丽的女子,又歌又舞,却突然静止不动,春兰在传递,秋菊在传递,远古至今,不曾中断,像春兰和秋菊一样的你呀,永远都在。)
抽丝般的低歌,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奔涌来,亦是狄阿鸟奔逐去,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妻,正在前方等他。
史千斤几个人跟不住,在左右小跑,陈绍武带一个新兵,总是去捞路勃勃的胳膊。跑了一会儿,眼看驿馆在前面,狄阿鸟忽然一收脚,站在了那里,几个人停在两路,看一看他,看一看驿馆。
驿馆静静地伫立,灯笼高挂,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几个去邓校尉家赴宴的宾客还自门口进出。身经百战的史千斤立刻就感觉出了点什么,太静了,一切太安静了,那些宾客,本来还在交头接耳,但一进门,就默默地往里去了,赞许地看了狄阿鸟一眼,脱口说:“有杀机。”
陈绍武哭笑不得地看看他,甚至有点儿愤怒,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心里难过,快进门了,他张口就是一句“有杀机”,是在捣乱还是在开玩笑?!狄阿鸟也往他看了一眼。路勃勃却怒了,哭道:“你娘的杀鸡,阿哥走呀。”他拉住狄阿鸟的衣襟,说:“走呀。”
狄阿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地问了一句:“宴会上,邓北关去了哪?!”
路勃勃觉得不对,阿哥的身躯有些僵硬,立即丢了手。
陈绍武不解地说:“怎么回事?!难道……”
狄阿鸟拉了丝鬼一样地笑容,问:“你们知道,安县长这样老于世故的人,为什么会辞官?!”
陈绍武想也没想就说:“他同情公子,心灰意冷。”
狄阿鸟说:“你错了。因为他已经在宴会上摸到了一点风。穆二虎造反了,他的官今晚就已经当到头了,被别人罢免,不如自辞,所以,这才脱衣取帽,那,谁能告诉我,邓北关干什么去了?!”
陈绍武狂闪灵光,说:“抓捕穆二虎的同党。”
史千斤赞叹说:“小相公心思好得很,一连起来,就是驿馆中有伏兵。”他想了想,又说:“可为什么,不在宴会上抓你跟安县长?!”狄阿鸟冷笑说:“应该是别有用心吧,我也不清楚,但我想,他是要秘密抓捕我,避免什么意外。”接着扭过头,问:“老史,能带我进你的兵营么?!”
陈绍武吃惊道:“不至于吧?!”看史千斤犹豫了一下,似乎有些为难,说:“去我那儿。”
狄阿鸟摇了摇头,说:“你跟我的关系太密切,别人容易判断,倘若到时用上令压你,你造反不成?!何况,他们要是判定我是穆二虎的同党,也有借口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