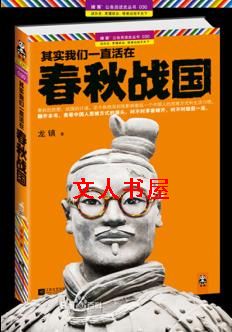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2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少女不知给谁喊了一句:“姐。你拉住他!”就猛地闯进来,猛地撩起帷幄,让抱着个透明的纱巾遮羞的吕宫猛地暴露到睽睽几目下。吕宫见小桃一下捂了眼睛,连忙跑去床上,随便拉片单子一包,大声喊:“有你这样的人吗?”
这时,他愣住了。原来,这个圆脸女子的后面,正是他梦中不舍忘怀的那个女子,此时她先捂了眼。而后睁开,最后和圆脸少女一起瞠目。大叫:“原来是你!”吕宫二话不说,抱上单子就跑。他几步跑到大门处,自己取了门栓,赤脚跑到大街上,刚一想扭头,发觉屁股后追来俩提白蜡杆的少女。连忙再加快速度。
单子被他裹去了脚下,他怕绊倒,往左右踢踢,甩掉又跑。
跑出十余步,迎面早起的老农妇出门,兴致勃勃地冲院子喊:“快来看。俩闺女提着棍子撵个光屁股的男的。”她的儿子出来不及时,她便兴奋地指了嚷:“那男的就腰间系了块纱布,看去黑糊糊一团,让人恶心死!”
※※※
吕宫一跑再跑,跑了又跑。心里正急,前头乱哄哄地起了动静。他发觉自己私印春宫图的院子不远了,立刻一溜烟地钻进去,从里面借身衣裳,急急忙忙地回家。还未到县衙门口。沿街就敲起锣声,到了县衙,许多人都蜂拥到那里,而吕经只身站在县衙门口,双手使劲下压。
他不知所以,随手拉住一个人。问:“怎么了。要打仗了?”
那人五内俱焚地说:“土匪要来攻县城!”
“什么?!”吕宫差点一屁股蹲到地上,喃喃地说。“博格把人带走完了,怕是还在等着打埋伏!”他大叫一声,挤扛而上,不一会到了吕经身边,刚到就挨了个耳刮子。吕经只骂了一声“你死到哪去了”,就说:“快回家去,看好家!我带着人召集人手!”
吕宫扯着他喊:“让人加急告知博格,让他回援县城。”
吕经大骂:“废话!还等你来说不成?”
吕宫又说:“让博格的人去,他能带上备用马匹换乘,走得快!”
吕经“啊”了一声,一手推了他,说了句:“那你快去!”而自己提着镇宅宝剑就喊:“不要乱,都回去。各亭的亭长把丁壮拉出来。敌人最快也要等到中午,援兵也会在中午回来。不要惊慌,没事地。”
※※※
人势渐渐被压下去,但不全是听调遣。
不少人急于回家收拾细软,只等情形一不对就跑。大概到了中午,亭长们只聚集一千多人。眼看赶回来的人四十里,三十里的数目报个不停,郡里的武员都一片火急,他们干脆拔刀指吕经的鼻子。吕经自己没法指挥,让人找李进喜,李进喜家里说李进喜不在家,一早出了门。他只好又让郡武官们指挥。
郡武官横眉竖眼地喝了一会,竟绑出来两个亭长,说他们惑乱人心。吕经又觉得他们不行,正紧张地给宣金良安排话,看到吕宫带着几个牵马人来到,一个是个身背几丛箭枝的青年,其余的都是身穿皮甲的老人和少年,连忙下到跟前,问吕宫:“这两位是?”
吕宫说:“博格家的人。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叫石春生!他们要先带十几骑去截敌头。”
吕经连连摆手,说:“十几骑怎能截得住?不是送死吗?”
石春生压住自己的紧张,立刻便说:“这样打过去,敌人就不敢再猛跑猛走。倘若斩得敌头,人都不怕了!”
吕宫给父亲解释说:“敌人一看咱抵挡了,最起码也会停下脚步。而要是斩了敌人的首级,还可以安释人心,拉出民丁!”
吕经立刻不给面子地说:“你也不懂。”他问宣金良,又问石春生,下定决心说:“好吧。看看能凑个二十来骑不?凑够了,全交给这位壮士。他杀他砍,咱都不过问!”
宣金良叹了口气,说:“老爷。敌人要到天黑才到,援军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的人有不少马帮旧人,说不准会通匪!主力天黑不到,夜里就熬不过去。”
吕经立刻安慰他说:“你放心吧,能到!”
宣金良这就转身,不大一会就照仅有的十二匹马挑出十二个人,令他们站成一排。吕经知道没钱不行,送来小半筐钱,让人抬着送到众人面前。石春生握着弯刀过去,抓上两大把,往第一个人身上一塞,接着又抓两大把,往第二个人身上塞,送到最后还有一半,给他们说:“回来,那些还是你们的。跑,我就杀你们!”
扈洛儿给他背上旗帜。他便带着二十余骑驰走。
第二部 击壤奋歌 第十九章 及回师县城转安,怒塞胸飞鸟报仇(1)
曾阳大县,置县时有民一万五千户,繁衍已过三、五代,虽战乱饥荒减人去丁,但加上入山躲避的百姓和外县奔趋而来的百姓,依然能有两万余户。县中地区是包括城关镇在内南抵县南的沃野,周围数十里沃野无垠,且不曾有大规模的战斗,更是良民们的避风港。
百姓或先前居住或接受吕经的后来安顿,在籍三千四百户,丁一万三,接近整个在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前日王水下来料计全州,也还是第一个见着这样一个地方,既使他怀疑吕经暗助郡守立阀系,成不法事,誓要扳倒之,可也不得不承认吕经的政绩。更不要说匪军。
众匪来到,眼里不全是户众宝货,也有对敌时的心虚。他们心里紧张不安,在没有遇敌前不太敢分散抢掠,簇走十分紧密。石春生出县南关,疾行十余里,穿过退走的百姓,很快就看到扛着简陋兵器的敌人。他见敌人或成排说笑,或一团堆里三三两两乱走说话,漫野无章法,立刻率本队十余骑迎头奔上。
最前走的敌人也猛地发觉他们,有点惊慌,嗷嗷一通吆叫。周围十几人“唰”地返头,有的退跑回自己的头目身边,有的竖着长杆往人堆缩,只有三五人留在原地。打前锋的匪头骑马挥剑,正迫他们回头,便看到对面冲到最前面的青年猿臂轻舒,老远手挽大弓,借追势起射。他本能地一低头,耳边听到“噗、噗”两声响,已有人卧地嚎叫,心里顿时又慌又上劲。
他是有面的人,不肯轻退,乱走赶出十余杆兵,再往后找。后面的人已经退空一片地,只好咬咬牙,追在人后大喊:“老子黑星黄达来砍你的狗头!”
两路顶头相逢,石春生赶县兵急走,扈洛儿带自家人后到转绕,电闪间又连声放弦,射在敌人身上。匪徒发觉自己又倒三五人,跑已跑不直,一个接一个地被撵杀。黄达心惊胆战,抬眼就见最先来犯的青年已舞刀掠来。胡乱搅马去杀,只觉得错身时前心一凉。有人问自己:“你叫啥?”
“黄达!”黄达心知不好,大叫着捂住飓血的胸脯,空走乱砍,又“杀、杀”两句泄气,摔在马下。
县兵认得他的名号,杀散敌兵去砍人头。纷纷簇拥到石春生身边说:“这下杀得好,那可是土匪头子呀!”
石春生听他们这一说,料想一战立功,就派一个人提七八颗人头的袋子回县衙。
几个郡武官来往调度,正找不到把守要道口的人选,忽闻有人来报吕经喜讯,倒出几颗人头,说:“石壮士领兵杀入敌群,一个回合砍了天二匪的四大头目之一的黄达。”便埋怨吕经:“敌人势大,怎可瞒着我们。把能打仗的人派出去攻打敌人呢?”王水也是这般认为,说:“不是正找不到把守的人选,不如就叫这位石壮士守南关的路口。”
吕宫怕父亲把韩复放出来用,第一个赞同说:“你们把守城门,我把马乡到城南关的路。石春生把张寨到城南关的路,谢亭长把谢庄到城南关的路。宣把总管住县仓和衙门,各位亭长和大人们一起把住城门……保证万无一失!”
众人纷纷同意,各抒己见,商量有半个时辰。这时石春生的人又回来报捷,说:“土匪派骑兵来打。我们杀七八人。夺马十余匹!”
坐中顿时惊起一片。大伙知那匪骑里有大天二收容的鞑子,曾几次打败李成昌。纷纷说:“各位大人,不但该让他回来,最好让他现在就回来。他把守住要路,蜂拥的百姓不会先冲垮县城,能做到万无一失呀。”
吕经见群情如此,也只好同意,立刻给送消息的军士说:“赶快让他回来,不然你们迟早要被敌人包围。回来,咱大伙一起守个结实,等到博格赶回来,这一仗就反败为胜了。”
军士也觉得这样好,出县找到石春生,把吕经的意思告诉他。
石春生连战连捷,已威震众匪,但凡遇到敌人,敌人就指着他喊“是杀黑命星,破鞑骑的无敌将军,我们快逃吧!”,然后就一哄而散。他也没有想到县里要自己回去,因而不满地跟扈洛儿说:“我们都是骑兵,在野外作战谁也不怕,可一旦回去守路口,就跟被捆了手脚一样,你说气人不气人?”
扈洛儿深以为然,叹道:“可主人在他们那里做官,不能不听呀!”
石春生还是不大肯,又说:“可我们一退,敌人就会打到县城跟前。之前打的威风都没有了。常听阿鸟说,将军在外面,就不能让回家就回家……”扈洛儿不知道“将军在外面,就不能让回家就回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无奈之际,破罐子破摔地说:“管他呢。反正又不是咱们在指挥!”
石春生反正也拿不定主意,听他一说,就领着人回去,不久见到吕宫。吕宫已为他找到一个路口,晃着一把明亮亮的短刀在那儿比划,屎顶屁股门地嚷:“快!快!快!你守这儿,我去守那!”
石春生看看扈洛儿和闹着跟来的图里牛老小一干人,心里怎么想怎么不舒服,干脆让他们回家去,一个劲儿挥手赶:“走!你们下马能打仗吗?都给老子回去,免得博格回来一看少了,怨我……”众人有自知之明,一个个低着头,牵赶着俘获来的马匹回家。吕宫一眼扫见,半路上面来拦,大声地跟石春生说:“你咋让他们都走了?”
石春生横着脸问:“你说我咋让他们走?”
吕宫“嗨”地一惊讶,扎了个吵架的姿势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早就听牛六斤说你倔忽忽的,那你也不能这个时候赌气呀?不就是从战场上把你弄回来了,让你守路口吗?”
石春生满脸通红地嚷:“守路口可以骑马吗?不骑马能打仗吗?”
吕宫摊着两只手,气呼呼地歪头摆理说:“骑马是打仗,不骑马就不是打仗,这是哪门子道理?你说道理呀。讲不出来道理吗?”
旁边的军士看石春生又急又气又火,就是说不上来,连忙解释说:“那都是老人和孩子……”吕宫是心里越紧张,嘴巴越上劲的人,鸡狗不是地说:“老人和孩子咋啦?!他告诉我说那都是老人和孩子都不行了,什么话,守路口可以骑马,噢,不骑马能打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要是你。你听得懂吗?”
石春生的头都快被他吵炸,哼一声走到一处泥堆旁。往上一个半躺,继而,他还来不及往下生气,就看看坐着的,卧着的,偷着跑地壮丁们。站起来又找吕宫,说:“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兵器!”
吕宫还在跟几个小兵摆道理,话儿流畅地,学了石春生的腔调驳斥石春生,说:“拿兵器能打仗,不拿兵器就不能打仗?你让他们用撅头夯你一下,用砍头锄你一下?”
石春生怒吼问他:“我为什么让他们用撅头夯我一下?用砍头锄我一下?”
吕宫又说:“不让他们弄你一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受不受伤?怎么知道是不是在打仗?”
石春生气茫然了,只好说:“不给你争了。他们这些人怎么指挥,谁指挥谁?”
吕宫也不再逞能。老老实实地给他说:“怎么指挥,不是你指挥吗?下头谁是长,你问问,我一下子也认不到!”他猛然记得自己那边把守的各长也没认一遍,连忙端着自己的短刀往把守地里跑。嘴里叫着:“不好!老子地还没问。”
石春生差点没有气晕回去,直到身畔有个敦实的蓝衣大汉边推他边说:“我是亭长张兰,本来一甲有一个队长,可眼跟前就那两个!你等上一下,我为你叫来。”石春生点点头,心里却在狂叫:“路勃勃。你骑马跑快。这阿鸟不能不回来。”
张兰比石春生还能调度,左右一喊。选出长兵器的站到前头,短兵器的站到后头,有兵器在手的跟着自己和石春生,总是瞪着眼喊:“那谁,你给我站到前头。你要是敢跑,老子先砍你们,趁我不在意跑,我到你们家砍你们全家。”
石春生立刻不让张兰地再整队伍,说:“咱们找个过不几人的地方守,把路拔坏,光几把弓就能守结实。”
张兰赞同,跑到自田下上来的土路上埂,而后让大伙收拾。那里本来就有一个摆摊的小棚子,路不但有坡,还拐了个弯。大伙都领悟到了玄机,四处扒土,或坏路,或加高站的地方。大概忙到一半,土匪来了,摆来几辆驴车一放,卸下几捆清一色的竹杆锐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