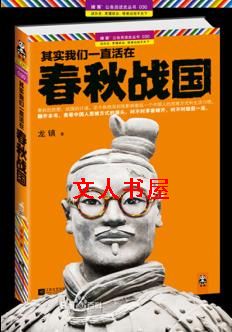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2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他妻子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去,好几次,还真是差一点。她觉得不找个人看不行,就把做早饭的佣妇拉去换值。这样一来,早饭就凑合了吃。
吕经大早晨端碗泡菜,放上两个杂面窝头去亭子,蹲在地上,用丰富的老脸和时时欠动的屁股来表达泡菜辣的程度。正吃着,他惊讶地发觉吕宫揉着鸡窝头,被他母亲喊打到自己身边,连忙问怎么了。
吕母告状说:“你看他的德行,竟爱上洗澡了,大早晨偷我烧的热水!”吕宫气急败坏,夸张地挥着手,激动地说:“不就是一点热水吗?我现在要出去做事,舒坦一点不好?我和博格商量好了,要把土匪头子的像一样画个百十张,就把画贴出来,发下去,给邻县送去,让他们逃无可逃……”
吕经疑惑了好久,反问:“用得着吗?和你要洗澡,有关系吗?”
“这个?”吕宫笑道,“什么时候,你和周哥找个大杂院,把人聚集一说,我就是主薄了。现在,我不就得为钱粮打好基础?”他想想,这和洗澡有了关系,却和要招画工没有关系,又强行牵引说:“我招了几个能写能算能画画的,先从书画局开始,为团练募集经费,给百姓谋福利……你们都不知道,博格的父亲在草原上发明了有名的彩印,可以呼啦啦地推出有颜色的书画,将来印圣人的书,印花鸟虫鱼,卖到京城都行……”
吕母看他说的跟真的一样,自己没法分辨内容里的价值,竟愣了,反问吕经:“这是咱儿子?”她欣喜若狂地去搂一搂,使劲地说:“过两天,我还打算让你去卖孵不出鸡儿的毛蛋呢……不让你去啦。好好干正事,咱读不会他圣人的书,就把他圣人的书全印成花花绿绿地画,让睁眼瞎也能看。”
吕宫点了点头,郑重地端出拇指和食指,压在母亲面前:“不过,可能会有点贵!”
吕经正要把详细的情况问一问,一个和吕经差不多的小人小跑进来,说:“老爷。老爷。铁狗要吃月亮啦!”这是一句约好的暗语。是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鱼开始咬钩。吕经大喜,立刻把威逼儿子这两天都在干什么的事抛得九霄云外,挣身往外跑时,把自己的碗都绊翻了。家人和吕母都随着地他的跑动把着两个手跟在旁边,嘴里慌里慌张地叫着:“你慢点,别摔倒了……”吕宫则大叫兴庆。他看看父亲的碗,发觉下面藏了半个鸡蛋,左右看看,弯腰一捞。顺手牵羊了。
吕经赶到二庭,还没有见到报喜的喜鹊。就看到一个青蓝布衣的下人牵引自家的主子,稍略弯着腰,欠着身,前低后高地、慢悠悠地向前作请。他再看看来人,一身乌纱,官袍。腹挺“日出竹隅”图,体态合宜,脚下缓稳徐扣,只好纳着闷,顶头拱手迎上去,说:“不知是哪位上官,清晨来见吕某人。有失远迎,幸会,幸会!”
有人交来官样文书。吕经皱眼过目,口中念念有词。走过他为何不带风声,突然来到自家门前的疑惑,笑道:“原来是便衣查访的王大人,快请,快请!”
王文官比他大。又是一个正路子一个野路子,没有谦让的理由也不需谦让,进了去。吕宫从弄墙边往外溜,半路就听几个到来的上差议论个没完:“你看。跟个猴一样蹦来蹦去,哪像咱王大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吕宫心知在说父亲,朝地上唾一口。骂道:“什么玩意?看老子怎么在老子的书画局整治你们好样的王大人。老子专门印他的裸体。”他挣个气话。歪着头直走,突然间傻眼。韩复竟叫了公门中可算点葱蒜的角色,乱杂杂地在那聚着。他意识到了,父亲也要经受他自己不得不面临的考验了。
※※※
吕经刚接到周行文的快报,生怕坏了这一仗,什么都咬牙不认。王文也就按韩复的意思,给他个难堪,逼他交出权力。吕经只是不快不慢地应对,一二再、再而三地说:“上头若有官文,我这个县长想当也当不成。上头没有官文,我还是得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您是州官,要管大事,不要老盯着我!”
王文还是第一次见这种烂角子,出了衙门还在给韩复叫板:“还有这样的人,让我不要老盯他,就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你也不要直说呀,是不是?”
韩复把他送上车,看到吕经站到台阶上整袖子,表情很严峻,心里还真有点毛。正好,王文又喊他,说:“今天,我要到城北去看看,你陪着我去!”韩复点了点头,正要上他的马车,感觉背后被什么叮住,肉皮都被叮疼。
他一回头,才知道吕经揪他衣裳,误捏了皮肉。吕经晃着肩膀,大大咧咧地给他说:“韩复。我当着上官大人的面,照样要说给你知道,你是个有能耐的人不假,一点不假……”他猛地一吼:“可你要坏了我的大事,我照样要你的人头!”他又把声音放低,说:“嗯?我知道你猜出来了,倒是要问问你,你怎么挑这个节骨眼给我来这一手。你是看不得别人的功劳呢,还是别有隐情,不会是想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吧?”
说完,他留下阴晴不定的韩复,转而给县中众吏说:“今天都不要走了。午饭有人送,晚饭有人管!”
王文狠狠地捶了一把车帮,他招上韩复,冷冷地丢了一句:“你怕别人分功劳,别人却怕你为出风头丢乱子!”说完,他便要车夫赶车。车夫吆喝了一声,正要走,被要报复的吕经拽到。吕经说:“这是雇的车不是?县里已通知下去了,所有役使的牲口都要备案,接受贴补?!你这牲口备案了没有?没有备案的,都归县有。”
赶车的老头经不起吓唬,连忙说:“备了。这是我们员外家的……真备了。”
吕经又说:“记着,不许它给我乱跑。这一趟下来回家,你让主家养好,喂好,什么役使事也不能跟春耕碰头!”
赶车的战战兢兢地又赶车,走不过十步就跟车里外的人说:“这车马,老爷以后是用不成了。谁让老东家领了人家的补贴呢?以后逮着就罚,抓人,也抓牲口!乡里的三老都说了。抓人给县里背犁,抓着牲口,一俩月都归县里用。”
王文反问:“还抓牲口?”
赶车的肯定地说:“抓牲口!哎!不许你家的牲口干别地,光让它们下地!”
王文的手又捶捣车板,激动地把两只盘着的胳膊猛一下送出去,大声给韩复冷笑,说:“我打第一遭见!我白活了几十年,第一次知道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开春种地是好事,是大事。可你看看,他还拽赶车的牲口。拽着咱用的牲口要抓!”
给百姓补贴饲养牲口,要求官私役半。这是韩复也同意过的主张。他不好意思落井下石,只是叹息说:“有时候,我心里颇佩服他玩阴谋的本领。你看他生活土,那你就错了,他藏了好几个供奉,大冬天用转动的竹子搅热水……你看他一心为什么春耕。他却把粮食捂着,不让人知道,你看他不把你当回事,可他给大贾马大鹞拉了一队兵马保护。这里有他,这里就被一只人手挡了天。我韩复弄不垮他,这辈子白活!”
※※※
吕宫知道父亲要碰上事,并没回去,而是要去加紧赶做博格需要的“春宫图”。去到,和挨过重鞭子,不能出征的路勃勃、石春生碰头,进到一个交好的年轻人家里,那里已经有两三个人在忙碌。吕宫看看,这两三人还是自己狐假虎威,硬以官家的身份威胁来的。目前为止,没招来一个上门的画工,便立刻朝招人的路勃勃和石春生看去。
路勃勃捏着的几个盲流画的“小鸡吃米”图让他看,说:“他们来应聘,我们要不要?”吕宫看了一看,无奈地说:“还问我画得好不好?这哪叫画。”
路勃勃只好抠了抠眼睛。再去和石春生一起招画工。
他们来到土巷外的墙角,架好摊子,大声地喊了两声。立刻就围来一大堆挤扛的人,他们凄迷着眼睛看了半天,又问问要不要帮忙的人手,都沮丧地散了。他们沮丧,路勃勃和石春生更沮丧。石春生搂着两条棉袖子,扒到摊子上打瞌睡,说:“我喊也喊不出来,光想睡觉!”
路勃勃连连撞撞他,激动地说:“我看到那个女小姐了。她会画牡丹,你在这等着,我去问问她,看看她肯不肯画!”他揉揉黑脸,呼噜噜地甩来胳膊追。丫辫少女没有和那天一起的姑娘在一起,换了个同伴,两人手挽着手,边说边娇笑不止。
路勃勃猛地跃过她们,按着两个膝盖喘气,说:“小阿姐。我又见到你了!你们把吕宫个臭小子怎么了?问他,他也不讲。你去帮他画画吧,也帮帮博格。我会记住的!”最后一句他说得响亮,一下就把两个少女砸愣下。
那个画牡丹的少女举了一支柔柔的指头,眯眼眯了半天,惊讶地掀起殷红的小唇说:“是你!你说的是那个傻书生吗?我们没有把他怎么着,一个人让他叫了一声姑奶奶!他真是个画师呀?我还以为他是骗人呢,可他画画还让人帮忙?”
另一个少女和第一个少女差不多高,有圆圆的脸蛋和圆圆的眼睛,可都太圆了,拼在扁平的面孔下,显不出好看和可爱。她撇了嘴,看着第一个少女说:“李姐姐还在等着咱们呢!别跟乡下的野孩子一起去,他肯定是个贼。”
她扭过头,左右看两眼,挑鼻子竖眼地说:“看这乱的,还让人出门不?”
路勃勃气了半死,只想一脚踢死她。可他还在请求另一位,就善良地笑了几笑,心想:先骗去再说,让吕宫那个嘴巴厉害的人拿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哄她,这就撒谎说:“他要人画牡丹!”
丫辫少女跃跃欲试,立刻说:“我要酬劳的。”
路勃勃也快说快决,说:“他肯给!”
丫辫少女点点头,又说:“这样吧。你在这里等我,我过一小会儿就回来!”
路勃勃大喜地给她指指那个墙角,飞快地跑走,心里已在大叫:“吕宫。老子给你招了个人来!”他跑过石春生那里并不停,一口气跑回去喊吕宫,大声说:“春宫图的母版好了吗?我请人来画牡丹!”
吕宫听了就蹦出来,夸奖说:“这回是个爱美女的人吗?”
路勃勃抓抓头,疑惑地说:“画牡丹的呀。春天花开,有花才是春呀!”他想了一想,那个小阿姐一直和相貌不丑的女子在一起,便肯定地说:“是个爱美女地!”又想她是个女地,补充说:“还是个爱美,爱春天的!”
这时,第一张画被印出来了。职业画工欣喜地跑出来,大声说:“看看,效果真不赖!”路勃勃拔着他的手,凑去脑袋,整人惊呆了,只好喃喃地说:“他娘的春天呢?这不是牛六斤的娘吗?肥胸大屁股。”他激动地摸过去,被女人腰下的男人和那根黑糊糊的东西刺激到,血脉贲张地退两步,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生理反应,心想:坏了!那个小阿姐还不知道春天不画花,不画穿衣裳的人!他不敢自己去见,就捅着吕宫的屁股说:“她还要酬劳。你去给她说酬劳,我再看看这画!”
吕宫被他骗了去,不一会就见到几个少女结队来问,其中还有自己的意中人,恨不得跑回去找路勃勃算账。他也是个脸皮厚实的人,总要有个说法,文雅地说:“主家要画一些阴阳交感,万物受到滋润的景象,用意境来感染一些心地不善良的坏人,让他们放下刀枪,向官府投降!这是全县百姓的大事。你们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当是忍受好了?”他觉得自己也不能把少女们想得太好,又说:“你们就画妩媚的女子和壮实的男人在一起相爱,相互那个……在家里画就行了。”
莺莺的问声一片:“哪个?”
丫辫少女解释说:“相互爱慕,辛勤劳作,过男耕女织的日子,不再碰刀碰剑……”她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大声说:“家乡蒙受战乱,不得已,父亲带我来这里投奔至交。我能体会得到和平不义,会很用心地画,让我的父亲也画。他的画虽然值一点点钱,虽然被张元帅追捧讨要,但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而收受一分一文。”
少女们受到感染,个个意气风发,大大方方地说:“对。回去就画,明天就给你!”
吕宫傻眼了,连忙推辞说:“我看还是算了,一幅两幅,再好也与大局无补。我需要几百张呢。”
少女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画!”
吕宫意中的女子早去了不良的印象,觉得他是个正直的士人,留到最后才羞答答地解释说:“我们都在和褚怡的父亲学丹青之术……虽然画得不好,也够田夫野老明白意思的!”
众人顿觉他们两个之间有猫腻,无不呜呜怪笑。她们你推我,我拉你,挥着手,说着尚不知道画画还有这般大用处,一时正着拉同伴的肩膀,倒着跟同伴说话,轰隆隆地一片走,一会就过了墙角,吕宫从边边上走到中道看,不舍地挥手。而他的那个女子确确实实又回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