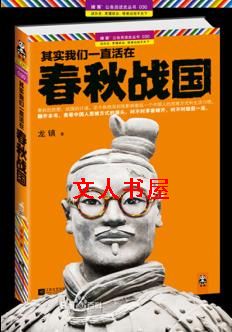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2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还不清楚?乱到现在,十户九空,不料怎么办?他来了,咱就把人往少里报。一来为以后的赋税打算,二来,以后地政绩也就越显著!就是不知道他是几品官,怎么巴结。”
吕县长嘿嘿一笑,乐观地说:“反正比我这九品大。我这不入流的小吏,也就是年岁乱爬个官,当下去也就这么大。糊弄也罢,交底也罢,爱民也好。小人也好,那都顶片棺材入黄土了。”他转过头,问自己的儿子:“你读书读得怎么样了啦?要不要我把咱家祖传的玩意送出去,给你换个前程?当着你干哥哥的面,你敢说句读得好?”
吕宫打个饱嗝,合不拢嘴地说:“咱家就不是书香门第!你说我读书,会读得好吗?”
吕县长扭过头给飞鸟说:“什么人他就生什么鸟。你这个兄弟读书不往好里读,给我说脑子不好,记不住。但他把官府的条律记得牢牢地。我给你讲,他一小就偎着衙门口。趴在地上那看大老爷审案,那府上有个师爷看久了。就教他背官府地章程律法,唉,那是一教就会!后来,他读书了,看到摆冤枉摊的老妇人,非要给人家写状纸。所以。他那些同窗就送了他给外号,叫‘吕壮士’,也就是状师。把我给气了个半死。结果,他乐呵呵地说:将来,我就去京城,专门给人打官司。”他顿了一顿,叫嚷说:“你说这熊人,他就没有一点出息。师爷那也好,那状师是干什么地,专门喝人血的。”
吕宫连忙皱着眼睛。以解释反讥:“我不喝不就行了?你说我能干啥,除了写状子还能干什么?你那点家产,除了能让我种地,还能让我干啥。”他给飞鸟摆手,又说:“你知道我家祖传的。我父亲当宝贝的青铜壶吧,我小时候老尿里面,他要送人,我就告诉别人去!”
飞鸟无端端地羡慕吕宫,心说:人家父子温馨,我却没了父亲。他看哈哈大笑的赵过停不下来。就让图里图利给吕县长敬酒。说:“户籍,我是愿意落到咱们这里的。可中州是故乡。总得回去看看不是。我不再的时候,就让他帮助您和周兄吧。不过,您可得相信他,肯用他才是。”
图里图利举了杯酒,边递边说:“我叫图海。世代都是博格家的部将。”
吕县长点了点头。飞鸟这就又要求说:“老图。你给大伙露一手!”
图里图利为难了,心想:我拿什么当本事呢?左右看遍,看到县衙里卧着一只大石槽,就过去掇了,憋一口气,一举举到头顶,而后扔了,在众人叫好声中回到飞鸟身边。飞鸟要他做下,又问:“让他做周大哥地左右手成不成?”
吕县长和周行文都觉得好,连忙还酒让图里图利喝。
赵过起了炫耀的心思,也要求说:“我也露一手吧!”飞鸟没允1许,只是又给吕县长说:“军士打仗用命,想要地不过是财物和功名罢了。我这些部下也一样,希望大人在打胜仗的时候,把从贼人手里缴获的俘虏、东西分出一部分给他们!”
吕县长拈须点头。周行文立刻说:“这是应该的。再说,咱都是为了自保。缴获的东西除一部分应急外,全分给有功的战士!”
飞鸟立刻识趣地拉了吕宫,说:“那就得有个人来管理杂务,钱粮。不如让我吕宫兄弟来操办!”
吕宫兴奋地站起来,不等父亲开口,就连声说:“可以、可以。”
飞鸟一杯水酒就把人事提妥了,这就又在吕县长地耳朵边说:“也不是非得现在就要钱要粮,找个土匪窝子打一仗,赢了,什么都有了!”
※※※
正是县衙热火朝天的时候,县城来了十几人几驴。骑驴的是个三十有须的读书人,带了仆仆的风尘也掩不了的书卷气,一瞧就是个有钱的远路客。城门两路有躲游牧人的难民。他们瞧见了就堵,呜呜地讨要吃的。
这十几人既然这么一路走过来,自是不怕。一人仗剑而喊:“滚开!”
人穷则痞,衣衫褴褛的讨饭青年说来推就来推。那骑驴地读书人只好从驴上下来,面容憔悴不堪,问:“上头不是免了你们曾阳的粮,还赈济了吗?都不去种地,改为向我乞讨?我能给你们什么?”这话把人问住了,众人看他也不会裹藏粮食,就说:“灾粮都被当官的吃了!我们是没见着,你看那衙门口,还飘着肉香。”
那读书人意气指点,大声说:“很快就好啦。凡战乱期间不称职的官员都要换掉,该杀头的杀头,该发配地发配。你们好好种地,不要闹事。”
人们都觉得他是上头派来的官员,纷纷诉苦,有的说怕鞑子,有的说没地种,有的说种了也是给别人种的,有地说当官地雪上加霜,不发种子。那读书人斯文地劝了这了这些痞民一阵,眼看闹的越来越闹,围观地大老远来看,不得已,就在随从的保护下跳出人圈,问哪里有住处哪里有郎中。别人便把尚郎中的大院指给他,一部分人去安顿人和驴,几个则随着他去看病。
一个下人扶着他一步一软地挪,说:“少爷呀。你这是累的。你哪吃过这样的苦呀。回去,老爷夫人非哭不可。咱好坏也是个官,怎么能这样走路呢?我知道,你是怕别人上计的时候骗人,可眼下,那地方官,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百姓呀。”
第二部 击壤奋歌 第十六章 余情未了(3)
那公子爷一路摇头,等走到尚院前的街上见到一所用皮革蒙了的帐篷,睁着两只眼往里跑。一个腰上别着弯刀,怀里抱了个孩子的年轻人在帐篷前道的木桩边下马。他嘴里几吆喝,一上前就拦了这鬼鬼祟祟的几个人,往大门里一指,骄横地说:“这是我家搭的,滚!”
跟着那中年少爷最近的下人觉得脸上过不去,搂着两个胳膊肘,斗气往上扛,嘴里骂道:“你这个不长眼的要谁滚?”这时,一个追风样的矮个子猛地从尚家大院里蹿出来,扣了拳头扑到对方个儿最大的人前,“嘣”地敲了下去,嘴里大骂说:“再不走。老子砍你们的头!”原本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个捧罐的蛮族姑娘,她把药罐往地上一放,一边冲拦人的年轻人喊:“博大鹿,你来干嘛?就不会说句人话吗?”一边冲猛虎下山般的矮瘦汉子喝:“你看我不告诉博阿鸟!”矮瘦汉子只好退到一边,往前头指了警告:“滚不?!”
那公子和身旁的人惊乱地朝他一望,整人披头散发,红黑的脸上透着狞色,胸前囫囵的革甲上绣了个斗大的狼头,像是活脱脱地一匹野狼,立刻大呼:“这是个鞑子!”鹿巴听到朱玥碧呼唤阿狗,放阿狗往大门里跑,自己也很快因身上的饰物和胸口的虎头引来震惊的目光。
这时,戴了面纱的朱玥碧听说鹿巴的事儿,最怕他抱阿狗,一随图里花子自大门内出来,就先喊“阿狗”。直到阿狗撞到她怀里,她才顾得和那捧药的女子一气,辩解说:“我们是刚刚归国的百姓。他们兄弟几个在外久了,哪儿会跟人打过交道?您大人有大量。别和俺们计较!”
公子嘴都打了哆嗦,激动地指着他们说:“那也不能动手打人!我们朝廷还是有王法的。小小的一个县城还住得下你们不?”
见牙猴子有话要喊。段含章出腿就是一踢,连连点头,笑了赔礼,说:“我们千里迢迢地归国,见人三分怯,敢乱打人吗?这不是一脚出门,看到几个人在这挤扛,不知道怎么回事,鲁莽了。
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们这些人一般见识。等我告诉家长,让他亲自给大人赔礼。”
那公子在女人面前终显大度。虽听自家人说人手重,还是息了火气教训了几句,往大门里进。他借直走再扫面前的三个女子,突然流露出奇怪的表情,不肯把目光移过朱玥碧地面纱。段含章等他从身旁穿过,便嫌笑一通:“这就是读书人么?”
她扭身去捡药罐去了。图里花子却发觉朱玥碧浑身颤抖。连忙问:“你怎么了?”朱玥碧喃喃地念叨:“我一定是认错人了。这不可能。不可能。”段含章紧问了声“谁”,接着笑着说:“是不是熟人,叫回来问个清楚吧!”
朱玥碧摆了摆手,进了帐篷才给段含章说:“像是你阿姐的同乡,叫一声也好!”
段含章已看出不同寻常的地方,迫不及待地要出去,又被她抓了回来。朱玥碧又说:“算啦。别去了……免得阿鸟知道了,疑神疑鬼的。”
“他穷大方,都肯把腰里的剑送人,怎么会厌恶你的同乡?”段含章说。“再说,你要不想让他知道,我就不告诉他。”
朱玥碧还是摇了摇头。段含章只好出门煎药,心里笼了一片疑云,暗想:在她的阿鸟那儿。我只不过是个牲口一样的女子。倘若她再生个儿子,我就更没有受宠的机会,像现在不能同床共枕的日子会越来越长……
略一迟疑,她立刻把药包里地草花丝儿抓掉两三条,暗自叹气说:“既然生了你,为什么长生天还生我?害你吧。我不忍心下手。不害你吧。宝特大人什么时候才肯正眼看我?老说我没才能,我比她好多了。”
她垂头丧气地扇着扇子。嘟了嘴巴又想:男人都是不长眼睛的,哪知道谁好谁不好?
她低头看看自己地胸,又记得飞鸟要自己时的奇怪,脑海立即被痛不欲生的自卑淹没。突然,一个声音在她耳朵边响起。她抬头看了一看,才知道是那个读书人身边的胖中年,没好气地问:“有什么事?”
胖人似不记得和鹿巴挤扛的事了,见牙猴子也顺畅,依然熟捻地拉家常说:“姑娘呀。你家自国外而归,花销一定很大吧?”
牙猴子冷哼了一声,说:“那当然。怎么,你还想送两个钱花花不成?”
胖子立刻摸出两颗碎银子,丢给了段含章,转脸给牙猴子说:“你让我们公子躺一躺这帐篷,行不?我们住的地方还没着落,这里地郎中又非让人按顺序就诊,我家公子实在是受不了了!实话告诉你们,我家公子是州府里来的,得了你们……”他声音越来越小,越来却轻,却更撩人:“的伺候。不是让你们攀了门靠山吗?”
牙猴子听得胸口起伏不定,转脸给段含章说:“他想到咱家的帐篷里住,说他们家公子是州府来的,得咱伺候了人家是咱攀了门靠山……我日他的娘,这都不知道怎么给阿鸟说好。”他一手提了那胖人的衣襟,想到对方让阿鸟的女人让帐篷,让自家的某个女人伺候一旁的念头,便狠狠地捆了一把掌,把那胖人打得尖叫不止。
那胖人慌里慌张地喊:“你打人?不怕坐牢么?!”牙猴子不吃他这一套,骂道:“打人。老子恨不得扒了你地五脏!”段含章脑子倒只剩下对飞鸟的怨愤,恶意地图个嘴快,花枝乱颤地笑嚷:“说不准博格还真要攀这靠山呢。你看他回来怎么说?!”
朱玥碧先推出阿狗,而后自己出来,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大度地说:“我们家还泊了辆马车,让他躺一躺也没什么。”她看了看段含章,说:“你家公子叫王水,字清河吧?让我们家这两个丫头照料照料也行。不过。真有了要援手的地方,还请令公子多多帮忙!啊?你问问他,行吗?”
那胖人捂脸而鄂,他看对方的手劲松了一松,挣脱而立,气呼呼地说:“莫非小娘子认得?就冲你家的人,不计较就是了!”
这正应了段含章地想法,她注视那胖家人走脱进院,心中决断说:“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你要是让我去伺候。以后也甭怪我无情!”图里花子却不知道她要借这事下争宠夺人的决心,轻佻地说:“怎么样?中原地俏郎君!”
段含章气不打一处来。撇嘴反唇:“那你要呀。”
朱玥碧心烦之下,倒忘了段含章对中原读书人的热爱,似不让她如意一样,轻声说:“她是被气着了。花子去,顶多是换个汤药。这娇生惯养的人,不一定哪饥着、寒着了。事情多!”
※※※
王公子在胖下人地搀扶下入了帐篷,是没听下人讲对方能呼出自己姓名地事儿的。他很想借感激之名去问候,看看那家地夫人是不是自己的旧人,却又迈不出这艰难的一步,就拥着被褥缩着。这时,他看到一只小狼样的孩子,一个有着瘦脸颊,尖嘴唇,却显得有点儿脏地孩子。他见那孩子扑闪了漆黑的眼睛看自己,便百无聊赖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阿狗坐到他面前。把两脚掌抵到一起,不老实地去摸他地袍物,好久才回答说:“阿狗!”
王公子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连忙问:“那你母亲呢?”
阿狗摇了摇头,被他问久了。诚恳地说:“还没名字呢!”他摸到王公子防身用的宝剑,摸到外袍,干脆爬起来去找王公子腰上的饰物,竟摸把小刀,自己去割拴饰物的系带。王公子又惊又乍,一把握了他的手。大声喊人。
图里花子进来看时都傻了。王公子把小刀藏到身下。被阿狗一手抓在头发上,一手抡打。只好一边惨叫阻挡,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