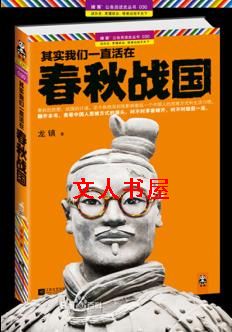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2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你以前来过吧。他就光笑不说话。
至于射箭前问好标准的,极少。飞鸟这回带的都是极少的“钻裆獾子”,专找你的空档,斗嘴斗得小刀笔吏嘴疼。
文武司长官拿了图里图利送来的好处,答应让飞鸟挑个女子,邀他到帐里说话。
武官是拓跋巍巍地嫡系,进了帐,挪身就上炕一坐,文官是从,因是陈州出身的读书人而没有入座的自信,搂着两个厚厚的皮袖子替武官捧出飞鸟的两臂弓。武官揉着厚圆地面片脸,递了一碗奶酒,诚恳地问:“你能拉开这宝弓吗?”
飞鸟把双臂弓拿到手里,憨憨地否认说:“这哪是什么宝弓?废弓!我那女人是从别人那抢来的,想害我。我把它拿回去,改送好的。”
武官胸里也没装礼数,转身向身侧的文官看一眼,粗声一“嗯”,耿耿于怀地问:“你女人怎么会不知道?该不是你看我拉不开,想收回去吧?”
文官立刻躬了身,摇着面颊帮腔:“野利大人心里是有你的呀。他受王庭器重,来这儿干什么来了?不单单是要你们一起去打仗,还在为可汗物色人才。他想把你推荐到另一位野利大人的帐下,得一个博取富贵地机会!不是答应了你,给你一个十户官吗?”
飞鸟摆了摆手。说:“可我有二十多户百姓,多出来地人呢?”
文官愣了一下,小声在武官耳边说两句,笑道:“从你女人送来的东西上,野利大人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与别人不一样,所以准备让你到另一位野利大人那里效力。你地人说给我们你没有部众,我们又怎么知道?说给你个十户官,那也是白给你了十户人,给你个能往上走地身份呀。”他竖了指头往外撇。补充说:“你若想要这外面的丁零人,有野利大人在。也不是没有办法。但事成与不成,那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也不是野利大人说了算的,因为那是可汗自个要要的!所以,你想要,得让这些丁零人承认你在先。其次嘛,到了可汗的王庭,得记着是谁给你的富贵!嗯?”
飞鸟发觉自己还真小看了这两个人物,竟没问这位野利大人的姓名,这就点点头,再给了个抱礼,说:“应该感激野利阿长大人!可这张弓真是废弓!我改天再送好弓!”
文官“啧”地一砸嘴,教训说:“你怎么这么傻呢?你不说,野利大人不说,谁知道它是把废弓?装饰一下。
可以送给野利大人要感激的人,野利大人也要感激人呀?是不是?什么样的东西最贵重,就是它不是个东西。”
飞鸟扭了头,直挺挺地冲他:“我不说,野利大人不说。那还是一把废弓!送一把别人拉不开地弓,不是在羞辱人吗?我不懂你的道理,只知道不该欺骗野利大人,也不该害野利大人!”
文官无奈地摇了摇头,野利长官高兴地点了头,喊着“对、对”。遥遥地伸出手拍飞鸟地肩膀。便又替他要求说:“野利大人的家族很大,出来公干。回去是要拿出能送出手的东~西地。你总得让他有两样别人没有东西吧?”
野利大人挥了挥手,自个问:“把你的车给我弄一辆,好——不好?”
飞鸟回答他说:“我这辆是不行,给了你,打仗时,我家的女人、孩子怎么办?我们高车人没有了自己的车,那就等于马没腿,鸟没有翅膀。不过,我可以给你做辆小地,好看的,让你哄哄人。”
文官发觉飞鸟越说越不像话,不阴不阳地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飞鸟冷冷一哼,说:“给,我就要,不给我就不要。”
※※※
领到的女子满头乌发,穿着一身湖水青底紧身小袄,下面的袄裤镶绣着花条子,足下一双粉头签底鞋,走起路来,左右两半屁股小西瓜般滚动,惹煞人眼。飞鸟把这女子送上车,到朱玥碧身边,见她用担忧的眼神望着自个,心里偷笑,暗想:这女人吃起醋,倒是让男人不知道生气好,还是高兴好。我总叫她傻女人,其实她哪里傻?这不,要不是我不舍得把自己家的大车给野利不花,能多得多少百姓?
他钻到车外,找赵过商量:“阿过,前日俘获的女人,人家都争着要,可你却嫌她们无姿色。今天得了一个好女,你喜欢不?”
赵过发愁地看看他,小声小气,用简直不像他自己的嗓音说:“我是想。可想到唐凯的阿姐,心里就愧疚得很!”
飞鸟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心里有点自惭,便劝他说:“中原乱成了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谁死了,谁活着,那都是没有准地,倘若得不到她的消息,你就不娶亲了?”
赵过嘿嘿笑笑,说:“咱不是快要去中原了吗?我回去找找看,肯定能找得着。”
飞鸟只好不再往下提。牛六斤都听着呢,他抢老婆抢晚了,硬是要了个三十余岁的红脸婆,听人说“女人大如娘,日子过得长”,倒也肯进被窝,让人老牛吃嫩草。但这前提是不能让他知道有了更好的女人,一知道,立刻便腻上来。
他刚说了个要得意思,赵过便已笑他:“糟糠之妻不能嫌。嫌了就不会是忠臣好汉!”
鹿巴和张铁头已有了,心里还不平衡,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嫌弃,却也合起来打击牛六斤。说他帐里卧了个,“宝”,不睡不知道好。而石逢春,那是在飞鸟眼底下的姐夫,得了飞鸟地阿姐回心的许诺,把吐沫咽了一坨又一坨,就是没法吱声儿的。
飞鸟哪个也不让他如意,转而想到祁连,心说:一个人给你们弄个,老婆,将来再有漂亮的,我就哄哄阿狗她阿妈。自个要了。
他这只是玩一样地想法,心神早已受到赵过的感染。被天风迭送荡涤,清亮地只想站到高处眺望。然而,打马登高,极目四方后,他突然间感念到自己对这里地热爱,不知道自己这么一走。还能不能任马驰骋,心里渐渐惆怅。
他记得少年时见的猛人——东部沃野地懦弱,北部荒凉地里的善战,又记得阿爸对藩事的灼见,便怀念一样感慨:“庸人喜欢安逸,丈夫喜欢忧患和磨难。人锦衣玉食一辈子,就会过于爱惜自己,什么时候也不能明白捧雪揉面、雪夜狩猎的乐趣。那时,难道心里不空虚吗?狼不停地追猎,羊不停地奔跑。这才像生命呀!”
他打马下来,拱着高车继续往前走,老远就听到张铁头嘎嘎地笑声,他正在给牛六斤喊:“你知道个屁!中原的狗比你们这地狗厉害,咬人。人都吓得不敢动。到了中原,见着了,你就怕了?”
牛六斤把张奋青的话拾起来反驳,反唇相讥:“以前你见着狗呀、狼呀,老觉得被咬了划不来。可现在一见着猛兽,眼里剩地都是好皮好肉。所以就不怕了!这可是张奋青自己说的。我们关外的狗吃的多是生肉。一咬就咬喉咙。”
路勃勃立刻前来帮腔,说:“你没见到牛六斤家的野猪皮!”
张铁头耍赖:“牵来呀。”
牛六斤哼了一哼。转而又拉了只狗,说:“阿鸟也养过一条狗。那狗就是‘雪山来客“又大又猛,可以撕死豹子!但我们这的狗从不咬巴特尔。我阿爸常常给我说:‘不做亏心事,不怕猎狗咬。人诚实、正直、威风,狗就怕你。’”
张铁头立刻找赵过帮腔。赵过振振有词地说:“人诚实,正直,威风,鬼怕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咦,怎么狗也怕你?”
飞鸟已偷笑起来,心想:你个傻家伙,硬是把帮张铁头地话给说翻了。
※※※
新女接到家里,朱玥碧有点忐忑,招来自己新心腹段含章散步。
段含章虽听她说家里多了个女子,不知道怎么摆放,却已深掘她的内心,立刻就说飞鸟的不是,嚷道:“阿姐怎么会嫁得他?他就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看,得凶一点,闹他!不许他胡来!”
朱玥碧软绵绵地说:“三妻四妾的男人多了。我不是明白事理,可是一想,心里就又酸又疼的。也怕。我是比他大不少的,哪天人老色衰了,他还要我吗?”
段含章啧了一声,怪她:“你就是心软!当初为什么嫁他?”
朱玥碧眼睛说红就红,扶着她的手臂,在雪上兜了几步,一声比一声小地说:“我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主见,只一心让他好好的,吃好穿暖,心里高兴,一心想让自己漂漂亮亮的,让他一见到就心痒痒。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去干,什么苦都可以吃!可他把我点亮,疼我管我,给着我温暖,可就是不让我知道,他是爱我呢,还是需要我地身体。他是个男人,要是看上了别人,长了翅膀飞到别人身边,我该怎么办?”
段含章想想,爱是什么?自己个也弄不明白了,嘿嘿笑笑,拿出自己的内心话反驳:“他有什么爱?杀人杀多了,心里铁实,让他爱嘛。就是得驯服他,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这样咱才有底儿呀!”
朱玥碧摇摇头,嫣然回眸,给了她一个轻瞥,笑着说:“这就是你不懂了。男人喜欢温柔的女人,你再有才,再有德,那也得温柔。他们打猎、打仗,熬得都是一身的伤,看起来更刚强,夜里也不过是个孩子!阿姐教你的,你要记住:一个真正地男人最需要的,不是你的本事,因为他已经很有本事了。他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体面的威严,有离了他就不行的女人和孩子,不然,他没有了休息地地方,日子没个着落,迟早会被别人打败。”
段含章心中一哂,暗说:“你真够可怜地。他都把女人接回家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还跟我大谈温柔。要是真能俘获男人的心,你也不会心里没有底了!现在就要去中原了,我就不相信他不会钻到被窝里和你商量,倒是一问一个无主张,看起来和一头猪有什么区别?”她多少有点内疚,叹道:“阿姐太善良了。迟早要吃大亏!我都在替阿姐着想,你说着马上就要南下中原,也不知道在百姓面前隐藏身份,怎么能在敌人那里安安全全地过日子?”
第二部 击壤奋歌 第十五章 丁零南下(2)
朱玥碧怔怔地看着,怎么也不明白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考虑这些,但稍用心一想,就明白段含章未雨绸缪、想得比谁都深远。她惊闷半晌,脱口就问:“你小小年纪,想这些干嘛?”段含章以为她定要深究“想这些干嘛”,心里虚,紧张地摆了摆手,解释说:“这是明摆着的吗?要不是关系到阿姐,我才不去想呢。”朱玥碧心里发热,可又想要她往下说,便连连追问:“那你说怎么办?替姐姐想想!”
段含章矜持地吐愁,眼神儿眯了一下,就比着朱玥碧的肩膀压到前头的地面上,颓丧地说:“阿鸟宝特不知保密,已将身份泄漏出去,我能有什么法子呢?就是阿姐,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也是没有办法。”是呀,嚷都嚷了出去,还有什么收回来的办法?朱玥碧期待之色稍一收敛,便拉了段含章,叮嘱说:“见到他,你好好地问他,要多给他出主意。我知道你是个伶俐的丫头,脑瓜里的籽多。等一会,你回去收拾收拾,以后就住到我身边,替我看着阿狗,咱就是一家的人了!”
段含章头摇得跟拨楞鼓儿一般,挣了身,跺了几步脚嚷:“阿鸟宝特见我的第一天就把我捆了,塞到帐篷里。让我一天到晚见他的面,我怕得很。”朱玥碧老听她说厌恶飞鸟的话,哪会由她,死活扯了那胳膊,劝说:“看你也不是胆小的女孩子。他吃得了你不成?”
段含章再嚷理由,已都是说不出口的,就半推半就地从她去了。她们回到小帐、大车边儿找飞鸟说事儿,没有找着。
图里牛、图里草都背过路勃勃,坐着车舱壁周围的蒙皮板,阿狗几个小孩儿晃着车舆,催督用盾牌挡头的路勃勃“好了没有”。路勃勃撅了屁股往地上栽画了骨头的小皮块。一绕,正准备进到车舱,被朱玥碧拦到。朱玥碧看看不早的天色,发觉那东面已沉得像一头黑牛,就给路勃勃说:“你怎么又玩起来了?你看人家钻冰豹子,哪天不是天不亮就去抓鱼。阿鸟疼你,你也该让他省点劲,别老跟图里牛,咱家里有他阿爸、阿妈地羊……”
路勃勃理直气壮地争辩:“钻冰豹子是我抓回来的奴隶,他勤劳不好?不是替我们家干活?再说了。我打猎的时候多了,你都没见着。”朱玥碧正为找飞鸟不着讴气。一听他的长篇道理就冒气,责怪说:“钻冰豹子的狗被狼咬死,你去看看就行了嘛。要不是你偷懒,阿鸟怎么会自个跑去?你也不想想,这营里大大小小有多少事让他拿主张?”
路勃勃收了委屈,气呼呼地说:“阿鸟不让我给你顶嘴。可你也不能老冤枉我。是我不去的吗?钻冰豹子看到那条狼会掏人挖的冰窟窿,来喊我,图里牛他们都不让我去。阿鸟就让我继续玩,自己去了。你怪我什么?”
朱玥碧朝段含章看了一眼,无奈地嘀咕一句:“都是阿鸟把他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