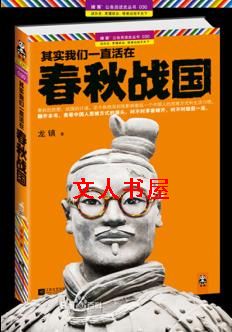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2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夜,图里图利、鹿巴挖窖,烤火。
夜,路勃勃决定尝狗粪,未尝。
今日,伐木。飞鸟让钻冰豹子打磨鼓身,中间薄,两头厚。让祁连磨皮,中间厚,四周薄。制成要敲,阿鸟让我敲。我敲:响。阿鸟截木烧炭。牙猴子制牛角,女人还仿制手抓,还做帽子……
今日,伐木。泡皮革。造大木锤,锤头又胶又皮,小地给路勃勃打牛,大的一人一把。阿鸟造弓,一只两臂、一只三臂。都太硬了,暂时没有人能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弓,就像两头蛟龙和三头蛟龙,偏偏都可以用一个身子使劲,有开动的一天,肯定能射四、五百步远。
今日,伐木。开山。阿鸟竖一根木,造大冰,以大冰撞高石头。让人以大木栓撼石,撼动垫冰囊,再撼。采石一车。以炭烧,烧成石灰。
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强烈的朔风和鹅毛般的大雪都将远去,飞鸟万事顺利,唯有大车和冶铁屡屡失败——不管飞鸟怎么设计大车,都是造到一半散架,不管他采回来什么颜色地样品石头,大抵是被炭一烧,用脚一碾,就是生石灰沫子。
飞鸟渐渐地焦躁,一边让鹿巴去班烈家接自己的阿妹阿弟,一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大车上,只等造好两三辆大车,就不怕战争中顾不得弟妹。
说到底,飞鸟在造车中遇到的困难都是因为缺少金属。首先体现在车轮的制作上——众人用大木曲截法制了一堆零碎,因没法用铜钉、铜轴固定而不牢靠;其次的难题是车体面:虽然用凿子和木楔子凑造了车身,也还是得有足够多的铜钉、铜楔、竹根;再次,则是几牛抬扛的车轼和辕,前两者拿不出来,后者就没法试的;最后,几只固定整个车身的大横梁,虽然用下窄上宽地车围卡着,但还是起不到固定的目的。
苦于无计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家的旧矿,决定到最近的一处走一趟——倘若还有工匠,就掳来工匠或换取块状铜铁,倘若没有工匠,就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残留地金属。
等鹿巴几个走了数天,回来时带了的惊喜——他母亲接了飞田几个去中原,摆到面前时,他更想在春暖花开前造出大车,往返中原,这就带上人,说去就去。
第二部 击壤奋歌 第十三章 生命之绝唱(3)
带着赵过、牛六斤等人来到黑驼山时,那座山矿果已荒废多日。
堆放矿渣的山谷中还有少许人留下。
这些老少都有“黑”铁的背景,要在高显拉走十三家大工后赚上一笔,眼瞅着冬天没能如意,个个都跟老猫瞄食一样,乍一眼看到飞鸟赶来的几匹瘦马、几头牛,就霸王式地给上五、六斤没过火的块铁,摆了不换也不行的架子。
大伙就着一座被雪压塌的工棚里那几尺高的雪台子,摆了大碗酒谈生意,谈着谈着,刀子就抽了插到面前。坐鹿巴对面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年纪虽已不小,腮帮子上却还滚了年轻人男人才有的横筋。他发觉自己灰白的头发被瓦进棚子的风荡动,就用粗大指头勾了勾,缓和一样来说服:“来一趟不容易,马也别牵走了,牛也留下吧。我再给你几斤铁精,你回去勾勾火,也能用!”
接着,他威逼一样伸出头,用鼻孔“恩”地一问,就走到飞鸟身边,把台子上的雪一抹,解了腰上的小袋,抓出一小撮,放在飞鸟的面前。
什么铁精?飞鸟一看在面前蹦的颗粒,就知道那是铁渣。
他左右看看,石春生对面坐了个黑青年,鹿巴的背后蹲了俩狍子头大汉,连路勃勃身旁也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是一个或几个看一个,因而心里更加有数——他们压根就是拿了强买强卖的势头,只因为讨假还价的鹿巴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铁”白痴,这才没有贸然翻脸。
既然对方有心吃掉自己,自己更不必手软。
他按掉心中的一丝愧疚,黑着脸骂要不换了的赵过说:“你懂什么?这种铁精做的箭头最厉害,射人身上就活不成,比铁贵!既然要为咱阿爸报仇。非得多多地要。”
说话地那老汉脸上露出几丝不易察觉的奸诈,“那是”、“那是”了一阵,拿出吃亏吃到底的样儿说:“既然是给你阿爸报仇,我也就不赚你钱,全给你铁精。你想要多少?要是不够,可以先欠着,打完仗再还!”
飞鸟看看他,心说:“铁渣勾火,质劣不说,一去就没了三分之二。你他娘的真当我是白痴!”连忙感激地喊声“阿伯”,说:“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我拿什么还你?我不欠你的。今天先住下。明天等图里图利再赶几十匹马、几十头牛,全换了——。你家还有多少?带我去看看。”
老者心里一喜,招手要了飞鸟说悄悄话,还把女儿许出了口。回头,他聚了三五家子坐下商量着这笔生意要怎么吃,吃多大。一商量就到下午。
这时,路勃勃和牛六斤已在他们的草垛和马棚边呆着,给几个女人吹嘘飞鸟家的富有,嚷那头领把女儿许配给飞鸟的事。一个年龄不大的姑娘听得入神,很快就咬着雪白的牙齿离开了。她摸到了飞鸟在山阳树起地营帐对面,卧在雪地上往下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一个姑娘爬到她身边,小声问她:“你在看男人吗?”
第一个姑娘羞然,小声地说:“豁哥林亲家根本就没有女儿!他老是欺骗善良的人,一定会被长生天惩罚地。我阿爸根本就不该受他的保护。为他打铁。”
第二个姑娘说:“你阿爸从中原来到我们这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离开了豁哥林亲就再也没有地方可去。我阿哥给我说,豁哥林亲虽不是好人。但他有办法,有儿子,很快还会为一个大部的首领冶铁,有好的前途呢。”
第一个姑娘咬咬牙齿,说:“他还不是想用阿爸炼的刀巴结别人?要是我阿爸还冶炼不出他要献给首领的宝刀,一定会因为坏了他地事而被杀死。
“我要把豁哥林亲欺骗他们的事告诉下面这些买铁的。让他们带我们走!”
说完她就爬起来。从雪坡上往下滚。
※※※
除了路勃勃和牛六斤。飞鸟几个人都在休息。他们只等到了天黑,就从马圈下手。怎么也不防一个姑娘摸到营地里,把小帐帘子一个一个地掀开看,就只好半羞半喜地把她逮到飞鸟面前。
飞鸟细细看这姑娘,白皙的嫩脸上透出股温婉贤淑的气质,苗条的身躯修长匀称,竟是名不可多得的美人,就色咪咪地伸出手,在她脸上抓一把,说:“这一定是那头领的女儿!也好,反正是我的女人,先拉到我帐里睡一觉。”
那姑娘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女伴的话,吐了一口吐沫,大声说:“胡说。我不是豁哥林亲地女儿。你们这群把铁渣当成铁精的白痴,不知道好歹的东西!要是敢碰我一指头,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飞鸟哪管,和石春生合力,说把她捆了就把她捆了,左右使劲,把她提溜到脚不挨地的高度。赵过好心地去安慰,说:“你人挺好的,还来告诉阿鸟。我们只让你睡一觉……”刚说完,他胯下就被那母虎般地姑娘踢中,弯腰往一旁跑。
鹿巴一巴掌抽过去,拔了刀,准备砍了再说。
张铁头立刻来争,保护在那姑娘面前,大叫:“我,我来……”刚叫完,他发觉自己做了赵过第二,便低了一低头,“嗷嗷”地弯下腰去。
那姑娘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恨不得一头撞到豆腐上,来换回自己自取其辱的本意,一边厉声尖叫,一边又奋起一脚,正中张铁头的头。飞鸟只后抱个结实,连忙让石春生再拿绳子,把腿也绑了。
等飞鸟把她摁结实绑了腿。几个人这才面面相觑,不知道对这样的俘虏怎么办。张铁头揉着自己的脑袋,商量说:“这小娘子练过腿功,正适合我。阿鸟,你已有了女人,就把她给我吧。我调教、调教,再给……再给……”他转了一大圈,觉得自己玩了后还不舍得给人。就说:“我做老婆!”
牙猴子不愿意,趴到跟前,边啧啧赞叹,边说:“我年纪大,老光棍,鹿巴也一个人,轮不到你先要老婆——我看,大伙拈阉,谁拈着了,归谁。”
那姑娘欺负这些人对女俘虏无经验。又是一口吐沫给牙猴子涂了脸,镇定地说:“你们想要我也行。谁杀了豁哥林亲。我就嫁给谁。萨满说我嫁的人必是一国之主,就看你们谁会是真豪杰,谁是欺负女人地骚山羊。”
飞鸟大叫厉害,心想:这女人还真有手段,简简单单地一句话,就把命运高挂了。即分化我们,又让人以巴特尔自居,不拿她为难。
不过,越是这样,越让人窝气。
于是,飞鸟很不舒服地笑笑,问周围的人:“谁杀了豁哥林亲,我将来就封谁做国王,把这个女人给她。牙猴子,你要不要?国猪呀!国家里地猪。再也不用训练了,吃饱就睡……好不好?”
牙猴子没有多想,笑吟吟地张了张嘴。赵过连忙用手堵了去,大声说:“阿鸟才是一国之主。今天夜里,谁也不能杀豁哥林亲。只许逮住他,给阿鸟杀!”
飞鸟更不舒服了,骂道:“你们都是一群头大无脑地人,娶一个女人就能当国主?今夜一定得杀豁哥林亲。只有杀了,其它人才不会抵抗,咱才以少胜多。既有了铁。还能多出上百的百姓!咱一个人睡她一回,都做国王。怎么样?”
那姑娘的脸一下发白,哭喊说:“我好心来告诉你们,豁哥林亲以铁渣骗人,你们却要恩将仇报。就不怕长生天惩罚吗?”
张铁头是有磨嘴皮的功夫的,说:“不怕!我又不是草原人……”
话音刚落,头顶就响了一声闷雷。鹿巴往天空一觅,扑通跪倒,看着阿鸟说:“冬天里打雷。长生天他老人家动怒了。
飞鸟也抬起了头,眼看四空晴朗无云,湛蓝的天空亮洁得让人无法相信,心里也生出一丝敬畏。他看张铁头也“哎呀”一声跪到地上,抬头看着青天白日,磕头告饶:“我是说着玩的。”上去踢了一脚,脾气就摁不住:“长生天示警,必有其因。要是为了保佑这个女人?要是。您老人家再打一声雷,让我们听清楚。”
大伙站的站,跪的跪,无不抬头盯着,紧张地等了半晌也不见了雷声,便把目光集中到飞鸟身上。飞鸟得意地笑了,又抬头大喊:“我没打算杀她,只想给她找个好丈夫。你看赵过好不好?他……”
突然,天空又撕了一裂脆响。
飞鸟心气转到耍赖上,不由咽了咽吐沫,把眼睛眯缝起来,扯着嗓子又喊:“万一没有人做一国之主呢?她就是寡妇了呀,你是在惩罚一个好心的姑娘,好意思吗?亏我这么——这么相信您老人家!我第一天跟您老人家谈心,您可不能让人失望!”
牙猴子拉拉他地腿,小声地说:“阿鸟。你就少说两句吧,千万别惹出什么大惩罚!”
“怕什么?长生天喜欢勇敢的巴特尔。”飞鸟给他一脚,对着天空问,“是不是谁敢把她拖进帐篷,你就让谁做一国之主?俺家兄弟众多,缺少女人,不能不要她呀。要是谁把她拖走不对她好,那才是真地恩将仇报。那时,您老人家再惩罚我不迟。”
说完,他并没有让人拖那姑娘走,而是让步地坚持说:“我留着你是怕走露消息。反正晚上杀豁哥林亲的人在我们几个里面。你就挑吧,扫好了便进他的帐呆着!”
牙猴子第一个摆手,刚说了句“我不要”,那姑娘已听进了耳朵,给飞鸟说:“我进你的帐。”
飞鸟微笑地摆了摆手,那姑娘就觉得身子一轻,被赵过和石春生一人抬头,一人掂腿,扔到一个黑咕隆同的地方。她既害怕又急切地等着半晌,不见人来,突然觉得那人不会再钻进来,只好大喊:“那个补丁头,你进来!”
没有人搭理。
她一下冒了一头汗,心想:他为什么不进来呢?他不进来,我怎么求他救我阿爸!于是,她大一声小一声地叫个不停。
一只手伸过来,把她嘴巴里填上破莘片。她更激动了,燥热,跳动。两条绑在一起的腿一伸一缩,始终也摆脱不了噩梦一样地处境,只好麻木地安静下来,瞪大两眼,在黑暗里望着,望到疲倦时就睡着了。
等被刨出来时,她丝毫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知道四面漆黑,前面有火光和人影。她麻木地跟着牵了马的飞鸟走,揉着发涨的嘴巴。活动、活动木木的舌头,说:“补钉头!我求你了。你把我阿爸带出来好吗?”
路勃勃凑过头。不懂地问:“阿哥,你帽子上打了补钉,她就叫你补钉头,要是你裤裆里有补钉,她会不会叫你补钉裤裆?”接着,他猛地一直身。跺了跺脚,喊道:“将军!路勃勃点了马棚,前来大叫。”
飞鸟傻然,问:“什么叫前来大叫?”
路勃勃揉了揉脑袋,说:“赵过教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大叫!”
飞鸟想了半天,觉得错是从赵过那就开始了,也不强行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