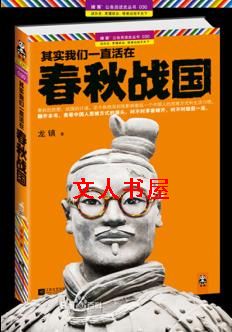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17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军虽然善战,然此战推到长月之势已成。”来人边说边扯过桌上地图。以手指划道,“此时将军屯于此地。无险无阻,怕是抵挡不住敌人全力攻打,即使一时能够抵挡,敌人可分出兵力向侧下移动,截摁水路渡口,陷关中为绝地。若不能妥处外藩,将使数万大军耗在仓州,内不能救援,外御三面之敌,是为亡国下策。”
健布诧异,尚不相信秦纲会有这般见地,但还是狞笑道:“这是你想的,不是纲王的意思。你又怎么知道我不能在此地一战败贼?”
董文还是第一次见健布有如此表情,心跳不由急剧加速,不禁为来人担心。他转过头。见来人半点不惧,直勾勾看住健布不放,眼中还冒着火花,更是在心底暗叫:“我知你为故上司之缘故,对将军颇为不满。却也不该这般游说,白白耗费王爷的一番心血!”
窒息的压势在室内上升,来人一字一顿的声音清越无比:“调练此军者对官兵的熟悉不下于将军,善战也不下于将军。将军若无前败,定可使人信服!而此刻,却也不是小看将军。不说什么知己知彼。
怕您连夏侯武律何故来攻都不清楚,又如何克敌制胜?”
“冒昧地问一句。将军可知道敌方大将何人,兵力之数?”来人戏谑地问,“恐怕连不少士兵们都知道,你可知道?!”
健布再也忍不下,牙关都在激动地跳动,他森森一笑,问:“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突然,董文醒悟,觉得自己不能这样观看健布受辱,当即大喝道:“大胆!来人哪,先把他压出去败一败火!”
气了半死的健布也不阻拦,胸口起伏不定地坐着,可一等兵士压此人而出,立刻问董文道:“与我对阵之将难道不是夏侯武律?观其作战,善于出奇制胜,确实没有默默无闻的理由。”
董文也是刚知道不久,这就把自己知道的倒出来。健布一边琢磨“狄南齐”和“狄南堂”,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却又想到他和秦纲的关系,便停住不问。他苦笑连连,突然猛一扯桌面,将上面东西尽数推在地上,自嘲一样悲嚷:“十三衙门不归我统属,是他们有意封锁真相。若我能得悉他作战的特点,又怎会有前日之败?天哪。这打的是什么仗呀!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江堤被掘一事,还以为敌人连胜骄奢,给我们喘息的时间。秦台,你难道不知道将帅若无耳目之聪,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吗?!”
朝廷朝战火起处一指,什么也不说就迫人去打的糊涂仗焉能不败,连董文也觉得可悲。但他知道是该让健布更加不满,便半点不劝,扯住了另外一件事回报:“朝廷里指派武学学子到军中任职,统御溃兵,怕是不能服众!”
健布又被打击了一下,“呼”地而起,大叫:“谁不知道猛将出于卒伍!他到底要干什么?到底是不放心我,还是以为这些未经锻炼的人才可堪大任?他们连血都没见过呀!还不如让武学里的夫子来代替我打仗,那也比把冲锋陷阵的人全换掉好!”
他像一头乱走的狮子般冲撞,喉咙里不断地咆哮:“这个蠢材,恨不早废了他!”
董文知道自己已经点燃了健布的熊熊不满,便激动地等待着。果然,健布一转身,便冲他问:“我若是废了他呢?!眼下,我说废就可以废他,我——”说到这里,他看董文直勾勾看住自己,突然泄了气一样闭眼,再睁开已掩饰住必露的表情,只是说:“我再想想看。还是先调集辖军吧,得找一个可以服众的人节制。张更尧过于世故,又远在仓州,孟然过于梗正,陈元龙被调离——”
董文在他盘旋的空隙插嘴,毛遂自荐说:“我!”
健布呼了一口气。点点头,郑重看过他,略一抿嘴,叮嘱说:“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对是非不可苛刻。谁是谁非,不提也罢。我对一些将士下手过重,以至军心涣散,就看你能不能赢得此军军心了!”
※※※
董文出来,雨已经停了。黑忽忽的夜里到处都是青蛙和虫子叫。他一回想到健布的牢骚,就想起失利的陈州之战中。那人的信中所提到地“知己知彼”,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驻地。
又把那封书信读上一遍,心里不免惋惜地感叹:错过此人,乃是错过战后复兴的机会,幸亏主子英明,深谋远虑地想到了许多事。
良久,他裹了一件油袍子出来。去向半路里对游说健布的人表达歉意。他知道健布并不是真想置此人于死地,而是正为冲突苦恼,但并没有给来人说这些,也算是对健布的同情和钦佩之心驱使,有意为健布留下隐私。
回来的时候,他迂了一个圈子,转到其下的几处不放心的营地去看看。
溃兵的营地湿漉漉的,新发的单帐都没裹被油布,入手湿透,到处都是难眠的兵士在抱着身子猴在树下发抖。而不多的营棚里,早早挤满了吵嚷、呻吟的兵士,甚至有人正为争地方而打架。
入眼污浊,他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一些军中疾苦,可全无解决之道。此地征调的房屋和修建地营舍要先仅着整编制的精锐住宿。一时间不能全顾。
不过游牧人也应该好不到哪去,湿热的天气和他们脏污的身子相遇,那肯定是疾病和瘟疫。
这样,他们一定急于决战。
健大将军和主子都对此进行预测,但得出的结论和战略不同。健布是死守此地,通过四通八达的地势保证供应。钳死敌寇;而主子却要避退到长月。不作正面交锋。此时,以他本人来看这大相径庭的观点。还是觉得健布的战法合理。
一想到这里,他心里便波浪翻滚,升起无限的敬畏和爱戴,也因而在急雨留下的水洼下脚时带起乱溅的泥水。
他随即向一处高里避,踏过之后才觉得不对,耳边只听到涡水声一响,半个靴子都陷到一个泥洞里。正是他又狼狈又生气的时候,旁边两笑喋喋刺耳,随后是几个幸灾乐祸的声音:“皇太鸟快看,又是哪个没长眼地踩进‘缺鳖坑’里去了!”
一个亲卫用火把一照。一旁的林子里吊着不少皮绳和布做的兜袋,上面的人都裹着油布和皮子,旁边横过的长木里拴了一排马,又怪异又难看。
见那里有十几双眼瞪得圆溜溜地看笑话,手下人便张口就骂。可那些人看不出董文的官阶,并不理睬骂声,而是带着肇事后准备打架的心理,愉快地点人头。其中的赵过摁住掳掠来的那个年轻小营医,用脚点了两下警告,一回头,就可着嗓子哄不知道到底怎么了的飞鸟说:“阿鸟!到底怎么回事呀,别闷闷不乐地了。先说,这次有十七、八个人,要不要跟他们打一架。”
董文拔出脚,带着半截腿地泥走到跟前,冷冷地扫视,目光深得让人不寒而栗,远不是沙通天可比的。几个离得近地人终究有点张皇,便下了自己的“床”,伸胳膊往前指着说:“那可不是我们挖的!我们也就是睡不着,看个笑话。”
这是想着千奇百怪法子入眠的兵士,他想。随后,他想笑却不觉得有任何可笑之处,转了身子看到二十多匹的马,不由踌躇了一下,便给身旁的人说:“问问他们冷不冷,以前是哪部分的!”
飞鸟接受着弟兄们挖空心思地哄他高兴的努力,半睡半醒地躺着,任谁怎么问也不回答。他根本不想动,也不想问,直到听到董文留下的两名严肃的士兵给众人说:“将军让我们问问你们这样冷不冷?”这才猛地坐起身,往董文走掉的方向跑去。
董文一行听到有人赶过来,先后站住。一个卫士询问道:“你追来干什么?!”
“我想问将军几件事。”狄飞鸟大声说。董文回头,看到一个浑身污垢,有着乱糟糟头发的少年军士腰部一剑一刀,便让他到自己身边来,微笑着垂询:“是有什么事让我帮忙,还是想向我道歉?!”
飞鸟一步一步走到十步之内,咬紧着牙关,冷冷地问:“我向你打听一个叫狄南堂的人,听说他以前是辖军都督。因通敌叛国,被健大将军诈降,死在异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董文敛住笑容,眼神闪烁不定,顿时想起那不堪回首的日子,经过迟疑一番后,忍不住问:“你问这做什么?”
狄飞鸟忍住上涌的情感,解释道:“他欠我父亲许多钱,使得我家无衣可穿,无马可放,无路可走。我父亲要我找他来要,可我听说他已经死了,就想在你这里确认一下。”
董文抬头,在黑黑的夜空中看了一番,这才注意到少年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他最终不打算回答什么,转过身子扔下一句话:“是死了!”
他带着军士大步往回走,这时,听到背后的少年又沙又冷的声音:“你不好好给我解释,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
“莫名其妙!难道是个白痴!”他想,“即使他真的欠你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能见了将军模样的就追出来要钱吧?!”
火把远去!留在原地的飞鸟被漆在夜里,心中无半分辉芒。他紧紧地握住两个拳头,一想起父子二人对靖康的忠诚,泪流已是满面,心中已是大喊:“阿爸!你为何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为什么?”
他转过头,见几个好奇的弟兄老蛇一样起伏,躲躲闪闪,想到隐瞒也不是办法,就说:“我和大将军有仇。今天夜里就带着赵过和大陈离开,所以才收了帐篷,宿在树林,愿意跟我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只要不想着告密,我也不怪你们!”
说到这里,他又已是泪流满面,心中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响:就这样走了吗?!我们都是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的。难道就可以一走了之吗?既然要走,我们又为什么要来呢?!
第一部 刀花马浪 第五卷 山高经行云漠漠,冲冠一怒家国仇 第三十节
回到不断“噼啪”滴雨的树林,气氛变得沉闷。
没有人表白心迹,也没有人询问飞鸟仇从何来,个个都挂了一付木讷。
这时,飞鸟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莽撞,竟然当众剖白,要让他们和自己的国家为敌。他期待地望着众人,渐渐知道自己被孤立,便明白地一笑,只把目光看往几个老弟兄那儿。
陈绍武能感觉到他投射在自己的面孔上期待,慌忙在地上乱看,希望在他眼里的自己是在找东西,而不是犹豫不决。
赵过收拾过自己的吊床,最后卷成一团,跟着拉出马匹,往几个各有所盯的兄弟那看一看,自埋自怨地嚷:“这怎么会是真的?我以为是说着玩的呢!”
这时,有人仍不敢相信他态度的急剧转变,追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才来到这里,还是你坚持来到这里。你怎么能这样?!”
仇恨和失意让飞鸟自暴自弃。他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镇住,突然察觉出自己难得的可笑,生出一丝自怨的心理,便放弃危言耸听和尽量说服,只是似笑非笑地掀起嘴唇,淡淡地说:“你们为你们,我为我。战场上见!”
这也是心烦意乱的陈绍武自己想知道的。他觉得飞鸟近几日的表现反常,便等在那儿,希望主人能让自己明白为什么。但飞鸟没有等他的反应就拉出自己的马翻身上去,心中已展起一把大剑,把许多情思斩断,让自己冷血,坚定。然后,他振缰转过半个马身,在马嘶后大声说:“决裁当如刀斩。还有什么可问的?!”
此兄弟决裂之时,只有被众人虐待半日的小营医怕自己的小命随着别人灭口玩完,图个最后的嘴快,大声呼吁众人不可一走了之,而其余的人都不知如何是好。
“阿鸟!”赵过给了旁边地小医一脚,果断地翻身上马,回头吐了口吐沫,肯定地说,“朝廷而已,我早就和他们势不两立了!”
几个老兄弟没有陈绍武的远见。心底被这实话砸了一下,想想自己以前的所为。先后上马。清醒一些的陈绍武左拉右扯无效,不得不朝飞鸟奔过去,挽住马缰,哀恸地恳求:“不投靠夏侯武律好不好?他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样是要受人唾骂的。主人要看得远一些,万不可因为小怨而自毁前途。去哪都行。到哪我都跟着你!”
飞鸟狠狠一笑,便把头扭到一边,一脚踢翻他,喝道:“走不走!”
“不走!大伙也不能走!”陈绍武跪于路上,哭泣道,“我们都是靖康人哪。哪里能去投靠杀我父兄,淫我姐妹的仇敌呢?!”
飞鸟愣了一下,想说什么没有说,直到振马走了好几步才冷冷地回头,但感情已喷薄而出。激动地大吼:“我不是靖康人,这又怎么啦!你们说我父兄为野蛮人,那就做点文明的事出来,为何照样去草原掳掠开疆,去奸淫妇孺。休找借口。你的誓言不算也罢!滚!”
在一群人目瞪口呆中,他一把扯去束扎的乱发托,冷漠地振头,用双手插在濡湿地发际往后捋过,喊道:“我本来就是鞑子,所以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做多么文雅的样子。都是你们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