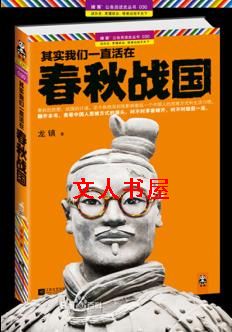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1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此同时,处地较低的健布难以观察到敌情,只好坐船逆行。他见当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有不太强烈的西南风,非常有利,再看敌军阵营,人马少而且稀疏,聚成一小堆一小堆的,因为地形不好,队列都列不起来,还时不时后退,前进,顿时心情轻松不少,下令推进精锐。
战斗很快打响。靖康精锐信心百倍地冲锋,而狄南齐的骑兵因为地形限制,难以拉掠,优势很快向靖康倾斜。
见除了在起烟后退外,放地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地抵抗,连健布也觉得意外,他边松气边给身边董文说:“你看!敌人对骑兵过于依赖,竟不知道把步兵放在前面!这样的地形岂能和我军精锐争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发起总攻,按预定的那样,在河边留出空间,让后军通过,插入纵深替换出击。
喊杀冲天,人头如麻。烟雾也越来越大,从西南直刮西北。董文惊讶地询问:“怎么烟雾越来越大?敌人不至于向自己放火吧?”
健布也在奇怪,不自觉地自船伸出身体,斜里观望,突然,他作为一名优秀将领的直觉,叫了一声“不好”,立刻就大声冲着下面嚷:“快,号令人马撤退!尤其是后面的车驾。”
因在舟中,传令颇为困难。正是他幡然醒悟的时候,喧叫声自南而发,在乱石堆里鱼贯出兽皮花脸的勇士。赶在靖康军之后,之南猛冲。
只要一回头,腾烟就冲人发泪,继而天地都被黑烟裹过,靖康人马不相识,相互自相残杀,尸血遍野,慌号中不知道敌人多少,见上路又被放地大军截断,不断又滚石飞下,只好往北里撤退。
那里却是一条不断送军去前线的通道,也是人马不断,自相一冲,顷刻溃乱,落水践踏者不计其数,健布紧急调集不多的小船营救,却被争相而上的士兵压沉。
眼看昏天暗地里注定了一场无法挽回的大败,眼睁睁站在船上,却无法改变的将领们全都泪流满面。
第一部 刀花马浪 第五卷 山高经行云漠漠,冲冠一怒家国仇 第二十七节
六月的炎热和潮湿从上浇到下,让跋涉中的人很难清醒地明白自己是活在人世还是活在炼狱。背着盔甲的士兵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眼窝集水成洼。他们的背上被硬物接触磨出血泡,只留在身上的单衣不单被挂烂成条,还凝结着因汗水浸涸的血痕汗斑,而且总是油在身上,而脚下的鞋子,都如同粘饼一般又湿又粘又烫。
在翻越高耸险峻的关中屏障前,飞鸟他们经历到行军的最大考验,队伍已减至一百多人,剩下的也都被艰险、饥饿、炎热,潮湿折磨得又瘦又疲、疾病连连。这时——即使他们以前再怎么有勇气,也会在消磨中丧失,面临着活下去和爬越最后一道障碍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也惟有留下做土匪,才能活得下去。在这种集体意志之下,飞鸟也难抱守自己的底线。在他们还算克制的抢掠行径下,他吃不下,睡不安,虽然总在安慰一样想:我们得去适应,顺从境域。这一定是长生天降下灾难。即使我们饿死,也是多余。
但,有时,他还是感觉到上天在睁着铜眼冷冷看着。尤其是在焦躁上火的情绪致使他脸都肿了起来,下巴下和脸颊起了许多的脓疙瘩后,他便一分一分地厌恶自己,觉得自己是受到了惩罚,流毒流脓。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知道了夏侯武律的身份,不知一次地觉得,自己在战争中负有使命和责任。所以,他觉得即使磨短两条腿,冒上生命的危险,也是应该回到关中,因此决定和大部分的人分道扬镳。在作出决定后,他挑出三十多匹还算活蹦乱跳的马匹和十余名心如铁石的军官、弟兄一起回去。而让左宁在惯匪方铜的帮助下,领剩下的人在原地休养。
唐关开战的消息并没有封锁。听说之后,他们在灰暗的晨色中入山。等到出山时,靖康已是败势如潮,伤溃之兵遍地。他们夜中下山,还未来得及休息,白天就被败退的人马卷裹,最后到达路德。
彼时,健布把自己从前线带回来的骑兵放在后线,本着良好的布置。得以避免整个局势被溃兵牵动。但中郎一过,关中往长月已是一马平川。虽是城邑众多,但刚经过西庆战乱不久,民生凋敝,城防新修,防守军力不足,也只能靠薄弱的丁壮役徒死守。对狄南齐的在运动上占优势的人马起不到足够的牵制作用。
此时,狄南齐也许应该全力乘势,不给健布缓和和喘息的余地,但他追击地人马在健布的骑兵那里吃了不小地亏,眼看闪电席卷的人马极需休整,而后顾之忧已经解除,便缓了一缓。
这一缓给了健布极其宝贵的时间,让他得以在二线上收聚人马。路德虽是新郡,本无固守的条件,但处于官道枢纽。既可拱长月,又可聚集游散人马和物资,因而应时变成重镇和健布收集人马之所。
飞鸟的人到了这,眼看要道当头已屯起大寨,各番号军旗麻花一样撒开。到处都是三三五五的散兵游勇游戈。他们见上头设岗封锁了通往后方的大陆,没有军令不让往后方通行,凭看军旗又找位置,只好等到被收集人马的游傲带到大营再编制。
飞鸟对人还好,一起的靖康军官回想起来尚有好感。但他们回归朝廷后多少会有对身份和名义的顾及,言谈虽仍客气。但态度已开始躲闪。不少去找熟人的一去就不回了,只留下几名没路子的什军官。眼看身边还有二十多人。飞鸟也只好降低身份,按上头的意思,补充到人马损失惨重的天蝎军下一个合成旅里,按令驻扎在旅驻地西北的白杨树林边。
所在的营地里全是肩膀略显耷拉的溃兵,回荡着一阵又一阵放荡不堪得比哭还难听的笑闹声,撕裂过受伤者那高低不同的,孩子似的呻吟和呼疼,汇合成浩大的杂乱。
但并不能影响这些疲倦到极点地人倒下歇息。东倒西歪地卸马,饮水,领补发的东西。等弄来油布、葛帐和一些粮食,飞鸟已靠了棵白杨树快要睡着。陈绍武注意到远处有几个人过来,居中是个颇有威武气的军官,便连忙推一推他。
此时,以前的军士已连忙挺身站起,见到对方先合手相抵,推抱行礼,小声的提醒一旁的各位大爷:“快站起来!”但赵过几个却仍没什么反应,都看着过来的人憨笑、傻笑、愣笑。
这也算他们进入真正军营地一种表达,但来人并不会理解。
“这就是你们的兵尉大人!”先行一步的督衣老兵,大声地喊,“起肃!”
兵尉不过是豆子大的小官。我却是将军,飞鸟心想。他刚睁了睁眼,就看到一双长筒靴子站在面前,正要表示半句客气,就已挨了一脚,刚抬过头,又是一脚。
周围的人吵扰,有人过来给他打灰揉肉,但还是点燃他的心头火。这与不同从前,身旁要么是自己要震住的靖康军官,要么是以崇拜眼神望自己的弟兄,尤其是在近来的焦虑让人脾气渐暴下。他感受到羞辱,摁了一把站起来,看着面前笔挺的年青军官和动手的督兵,一声不吭就去拔刀。但在对方略秀气的面孔上闪过一丝惧色后,还是忍住并制止旁人。
军官喷着吐沫,看看飞鸟的身材和样子,挑中了他凶恶地大训:“无论何等情况下,你们都是王国之军人,不可对军令懈怠!当奋发忠勇,报效陛下。”
赵过一口吐在地上,立刻冷冷地还了一句:“滚!来打仗的还是来唱戏的?!”
新兵尉不禁一愣。随即有个军官也爱睬不睬地说:“别理他。肯定是太学里的候补!”
他说的话是很有道理。从底层爬起来的军官都知道,溃兵中即使不论许多有低级军衔的,也都是失去直属长官的军士。他们未必甘心受命。若老军人来,要么和里面的军官联络感情,要么不热不冷地编制,等着别人巴结,甚至区分对待。只有刚提上来地。没有相处经验的军官,才迫不及待地想着立威。
这个威可不是说立就能立起来的,不是没有过叱咤风云的将军因战败后弹压不当而被杀的例子。此时,和他们呆在一起的其它溃兵也都笑笑咧咧,随即“去”了一声,不管他的狂吠,各干各的了。
而那被遗留在原地的兵尉军官像只大公鸡一样涨红了脸,看督兵也无奈,只好在事过境迁后打嗓门里吼“尔敢”。
飞鸟睡意没了,又迫切地要知道自己阿爸会不会带军在此。等他们一走就拉了赵过,上马往外走。他们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在各色旗帜下地营地旁张望。从横路里走到最末,又从南往北,也没看到父亲的军旗。
两骑重新回到白杨树下,谛听着风叶交拍而发地“簌簌”作响,他用手小心地摸过自己脸上的疙瘩,预想着见到父亲时那暖人心房的一刻。但仍感受到一种奇酸。刹那间,他黯然地想: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就让千军万马踩过我们的尸体吧,这是一个勇士的归属,也是向祖国地一种交代。此时,他自己也百思不解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悲观,原因是厌倦,崩塌,矛盾,自责?还是因这阴郁成灰苍苍色的夏日和这场两难战争?
渐渐地。他终于明白过来,这其实是自己在心底里营造出的悲壮遭遇,带有一种对杀身成仁境界的追寻和憧憬,便在心底里说:“阿爸!你可以看看我的马刀,这刀刃卷了又卷。而我也越长越大!现在,离你对我的期望还远吗?”
他回过神来,看赵过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自己,突然想起他只有爷爷,是既没有“阿爸”又没有“阿妈”的,便从马上伸出胳膊。将人和马都并在一起。说:“我阿爸就是你阿爸,我阿妈就是你阿妈!”
※※※
夜里。飞鸟还美美地梦到父亲那儿不轻易的赞赏,又一次赖着不起,一醒来就听到协助兵尉编排的督兵大嗓子地喊声,便带着大兵二十三个人到指定空地。
打仗时期是没有早起操练,夜晚集合的训练要求的。外围站了不少来找笑料的军士围观。他们围成的圈子里,七八个人堆稀稀疏疏地保持间隔。有些人少的见飞鸟这一拨拔刺刺、凶悍悍地进场地,不自觉地退让到外,保持出距离。
这个卒满额在即,带了个家兵站在人前的那个兵尉把胳膊抱得很低,但仅仅是为了把带点颤抖的两手压在臂下而已。
飞鸟很不愿意让他这样一个新兵站在自己这“将军”头上,便大大咧咧地叉着腰,站在最前面,歪着头很看对方,眼神里带满挑衅和敌视。
赵过几个找到他面朝的方向,很快围上来,指指点点地怂恿。马里得晚了一步,只好强拉硬挤,跑到飞鸟身边“呵呵”傻笑,回头给兄弟议论说:“看他那熊样,脸白嫩嫩的,一指头能弹破。是不?!看,硬是连毛都没长出来。”
飞鸟敏感地咽了口吐沫,慌忙去摸自己的胡子,见入手有绒毛感,放心了不少,心里却说:“这家伙乱放炮。是我往上一站的话,他敢这么说,下来就掰他的牙!”
新兵尉见人来齐,接受自己从家带出来的人鼓励,头颈僵硬地走到人跟前,把眼睛看在这群人后。他喝道:“我姓杨!是你们——”可话到一半,嗓子变得尖啃,说不下去了。
下头立刻有人嘈扰,出洋相一样粗声接话:“杨什么?!羊屎球?!”
见人群中起笑,督兵和扈从立刻上来,厉声叫那个接话地人出来。两声问过,却真有人应声出来。飞鸟等人转头,却看到一个胳膊缠布的大汉。
他敞着怀,边走边甩褂子,口中怒骂道:“老子杀人如麻,是军功累至。他一个白脸后有何能耐,就不能问问他叫什么?碍你们球事?!”众人还记得刚才的声音,不难知道喊问的另有其人,他是出来架梁子的。
“认了吧。说不准人家去勾引夏侯老贼的闺女,弄了她的,仗都不用打了!”一个阴阳怪气的人跟着喊,“人家睡一觉——”
飞鸟笑脸一下消失,心肺的血脉被什么勾紧。他听到声音就在身边,便猛地转头,最后看准一个捏着嗓子的瘦个子,咬牙切齿地扑了上去,照准那人的下巴就是一拳。
人堆一下炸成一团。遭殃的连忙往一边跳,傻愣愣的只是看。反应过来的陈绍武提枪推赶人群。赵过赶过人隙,大脚狠狠地往下踩踹倒地的人头。张铁头惟恐天下不乱,嘎嘎就叫:“打吆!”
一转眼,二十几个打六七个的混战在圈子里“砰砰乓乓”。圈子外的人都把眼睛盯向杨兵尉和走出去挑衅的大汉,等他们这样的人制止。走出来的大汉感受到众人对他的期盼,便往人堆里乱踢几脚,不住地骂:“你们这群狗崽子,有本事向敌人撒!”
两个火速支援的督兵学着他去制止,大喊着“拉开他们!”,却很快把自己陷进去了。不少人都趁机在这些不打仗只抓人的兵上抓两把。
蜂蜜最招惹蝇虫,一声声“打架了”的沸腾声带动热闹的程度。有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