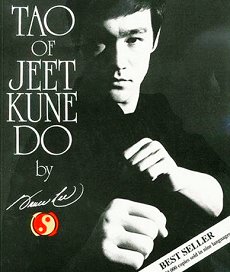Ϊ��֮��-��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ǵ����ૣ����������š�����
��û����������˵ʲô��ֻ������ѧ����������Ӹ���٣���ĸ��Ҫ����������ݹ���ȥ�����Ӹ�ǰ����ָ������ɫ�����ź�
Ľ�ݬb�������������ĸ��£���
����ʥ�¡�����˵������Сʱ����������ĸ�����������ͼ��������������ӡ����ү���ӣ��������ֵij��ˡ�����Ҫ�����ˣ���ȥ���ﻹԸ����
�����ͷ�����ѹ�ȡ�˸����ֽ������أ�������������������С�ֺ���Щ����˵�Ž��¼ӿ죬Ҳ��������ɡ��ֱֱ���ߵ���ͷȥ�ˡ�
����������˵ƣ�����ͣ�ˣ��λƵĵƹ�����ѩ���裬ĭ�����˿ڱ����ꡣ�������֣����ߵij��俰���ϵ������ϡ�����æ������ɡ��ȥ������ͷ�������������£���Ҳһ��ȥ�����Ƴ�������Ժ�����ǵ���ʲô��ͬ����
�������£�����Ҳ����������ˮ���������������һ�ͷ����ͨ�����֣��������š���
Ľ�ݬb�������֣��������˵��̫¡���ˣ�Ū�ô�Ҷ������ڡ�����ô���ĵ�ȥ�����˷�ͻ�������
�������ǣ�������̨�ף�����ҡҡ�λεģ��������ѣ���������ϸ���¡���
���������ļ�ͷ�����������ķ���ѹ��������Щ�����мܲ�ס���ҿ�����ǰ���֣����������˿�������ͷ�����ˣ���æ�����ݼ����ȥ���嵽����������������Ѭ���㣬Ҳ�����ˡ��������������µ����ϵİ����ӡ�����������̧��ľͰ���������ź����Լû��ʲô���ˣ��㸣������������ЪϢ�ɣ�ѧ�������ˡ���
�����ڹ�ñ����������Ļ�����̬��ת������Ƴ���������һ˫�ۣ����������ʱ�����������ˡ���û˵ʲô��������������Ƥ�������Ӻܲ��ͷ���
����������С�Ӷ�������������ģ�������ֲ����������ˡ����²����ٶ����ʶ��Ĺ�ȥ�����ӣ��������������ϵݡ������ˣ���������������ü���������̡���
Ľ�ݬb�и�ϰ�ߣ�ϲ�����̵Ŀ�ˮ���̳������������֡�������ǰ��֪����������Թæȥ������ͭ���ӣ�������������һ���衣��ֻ���ݽ�ȥ����ʱ�̵����������졣�����÷��������߹�����Ǹ����ʹ�������������Ĵ����ã��Ȼ���̫ѧ��ͺ��ˡ���������ͷ����Ӳ��ͷƤ���°��ף��Կ�Ҳֻ��������ˡ�
�ֽ��ʵ�����ǰ��ʱ������ð�����������ı��������ġ������ľ���ս��������������ǿ�������¾��ӹ������������������ݽ�ס�ˣ�����ض����������ϡ�Ȼ����վ�������������ǡ�����������һ�£�������Ҫ�����ˣ�����˵һǧһ������������ź���ˡ�����ѧ�����ֲ����������Ѿͷ��ȥ�������������£���������Ĺ���ң�ԭ�������˱��ּ��ߵľ���Ŷԣ����ڵ��ã���Ҫ�����ϴ����ɣ�
���������������������ģ��ղŵ��¼�Ȼ����л��Ů���ߣ��������Ǽ�����Т�ĵ�ʱ�����ˡ���������������������ȥ��æ�����װ�����һ�ٴ�Ź֣������ͬ����ûʲô�������ò��űܻ���ô��ɣ�̫ѧ����ǧ���������ҳ�Ϊ���ҵ��ӵ�ֻ��ʮ��λ�����ӵ�ǰ�ĸ����ǵ�����һ�����ŵģ�л��Ů�ɼ�Ȼ�������У����ľ������ź�Ҳ��Ӧ�����������ӵı��ְ������Ҳ���������ô���ġ�
����Ŭ�����ɫ��������Ҳ�����������ˣ��ⵣһ���Ͱ�ˮͰ���˳�ȥ������û���ӣ����ŷ��ӵĸ첲Ų�������߱ߵ����������ϴ�ЪϢ�ɣ���̤�塭�������ȡ�����
���Ĵ���������������ˣ������ǿ��÷�Ҳ�ۡ�������·�ϻ�������������Ī���Ǿƺ��������ͷ�ˣ�������������Թ�Ǽ�����磬ֻ�ܹ����������֪��ù��������
���˺����Ľ�̤�����·��Dz����ˣ���֪ʲôʱ���ˡ�������˵ʵ������Ϊ�飬���������ߣ��Լ����㰫�ˣ���Ҳֻ�������ؿڡ�������û��������ֱȫ������Ų����ʹ�ž���Ŭ�������O����ɢ�ˣ���������������Ҳ�˲��á�������������Ҫ���������ˣ�
�����ӣ���̧̧�ȡ��������ļ�ͷ���������������죬�����ӻ��������������Դ���������˯���ˡ�
���п����ֻ������ȥ�������ȡ���֪��ͻȻʧ��ƽ�⣬����ǰ�Թ�����һ��������ת�����һ���������̰��ϡ�������ɽ�������ʵʵ����ѹ�������¡�
���������������Ĵ������������������Ҫ�����˿�����ô���ˣ�
��ʹ�����̵ľ�������������������������˿���������ݵı�Ϣ���ڶ��ϣ����������������㡭����
��������ɵ�ˣ��ֽŲ��ôӵ�������������������ǰ���ػ��˰��죬����û��Ҫ�ѹ����ļ���ų���һ���������ѵĺã����˷������Ρ��������ˣ��ٲ���С���ӡ�ƽ������ѹһѹ������ȥ��û�����ˣ�
�������Ƕ�ſ�ţ���ֻ�Ŵ��ڴ����⡣��̾�˿�����������ǰ������Ь������ת�����������һ���ʻ�ҫ�۵���ס��������Ǽ���η�ģ�����Ҳ���ҷ����Ĵ������·����߶�ͣ��һ�����������¡�̫ѧ�����հݿ��ϣ�����������Ҫ����Ȼ�����ء�
����������Ƥ������ڽ�̤�ϰ�������Щ�����Ϲ������������ھ��¡��������̳������ˣ�ת������������Ҫ�˳�ȥ��ͻȻ����˵��������ʱ�����ҡ���
���ںڰ��ﻣ�ñ����������ڳ������úܣ��������dz����˵����ӡ�����ǰ����ô���£����̺����룬�ѵ���һ�����������ˣ���Ȼ���ˣ���ô�ֲ������������Ϊ�˱����ѿ�����Ӧ�ü�����Ĭ��ȥ������ӿ��ڣ���������ʱ�ˡ�
����תת�������Լ�Ū��ͷ�����͡����ŵ�������ҹ���͵ƿ������ڱ���������������������������ϡ�ͷ�����ˣ�ˮ�������������磬����ȥ�������ز��ζ����
�����������ˣ��������Ͱ͵�˵���е��Լ������ջ���һ�����̣�������Ҳ�л��㱡����˶���������ȥ�ѵ����ϡ���
��˵���أ�������ü�ģ�ɤ����Щ���ƣ������ҵ���ˮ������
������ȥ�죬��ͷһ�����������������Ǹ�����ˣ����о�ֹ��������������ֻ����ô��̫�����ˣ�����һǧ˫�۾������εģ����¶�����������ľ����Լ������˶̴���������̫����˼���������Ҳ������һ˲����Ц�Լ�ɵ���������Ȿ�����Ǹ����⣬��˵ʦ���縸���������˵��أ�����������֮����ʲô�ɼƽϵģ�����˯��һҹ���ڶ���������ˡ�
�����ű�յ��ȥ�����������������ϣ�����������û��ķԸ���ѧ����ͻ��Լ�����ȥ�ˡ�ʱ�����ˣ�������Щ���ðɣ���
�����Ź⣬��Ŀģ����Ľ�ݬb�����������ڰ��ְ������ˡ�
�������ŷ�ƣ������龰���˴�ɴ�������������������ȹ����̨�ף�վ�ھ����³�Թ��ȸ����ơ���־������Ѿ�˯���ˣ�����������ҹ�ź�
ѩ�µúܴ�һƬƬ�����Ƶģ��ּ����ܡ�����ס��££ͷ����Ժ���Ͻ����������Ӹ�����������ů�����������˷���ɡӵ����ȥ�ˡ�
�������ˮ���������������Ǹ�ģ�����¶ȡ���Լ���ŵü������������������ϧֻʣ�½��ϲ��ϵ�˿�ơ����ѱ��Ӹ��ڰ�ͷ�ϣ��պ��Լ�������ô�á�����һζ��Ȱ������ȴԽ��Խ���ѡ���ʵ��ʱ������һ���ܲ�������ϲû�ˣ�����Ҳû�ˡ��ѵú�Ϳ��������������˵ίʵ������á�
���ʮ�¡�����ʥ
����ô����Σ��������ੱ�Թ�ţ���û�й���������Ƶĸ�ǰ�̺�ģ�������µ�С��������������������ô��ֻ������һ���ˣ���
��������˵��ֱ�����ۣ���Ҳûʲô�������ѵþ�������Ҳ�������յ�������¡��Ȼ������ǣ�̫ѧ������Т���ǡ����ֺã��������Ŵ����أ���
��������������ȥ��������������Ӿͽж����﷿�ﱸ�˺�����ͳ������ü������ʳ�н������߲��˱ߵ���������ի������������ˣ���˵��ʱ��Ҫ�����ģ��������ϱ����ˣ�����Щ˯����
��������������Ҫ�η�ȥ���ͺͷ��Ӹ��˼١�û�������Ҳ˵Ҫȥ����������һ����������������ͷɥ���������Ӹ�ǰ������Ҳ�����ܣ���Ҳ��������ֻ��Ҫ������������
Ԫ�㵹�ܸ��ˣ����������ͬ�У���������飡�㻹��ʲô����
����ֻ���������ˣ��������㣬����ǵ�����ͣ����ȥ�����ˣ�������ü��һ�������Ц���������Ǻ���Ƕ����ֵ��������Ӣ���Ǹ����ŵģ�����ͷ���Ҽ��̻���ĸ�ף������������ε����ӣ��ܽ������⣡��
Ԫ�㺦������������ü�٣���Ů������˵����ˣ��㻹��Ц�������㣡��
����ֱ�ֵ���ͷȥ�ˣ��������������ڶ����ſںdz⣬�����С�У�������ͳ��������ʰ����Щ���ã����������������ָ��Ŵ�������������Ů��ҲЪ�Űɣ�����Ҫ����ġ���
����Ӧ���ǣ������������͵ơ�
�����첻��Ԫ��������������������ǰҪ��ԡ�����Ƕ����ľ��أ���ð��ۻ������š��������Ϳ�����Dz��������������Ѿ�����ԡͰ������ӣ�ϴͷ�����������˰��ʱ�������ꡣ��ԡ��ʱ���Ѿ�����ʱ��������������û���������´�ȥ�밲��һ�¼���ʲô�Ƶġ������������ˣ�ʪͷ���ýʹ���һ纾��ܳ�ȥ�������ں��漱�ô�У���Ƥ���۶����ţ����˺�Ҫ�����ģ��ȵȡ�����
������˵��ˣ�ֻΨ�ַ�����Ҫ�����ˡ�����û��ţ�Ҫ�������˹�ȥ���������ˣ���ô�������أ��������ﲻ��ɳ�������ٲ���һͨ���䡣
�����������û�н�����������ȹ��һ·���Ƚ���ʱ����ͷԺ���Ѿ����ˡ������������������������˵����ϵ�ѩ������������ȥ����
�����Ѿ������ˣ�����Ҫ�����ţ����˼����ؾ������ѡ��°ķ����������࣬û��ƽ����������Ҳ������˿�Ĺ��У�����ƽ�����鲼�ϡ����غ���Ե�����źڶд���ͷ������������ͭ���������ϴ�һ˫��Ƥ�ѥ��ʵ�ں���ͨ��װ�磬���������ϣ���Ҳ��ò����������ƶ����ˣ����ֱ��һ������㡣
ֻ���������������ޱ�������������־壬�����������磿��
�����ұ�ף�������������ѧ������������ˡ���
����������һ�ۣ����������˰ɣ���Ϊ�㼱�Ҵҵ���������������죬Ҫ��ͷ��ġ�����������Ů������������ֽ�������ͷ���Լ�����¿���������ѩ�����°�����
��������̿��ǰ������ů����Щ��Ӧ����������һҹ�����Ǵ�ɨ���ġ��ҲŸվ�������ͷ��ѩ�����·���Ҳ����ˡ�����˵���ӻ��DZ�ȥ�ˣ������˶����ӣ���һ��ײ����ô�ã���
����������Ц�⣬���������Ҳ�ȥ�����û�о������Dz��ǣ���
�������£�æ�������֣������ǵģ�ѧ�������к����Ӳ��ܣ������и���ʧ��ѧ�����ﲻ�𡣡���Ȼ�����������ϵ��£��ܾ����е����Ρ�����Ҳ���ٶ��ԣ��Լ�ڨڨ��������
��˵Ҫȥ��û�˸�˵�����֡�����˺�ɩɩ�dz�����ʱ����Щ���ȣ�������ĺ��ᱧ����վ���������������ǰ�Ȼ��ģ��������������Ķ�����ѩ����֥������һ�㡣
����˿���Ľ�ݬb���ֿ�����������Ц�ʣ�����������Ҫһͬǰ��ô����
������ҲҪ���Ƴ����ľ��¡�������Ц������Ľ�ݬbһ������ѧ���ͷ����ϳ�����
Ľ�ݬb���˻��֣�������С�����ͷ����ϳ�����������ǰ����ů������ǰ���ӵ����������롣��
������ܳ�������һ������Ƿ����л�������ƴ�һ������л�л���ҵ����ζ����˸������������Ŵ��վ��һ�ԣ���Ҫ˵�Ƚ����ӣ�����Ľ�ݬbû�������ӣ�Ƴ����һ�۵�������ȥ����
������������Ҫ���ƴǾͳ��˲�ʶʱ��æǫ���ĸ����������ͷ��ӡ���
��̤�ߣ�������ȹ�°���С��Ҫ����ȥ��IJ����ס��ۿ���վ�����ȣ���������ͷ���˰ѡ��Ǵ�����������һ�ţ���Ȼ�����˵����ȣ����ȵ����ģ�����Ī���İ������ܹ鲻����˼��û�һ�ͷ��������˳�����������˲Ż����룬��ôû����ʱ����л�����������ղ�����С�����Ƶġ�
�����Ӵ��ڿ���������ǰ��һ��������λСɩ��Ҳ½�����ϸ��Ե��������ӻ����н�������ѩ����ͷС�˵㣬��Ҳͣ�ˡ��ܽ�ͭ��ҡҷ����������������������ص��������Եÿ�Զ���ɽˮ��������ס�ˣ�·�������б��ֻ¶�����ϰ�ؿݻơ������ų��ޣ�Χ�ӹι�ȥ��ʱ�����������˲ݼ��Ƭ��ѩ��
����˰



![[��]��Ӻ֮������](http://www.aaatxt.com/cover/2/28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