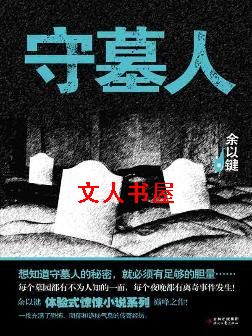守墓孤儿-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说春节已经到了,但在北方,冬季的寒冷可却远远没有说走的意思。过了春节再下暴雪,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再降个十度的温,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毕竟天不由人,老天爷可不会因为一个节日改变了自己一贯多变的姿态。
温倩走出去,环视着四周。四周再一次被银色的雪覆盖了,把这个复杂的世界都无情而简单地踏在自己的脚下。屋檐上挂着一根又一根像水晶一样的冰柱子;挺立在屋边的桃树向四周伸着它那苍劲有力的手,手指一抖,一簇雪就簌簌地落下来,在地面上堆出了一个环形的雪堆;墓碑上也披上了银装,在冬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温倩看到了远方忙碌的庄仲,走过去,说:“我来帮你吧。”
“不用,这是我本职工作,”庄仲微笑道:“话说你真能睡啊,这都快中午了。”
温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我都是很早起的。”
庄仲开起了玩笑:“口说无凭,谁知道你平时几点起,估计每天都是这个点吧。”
“才不是呢。”王雅撅撅嘴,看着庄仲把那片狼藉一点点地清理干净,连同前夜留下的积雪,全部送进了垃圾堆里。
“庄仲,”温倩突然喊起了他的名字,“我会记得你的。”
庄仲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但随即笑了笑,说:“我也会记得你的,温倩。”
“嗯,那……我先回去了啊。”温倩边说边弯下腰摸了摸钉子的头。钉子“喵喵”地叫着,抖动着它厚厚的毛,跑到庄仲身后趴着。
“那路上小心吧。”庄仲朝她挥了挥手。
温倩也朝庄仲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
庄仲目送她走出拐角处后,就拿起抹布,把每座墓碑上的雪都擦掉了。有时他真想变成照片上的人那样,无论烈日还是寒风,无论落雨还是覆雪,都表现出微笑的样子,而且永远都不会再变。
路过父母的墓碑时,庄仲没再停下脚步。
春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走到了每个人的身边:墓碑下的人、还有像庄仲这样墓碑外的人。收音机里的音乐也从往日伤感而怀旧的《再回首》变成了各种欢快闹新春的曲子——虽然这在庄仲听来并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小鸟从南方慢慢迁徙回来了,落在屋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但它们显然来早了,这里仅仅只有没有温度的阳光而已。
回想起以前在孤儿院过年的时候,阿姨们和院长都是加班加点陪着孩子们,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失去了一家团圆的暖景。每到初一的时候,厨房都会煮一大锅香喷喷的饺子,然后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围在一张张大桌前,每个人盛十几个,大家吃得有滋有味,开心至极。庄仲突然有回孤儿院看看的冲动,虽然好多年没有去已经有些忘记去那里的路,虽然去到那里可能也不会被允许进去,虽然想见的老院长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继续爱着孩子们……但是,他还是想去。
凭着记忆中的地名,庄仲问了十几次路,倒了四辆车,坐了快三个小时才到达那个模棱两可的地方。下了车,一阵失望袭上了庄仲的心头。这里的一景一物,没有一样是庄仲曾经熟悉的。在他的记忆中,孤儿院应该就坐落在这里,应该往前走五十米就是那熟悉的大门,那熟悉的小楼,那熟悉的院子和那熟悉的旗杆。然而,庄仲往前走了好几个五十米了,却没有看见他熟悉的一切。
突然,他的眼中闪现出一抹红色,那红色虽然常见,但是这是这附近和孤儿院唯一能联系到一起的东西了——国旗。庄仲循着国旗走过去,一下子惊呆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高楼挺立在国旗下面;院子里面虽然被雪覆盖着,但是却能清楚地看出那形状各异、各式各样的花坛;院子里面已经不是庄仲记忆中破旧的篮球架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院子和高楼旁边的一个标准的大足球场。庄仲觉得自己找错了,但是大门上写的明明是庄仲所熟悉的那所孤儿院的名字。
“你找谁?”有个人隔着大门问道。
庄仲还在他的惊异之中,依旧环视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孤儿院,甚至都没有看那个人一眼:“没……没什么,我就是来看看。”
那个人“哦”了一声,并没有离开,一直在这里和庄仲面对面地站着,直到庄仲直视了他。庄仲这才发现那个人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但那眼神并不像一个安全人员在盯着一名可疑的人士。然而,刚把眼睛移向那个人的庄仲却怎么都移不开了,因为映在他眼睛里面的分明是一个熟悉的身影,西装革履,拎着两盒糕点和一袋子水果。而他右手那残缺的手指显得格外显眼。
“你是……”庄仲呆呆地指着他,但是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好久不见了,那个天天在院子里听音乐的小子。”那个人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向保卫室里的保安示意了一下,门缓缓地开了,那依旧壮实的体形显现在庄仲的面前,只不过少了之前那让人头疼的攻击性了,现在更多的是沉着和稳重。
“你是……”庄仲依旧没有叫出来他的名字。
“我叫姜山,这个孤儿院的院长,”他依旧笑着,那笑让之前接触过他的人难以适应,“你们以前都叫我‘孩子王’,当然也就不知道我的名字了,庄仲。”
“你真的是……”庄仲不由得略带叹气般地笑了起来,他从来不相信人的后天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在,他相信了,他完完全全地相信了。
“进来吧,”姜山很礼貌地说,“虽然说这里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毕竟你在这儿生活了那么多年,而且你这一趟不能白来吧。”
庄仲走了进去,再一次踏入这片土地,他已没有了之前的感觉,大概是因为现在不受这里的庇佑了吧;或是物是人非,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而现在的他,只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这里参观罢了。
“姜山,你……”庄仲还是难掩心中的惊异。
“有些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要慢慢和你说,先进去看看吧。”姜山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庄仲进了那座楼里面。他们把这整个的楼从上到下地转了一遍,里面的情况和之前也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原来单调的绿色刷墙漆现在已经被一块块靓丽的瓷砖和卡通壁画代替了;原先头顶上老式罩灯和昏黄的灯泡现在已经变成了绚丽多彩、各式各样的小吊灯;寝室里面的床已经不是当时硬梆梆的木板床了,取而代之的是舒适的软垫床……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像家了。
“回想起咱之前在这里的生活,是不是感觉这里像天堂一样?”姜山看出了庄仲的惊异。
“倒没有那么夸张,”庄仲冲江山笑了笑,“不过的确比咱那时候好得不是一点半点。”
姜山笑着把庄仲领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那就是院长室了。院长室倒是不大,里面也只有一张床、一个满是档案的柜子、一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地上放着两个哑铃,墙上挂着各种卡通壁画,还有一块表。
“坐吧,别见外。”姜山一边摆好椅子,把手里面的糕点和水果放到桌子上,一边把烧水器的电钮打开。烧水器“嗡嗡”地响起来。
庄仲坐在椅子上,再一次端详了一下姜山:有些短的平头,一双带有笑意的眼睛,有些宽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镜,厚厚的嘴唇嘴角微微上扬,一件长款的西装下显出那依旧壮实的身躯,西装里面的衬衫上系着黑色的领带,笔挺的西裤下露出一双被擦得光亮的皮鞋。这装束看起来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会议似的。
“你穿得那么正式,一会儿有什么事吗?”庄仲问道。
“没什么事,你就呆着吧,晚去会儿也行。”姜山的话证实了庄仲的猜想。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那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啊。”庄仲站起身,推脱道。
姜山把庄仲按在座位上,板着脸说:“不把我当朋友是吗,虽然我那时候总欺负你们,但你信不信现在我也能给你来两拳?”他看了看庄仲,随后又笑了笑,说:“开玩笑的哈哈,坐吧,我真不着急,就是去拜个年,咱俩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庄仲见拗不过他,就坐下了。
“最近怎么样?是去上大学了吗,现在大几了?”虽然姜山只比庄仲大几岁,但是说话的口气却像是一个长辈。
“大四了……”庄仲回答得也像个晚辈一样。
“大四了啊,那今年就毕业了吧……怎么样,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找工作还是干什么?”姜山依旧像个长辈一样,问着庄仲的未来。
庄仲许久没有回答,一是他真的没有规划过毕业以后的事情,二是他对姜山还是有戒备之心,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毕竟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地专横跋扈,还是让那些阿姨坚信他以后“用来祸害社会”,庄仲不相信一个人会在这短短的几年改变这么多。
姜山见庄仲不说话,也就没有再往下问。烧水器“啪”地一声自动断电了。姜山站起身倒出两杯水,把其中一杯递给庄仲:“慢点儿,烫。”
庄仲接过水,说了一句“谢谢”,小咂了一口,就把水放到桌子上了。
“你近来的情况怎么样?”姜山坐在那舒服的椅子上,问道。庄仲就用寥寥数语把上学和最近住在墓园的前因后果大体说了一遍,仅仅说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就问起来到这之后最大的疑惑:“孤儿院……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怎么又成院长了呢?”
“你猜猜。”姜山开始卖起了关子。庄仲当然是没有什么兴趣猜他这关子,假装思考了一会儿,就以一句“不知道”收尾了。
“这些都是我捐的,”姜山眼神间透着一股自豪,就好像儿时把一个小朋友打翻在地时那种洋洋得意的那一瞬间,“我从孤儿院离开后就直接去找了工作,一开始因为我没有学历,而且脾气又暴躁、性格又不好,所以屡屡碰壁,就连持续时间最长的那一次工作也只是刚刚过实习期,刚转正就被开除了。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个家都没有,好像这个世界都没有我容身的地方……”
姜山说得有些伤感,好像他经历的那失意的一幕幕都浮现在他的眼前,连成一部加速放映的长电影,让他看得很别扭,很憋气。他看了看庄仲,问道:“还想往下听么?”庄仲点点头。姜山把眼睛垂下去,说:“我从来没和别人讲过我自己,但你例外,你是我离开孤儿院后见过的第一个故人,所以我想对你说说。说实话,能见到以前在孤儿院一起生活的你,我真的很高兴。我一直想和之前孤儿院的那些人联系,但是我那时做的那些事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害怕他们会看不起我、讨厌我,会怕我找他们的麻烦……今天你来了,我真的很高兴,真的……总之,欢迎回来!”
庄仲被他这一席话弄得有一些感动,也有一些愧疚。愧疚姜山可以这么信任他,把他当朋友,但是自己却不信任姜山。虽然过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姜山对庄仲的态度似乎就像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好兄弟一样。从进孤儿院的门到现在也就才有一个小时,姜山却已经要对庄仲说出他从未对其他人说过的事情。而最末那句“欢迎回来”让庄仲的毛孔不由得紧缩了一下,这种感觉就仿佛一个流浪在外很多年的游子回到了家乡,家里的人对他说“欢迎回来”的感觉一样,那样陌生,却无比温暖。
“那我接着说说我,”姜山开口打断了庄仲的感动,“后来我在社会上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我和他们每天喝酒、唱歌,甚至还在那里找过小姐,几个人折磨那一个人啊,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弄得她全身是伤,下体也因为我们酒后的没轻没重,流了不少血。当时正赶夏天,那个女孩转天早晨都虚脱了,但是她又害怕去医院——确切地说也没人愿意送她去医院,所以说只能就那么忍着。说实话,那时我突然觉得她可怜了,但是,我那些朋友一边骂着‘废物’,一边扔下应该付的钱就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沙发上一丝不挂地躺着,无力地哭。”
“三伏天啊,那女孩居然在发抖。”他用他那残缺的手拿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面前那还没凉的水,眼睛瞟向窗外,目光凝滞了一会儿。窗外的小鸟飞到了窗台,沐浴了一会儿那依旧没有什么温度的阳光,又一下子飞走了,在薄薄将融的雪上留下了一双清晰的脚印。
“后来我们又去了那,那女孩说那次之后她卧床了好几天,等到能下床了几天后感觉下体有异样,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告诉她,她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姜山用手托着下巴,看着庄仲,说:“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