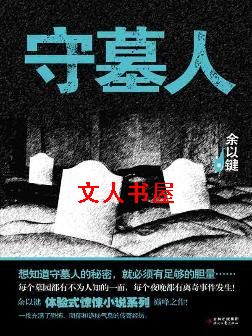守墓孤儿-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姚仲素
【由文,】
序
人生来的本性就是喜欢逃避的,逃避着困难,逃避着责任,甚至逃避着那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温存。然而,人生来又是喜欢自我批评与自我检讨的,于是又不停地检讨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逃避。但是,你远不用担心人们会因为自我检讨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因为人们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能力,那就是自我原谅,他们找着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来原谅自己,而后,慢慢地宽心。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只能说我也是在这个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轮回着,虽然了解这个循环的可笑与危险,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陷入它,然后,慢慢地被它所同化。
但下面这个故事却对这个循环给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我不敢说他们打破了、战胜了这个循环,但是,他们绝对改变了这个循环。我不会用一些华丽的词藻来为他们的故事添脂加粉,我只是想慢慢地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将给每一个需要对这个循环给一个解释的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北方,发生在拥有有“九河下稍”之称的海河的天津。这座城市虽然不像北京那样是政治的中心,也不像深圳那样拥有着发达的经济,更没有像昆明那样四季如春的气候,但是,这里的人却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极端的“盲目乐观性”。简而言之,就是几乎任何事情在这里都会被近乎以游戏的方式解决,即便这里充斥着让人难以接受的小市民,充斥着震耳欲聋的脏话与望而生厌的白眼。
然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却比较特殊。他——被我虚构出来的那个少年——是我的一个朋友,有着特殊的身世、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思维。他虽然是个生在天津的北方人,却有着南方人的温婉。
现在,请把时间分给我一些,让我把这个少年那两个月的一点一滴和他过去那些事情连同他身边的那些人一股脑地讲出来,就当做是喝完下午茶后无聊地躺在沙发上的一种消遣,抑或是满足一种急切于了解一个陌生人的**。
第一章 抉择
北方的雪景总是令人神往,然而你如果想去享受美景,就要有勇气去忍受严寒。
叶子在这个时候已是全军覆没了,即使是死皮赖脸不愿放开树枝的那些“钉子户”,此时此刻也不得不零落成泥。当然,北方的寒风也是催着这些钉子户搬迁的凶手——没有这风,有些叶子也不会愿意离开那供给着营养的母体,落到那冰冷的地面上。
在北方,有意思的是雪停了以后有可能还会立刻再下一场——那不是什么气旋带着什么什么的地理现象使得哪里有了第二次降雪,而是风——风将树上、房顶上的雪吹下来,从屋檐上、树上顺着寒风呼啸过的痕迹绕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圈,再缓缓地飘落到了地面,看起来像是老天又补了一场雪。
而雪地里的行人,也是极其值得一看:裹成球的路人;小心翼翼骑车的骑行族——不过雪下得大的时候那些看着有些落魄的骑行族大部分是用了牛劲推着手里的车,走着,倒着,站起着;雪后的孩子们好像在天堂里嬉戏的天使,那些被他们用顽皮的双手掀起的雪花好像在他们的背后组成了一对又一对如梵高的画一般抽象而美丽的翅膀,那圣洁的雪映着他们纯洁无瑕的心灵。
而在这些嬉戏的天使旁边,总会有一个人在静静地看着他们。他静静地、微笑地看着他们,流露出那种不知是平和还是羡慕的眼神。
他的名字叫庄仲,一个大学快毕业的学生,是个孤儿。
庄仲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那时候的庄仲对死亡的定义就仅仅是“以后永远都见不到了”。成为孤儿的庄仲没有其他的亲属,或是其他的亲属不愿意承认庄仲的存在——这在当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庄仲因此一直在孤儿院生活,不过,他天生独立的性格让他早早地离开了那里,他考上了当地的大学,闲暇时间还靠打工赚钱为自己谋生。而如今,庄仲差不多能过上一个正常大学生每天应过的生活。
庄仲喜欢这种下雪天,喜欢看雪地里的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喜欢把他们的童年融进自己的回忆中,好让自己童年原本痛苦的回忆消失得一干二净。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会到埋葬着自己的父母和那本应快乐的童年的墓园看一看。这片墓园建在郊外的山脚下,是庄仲的父母去世后父亲的同事张罗着把他们安置在这里的;景色很好,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看点,但嵌在这四季中的却一直是那些脸颊上布着阴云的人们。而这个冬季,这里仍旧白皑皑一片,林立的墓碑冰冷地卧在这惨白的世界中,一眼望去,眼中似乎满是被冻得发硬的石块硌到的感觉。这片雪地里偶尔会出现一些脚印,形形色色,但也都是稀稀拉拉的。
来墓园的并人不多,但每天都会有。庄仲父母的墓碑在这个墓园的深处,一个最冷清但却是整个墓园仅有的两座被半圈青松围绕的墓碑。庄仲其实很满意这个位置,他不想让父母再经历人世过分的喧嚣。而这片宁静,在他的眼里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来到父母的墓前,看着父亲和母亲墓碑上的照片——在他的记忆里,那两张面孔也只是二维空间里面那一动不动的“照片”而已了,原本那两张鲜活的容颜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悄悄地消失了,就像那被沙漠侵蚀的草原——这让庄仲感到无比的无奈与惋惜。
墓碑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是有人之前清理了一番,不然早就会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庄仲带着那习惯性的感激笑了笑,转身走到一间小屋前。这间小屋虽然小,但却是这个墓园最有烟火的地方。他试着朝屋子里面看了看,但屋内玻璃上的热气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到近处些许物品的轮廓。于是他又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应。他显得有些失望。
“你来了啊!”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庄仲兴奋地转过身,一个七十来岁、背微驼的老大爷站在他身后,须发已经差不多白了,戴着一副老花镜,身上穿着旧式的大棉袄。老大爷见到庄仲,立马笑了起来,皱纹瞬间变得更深了。
他姓薛,是这里的守墓人。
薛大爷一边走到门前一边笑着说:“刚才出去转了转。”说着就拿出钥匙开了门。两人走进屋,薛大爷慢慢弯下腰,拿起暖瓶,庄仲赶忙接过暖瓶,说:“我自己来吧。”他倒了两杯水,将其中一杯递到了薛大爷的手上,然后熟练地给地上的壶灌满水,做到炉子上。
薛大爷咂了一口水,问道:“放寒假了?”
庄仲一边应着,一边坐下来,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将眼镜上的水雾擦掉。四周的景物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一架摆满了书的书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台折断了天线的收音机和一架火炉——这一切从庄仲对这间屋子有印象的那一天开始就从没有改变过。
“您身体怎么样?”庄仲注意到了写字台上的一盒药,问道。
老人倒是显得很轻松,笑着说:“很好,挺硬朗!”
“那就好。”庄仲寒暄地应道。
这位老人在这里呆了很久了,从庄仲的父母去世时他就在这里,算算也有十来年了。这些年,老人帮了庄仲不少忙,虽然他工资不多,但是经常给庄仲买东西,帮助庄仲度过艰难的生活。而在庄仲失落、难过时,也是他,不厌其烦地鼓励着庄仲。小时候,每次庄仲父母的忌日或是逢鬼节时,薛大爷都会亲自去孤儿院接庄仲去墓园看他的父母,然后再不嫌麻烦地把他送回去。庄仲亲眼看着老人的背一天天地驼了,头发一天天地白了,而他虽然感激,但勉强维生的他却不知能为老人做些什么。每当想起这些,庄仲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也曾问过老人为什么他这么大岁数还要在这里工作,老人也只是笑笑,说些“老了也没事干”“儿子不肖”之类的话来回答。
一阵“吱”的响声打断了庄仲感激却又心酸的念想。庄仲起身将炉子上的水壶提起,灌进了暖瓶中,又把剩下的水倒进了老人的茶杯。
老人又和庄仲聊了几句,问了问他毕业的打算,未来的目标,甚至还开了几句“择偶标准”的玩笑。不过说实话,这些关于未来的问题庄仲一个都答不上来——一个孤儿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生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为未来打算。
如平常的例行谈话一般,庄仲在薛大爷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起身要走了。薛大爷也没有留他,扶着椅子,费力地站起身,和庄仲一起走出了门外。
门外的雪很厚,庄仲踩在上面,发出了踏实而清脆的响声。房顶的雪可能被庄仲那猛的一下推门惊到了,恐慌地滚落在庄仲的头上。
“您回去吧,”庄仲让道,“别冻出病来。”
“没事,硬朗着呢!”老人关上门,走入了雪地,脚下发出有些沉重的“嘎吱”声,虽踏实,但却失了清脆。
雪后的墓地十分美丽,但也勾起了人们悲伤的情绪。庄仲扶着老人走过一段路,前面是一条被雪覆盖的大道,就像一条通往生命尽头的河,河的左岸是生者的世界,喧闹而愉悦;河的右岸是死者的世界,安详而死寂。
老人将沿途墓碑上的雪仔细地擦拭掉,每擦完一块,老人脸上的轻松好想就多了一分。这一段路很短,但他们却走得很漫长,漫长得像走过了一个轮回。
快到路口了,庄仲马上就要走出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而老人却还要留在这里。
“一路顺风。”老人甩下一句话,然后转身往回走。
“您也慢些。”庄仲也抛下一句话,目送了老人一会儿,踏上了逃离的路。路两旁的树被风狠狠地吹着,树枝上的雪如同之前残喘在那里的树叶一样,也被狠狠地吹落了,再一次飘回到空中,享受那如同转世般短暂的自由。庄仲漫步在这雪地里,看着过往的行人,看着雪地里嬉戏的孩子。
这时,一条长队伍吹吹打打地从远方慢慢地踱过来了,队伍里的人们都穿着丧服,而那之中的白是让人敬而远之的白,而不是像雪那样供人欣赏和玩乐的白。路边玩耍的小孩子们也慢慢地看见这一行人,大概是受到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吧,现在无一例外地让开道路,凑成了一团,小声地议论纷纷。庄仲也站到了一边,看着这一个个悲伤或是强作悲伤的面孔闪过。队伍里面的有老人,有孩子。孩子少不更事,去世的人可能也是他的远亲,所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悲伤的表情,反而好奇地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时不时地发笑。
殡仪馆就在墓园附近,这一行人应该就是往那里去的。在殡仪馆进行一些繁琐的仪式之后,遗体就会被火化掉,之后殡仪馆会将骨灰盒交给亲属,让他们选择是墓葬、海葬还是其它比较特殊的方式。有些境况比较好的家庭会选择墓葬,境况不好或是比较开放的家庭会选择海葬,也有的家庭会把骨灰盒留起来。
吹吹打打的一行人慢慢地从庄仲面前踱过去,这时,队伍里面的那个小孩子指着墓园里面大声说:“妈妈你看,有个人躺在那里了!”
一名披麻戴孝的妇女回过头,瞪了孩子一眼,嘴里不知道嘟着什么,但眼神也不禁瞟进墓园。在当地,送路的时候是很忌讳回头看的,说是这会影响死者的轮回,当然,现实点是会遭到死者近亲的一顿臭骂。
然而,庄仲却意识到有些不妙,于是拨开人群回到墓园,看到雪白的地面上映着一团黑影——薛大爷蜷缩在那里。庄仲赶忙跑过去,看到老人紧锁着眉头,脸色蜡黄,右手紧紧地攥着衣角,呼吸也变得急促了。庄仲一面大声喊着周围的人,一面掏出手机,打了120。墓园里面热心的扫墓人也都围了过来,安慰着老人,有个大叔还把自己的外套披到了老人身上。
“您要撑住啊!”庄仲一面喊着,一面不知所措地将老人的外套裹紧了一点。
“药……药……”老人指了指胸前虚弱地说。
庄仲赶忙用手搜索着老人胸前的口袋,果然摸到了一个药罐,连忙倒出一粒送到了老人嘴里。
虽然这里算是郊区了,但救护车来得还算快,老人被抬上救护车,庄仲也上了车跟着去了医院。医院里里外外的人不少,但庄仲也顾不得留意那些人了,只是没头没脑地和一行的护士径直“撞”到了急诊室。不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老人是突发了心脏病,幸好送来得及时,吃的那粒药有效果,老人才没有了生命危险。庄仲按着老人的意思和一个电话号码联系了一下,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急切的声音。
“什么,他没事吧?”那个声音道。
“没事,医生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庄仲应道。
“那我现在马上过去!”说完电话那边就只有“滴滴”声了。
庄仲挂了电话,进病房看了看老人。老人躺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