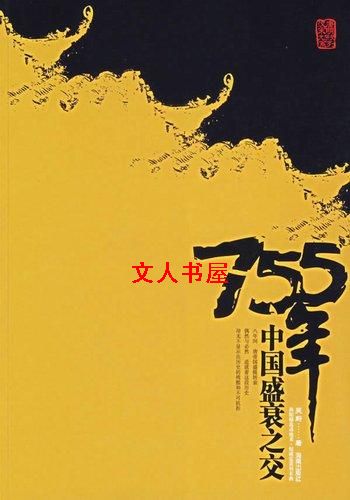七日一帝国盛宠-第1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亚国那里现在军阀林立,过省过境的手绪都相当麻烦,这次去我们损失了三个下属。好不容易终于将他们送回川省的芙蓉城,属下以为有那小叔照看,又加上那个功夫颇为不错还是华南姜家幺子的姜恺之在,小姐应该不会再有危难,便即刻赶回来了。”
说完后,久久没再回音。
十一郎却不知该再说些什么,想要安慰,便知词穷,那人真的已距十万八千里远,现在想必尽在家人呵护疼慰中,哪还有什么可说的。
突然,有疑声问,“你说,还有一个叫姜恺之”
“是,那个姜恺之似乎来头颇为不小。到达上海时,华北拥皇派的张系军阀正和华南这方刚刚成立国民政府姜氏一派谈判合力抗击左大将军的海军,局势非常混乱,公路和铁道都被其两派分割掌握,要离开非常困难。多亏了这个姜恺之,他大哥姜啸霖正是国民政府刚刚推选出来的大总统”
十一郎见男人眸色渐淡下去,似是真的放心了,便又宽慰道,“早前我们查到向兰溪也是姜啸霖的表弟,属下想,有他们二人在,便是战乱,小姐安全应是无虞”
男人慢慢垂下眼,唇角竟似弯了起来,低低笑了起来,“原来,那就是她念念不忘的恺之哥哥,难怪呵,正好,倒真是好竟然远涉重洋、不畏坚险来救未婚妻么?确实有胆量。呵呵向兰溪,他已经回国了罢?好,真是好呵呵呵”
“真不用担心了,有这两人,便是亚国也无人敢轻易伤她好,真好”
十一郎却觉得大大的不好了,听着男人沙哑嗓音里那愈发浓切的悲恸绝望,急唤着却不知该说什么,似乎说什么都不好。
男人哑哑地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自抑,笑到最后全身巅抖个不停,吓得十一郎大唤来人,笑声突然截止,男人俯身“哇”地喷出一口鲜血,便似止不住了般一汩汩地溢出唇角,溅得满壁血色,骇人不矣。
这一吐血,全是大惊动,明仁帝并四少全到了大牢来。
再见织田亚夫,竟是这等呕心沥血的凄厉场面,便是钢铁锤炼的男子汉,也不禁湿了眼眶。
对于某些事,也许男人们也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想戳破罢了。
明仁帝恼恨之下,命人开了牢笼,第一个便进了去。
“滚,你们通通都出去!”
哪料那倔傲的男人竟然又喝声斥骂催赶,不少“保光党”的人都以为皇帝至今不放织田亚夫,又不令其入院治疗,都是为了平息民怨,而事实上真正造成当前情形的却是织田亚夫自己。
自入牢后,他便拒绝他们的探视,除非必要的审讯,否则绝不见皇帝或其他好友。
这段时间,他面整日面壁而坐,饭食稀少,有时整日滴米不沾,简直可与古印度的苦行僧相较,或许于他来说,这便也是他一身罪孽应受的惩罚。
然而,不管再何自我折磨,心头总也存了一丝念想,关于那个人。
等了这许多日夜,终于得回些许消息,竟都是佳人已有归宿。这自是好消息,而听在他耳中,却是冷辣的嘲讽和斥笑。
织田亚夫啊织田亚夫,你果真是人人唾骂的禽兽,她离了你自是会有更幸福美好的未来,你算什么东西,你于她,从头到尾,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我对你只有恨,只有恨!
——你织田亚夫对我来说,从头到尾,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
——若恺之哥哥不嫌弃,我会嫁给他做妻子,生许多许多孩子。
男人笑着,鲜血不断涌出口中,溅湿了他往日面对的墙壁,上面似有用指印一笔一笔地写了什么,却都被他的血抹去。
最后,男人昏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明仁帝终于忍受不了,喝斥众人将人抬出了大牢,秘密送至医院中抢救治疗。
又两个月过去,果真人算不若天算,时局竟已翻天大变。
相较于两月前,全东晁都在为“光德亲王”是否应该斩首示众还是应该论病轻判争吵不迭,在其后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一连串来自于亚国的战事失利的消息,让整个东晁陷入了真正的信心危机。
亚国于半年前终于结束了长百千年的封建皇朝统治,进入无国无政府的一片军阀割据势力的夺权大战中,而殖民于亚国的诸国势力也被卷入了争霸战中,半年左右的拉距致使亚国整个国家几近崩溃,那些想要借机抢占更大地盘和经济利益的列强们也开始为无法调停的战乱头痛不矣。
对于喜好分权制之、邦国小治的西方人来说,他们自然无法理解这个东方大国传统思想里的渴望“大一统”的民族传统精神有多么强烈,这混战越打越没个尽头,对于从最初开始就只是渴望掠夺其经济物资资源的列强们来说,光打不产出那是十分不划算的,于是纷纷从最初支持其看好的军阀倒戈,要求尽快停战,恢复经济贸易,否则就不会再提供枪支弹药!
自然,这样的愿望也是亚国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这个契机,便出现在东晁远征舰队趁着亚国国内大战无暇顾及之时,占领了黄海上的几座岛屿,转而向距离最近的港口,素有东方之珠美称的上海一片地区发动攻击,意图登陆占领开始。
左大将军早就在占领黄海岛屿时,对上海垂涎三尺,妄图占领上海后赶走所有殖民列强,并以之为跳板,占领华南腹地南京——这个在亚国历史上曾为多个古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且在当前也是亚国十分重要的经济军事重镇,再以其为根据地逐步蚕食鲸吞整个亚国。
其野心之大,甚至狂妄宣称不下一月就能拿下上海。
这无疑让正在谈判不下的华北张系军阀和华南姜派国民政府产生了同仇敌忾的革命感情,当上海港口的古老炮台被击毁的那天开始,这两大军阀几乎是没再废多少唇舌,互让一步,达成了统一对外的协议,以淮河为界,南北各自为领,共同驱逐来犯的东晁舰队。
于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让诸国见识了团结起来便是一条龙的亚国人的强大力量。在颇有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海上喋血大战中,群策群力,以落后的老旧战舰加近海渔民们的小油轮,竟然将东晁最先进的远征舰队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
长崎,海边。
“左大将军下令撤退,但当时舰队被渔民自制弹打得慌了神,队型散乱,甚至慌不择路地跑进敌阵里送死。这都是左大将军狂妄自大,因打了一两场大战就轻敌所致
幸好南云将军临危不乱,夺得指挥权后,冷静下令,才将舰队损失降到最低,保住了一半以上的力量,退守回黄海岛屿上休养生息。那片海岛距离上海也仅一千海里,而亚国的舰船老旧,不可能驰行追击,这就给了我们舰队一个极好的重振旗鼓的机会!”
柏原康情绪颇为激昂,说着战况仿佛自己都身临其中,又是踢脚又是挥拳。
“对了,我还听说有个叫龙村治也的陆战军官在左大将军计划夺取上海的作战会议上,就提出了不可行性的反对意见。并且详细分析了远征军不熟悉敌军情势的弊端,可惜左大将军求功心切,丝毫不将亚**阀看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在不得不后辙时,这个军官虽是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却相当精明,在自己舰队陷入敌阵时,带着自己的下属竟然夺了一艘敌方老舰船,突破重围,追上了咱们大部队,真是太精彩了!”
他一跺脚,走到前方正坐在岩石上的男人身边,急道,“亚夫,现在正是你力挽狂澜的好时机啊!你倒是吱个声儿,咱们就求皇帝陛下让你入军,等立了这等大功,还怕恢复不了你光德亲王的爵号嘛!”
野田澈也上前,“是啊,亚夫,由你挂帅出战,我们都跟着你。”
清木义政笑言,“以民众对光德亲王的迷恋,只要亚夫打上一场胜仗,之前的倒光呼声就能消糜不少。”
然而,坐在岩石边的男人并没有应和朋友们激动的推举。
这急得柏原康团团转,又是指天又是立地的。
良久,男人终于开口,“不,现在不是我出去抢功的时候。”他看向好友之一,淡声道,“阿澈,该是你为国家效力的时候了,这个大帅,由你挂旗。阿康,你便做阿澈的保护者,千万别让野田家的三代单传绝了后。”
这话一出,男人们就闹开了。
“别说什么绝后,某人自己还没成亲,也不知这后在哪里!”
野田澈一出口,立即挨了白眼,住了口。紧张地看向前方的男人,现在众人都知道那道伤恐怕是男人心里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刺了。
似乎织田亚夫并不以为意,只道,“皇兄和诸大臣都知道,我到德国和荷兰游学时学的是商贸,并未学打仗作战,何来挂帅之说。阿澈,阿康,这是你们的机会,不要让我失望。”
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啊!
还有谁想说什么,却在男人再次调远的表情中,沉默下来。
也许,只是暂时不想再去碰触与那个人有关的一切罢!果真将军队开拨到她所在的土地,恐怕,会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
也许,人真的只能在经历过一些事后,才能学会畏惧。
东堂雅矢终于走上前,“亚夫,你的苦肉计应该适可而止了。要再这样下去,我们兄弟这辈子恐怕都没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织田亚夫转眸看来,目光一一掠过众人,“果你们真觉得内疚,那就助我把东晁拿下!”
众人闻言一惊,竟似都没想到他会此大口气。
清木义政说,“我以为,你会说要我们帮你拿下那个亚国。”
他低头,轻笑,“要拿下亚国,自然必须先拿下东晁,不是么!”
四张嘴大开,喝了满嘴冷风。
真不知道,被这样的男人爱上,到底是幸,亦或不幸?
不过他们很清楚的是,爱上这样的男人却不被爱,甚至被厌恶,那是比任何事都要凄惨绝望。
众人离开后,十一郎仍陪伴在男人身侧。
似乎又犹豫了好半晌,才叩身上前低声说了一句话:
“殿下,属下有私自作主,将小姐的大花包送了回去。”
男人远眺的目光微闪过一丝光芒,又很快沉寂下去,仿佛那抹明晰从未出现过。
三个月前,一艘开往亚国的英国油轮上。
轻悠在轻微的震荡中醒来,一睁眼便看到姜恺之担忧地看着她,随即便一笑,说肚子饿。
姜恺之像过往一样,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她下意识地躲了一下,他的动作僵了一下没有再揉她的头了。
吃过饭后,她说睡不着,他便给她读随身带的,这是她以前最喜欢缠着他做的事,他还给她讲国内的局势。
她听得有些走神,却又说不想睡,只想听他说话。
他心下甜暖却又酸涩,知道她撑着眼不睡,其实是怕又做噩梦,梦里哭着喊着的都是那个东晁男人的名字,那恨憎恨的字眼,听来让人惊心,可他却有一层说不出的深忧,为自己的情,更为她的心苦。
“轻悠,有一样东西,你或许可以看看。”
姜恺之犹豫了一下,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大花包。轻悠看到,果然眼眸一亮,立即伸手接了过去,比她之前叫饿接吃的还要快。一抹浅浅的苦笑从他唇角消失,这是他们上船后就在柜子里发现的,他自然认得这极具特色的包包是她平日爱背的,可他也记得很清楚,他们匆促逃离,她身上并没背任何包袱,这包又怎么会凭空出现在此。
可见她此欢欣就接了过去,也没问由来,他便也不提罢。
轻悠看着里面半熟不熟的工具,脸上的欣悦却渐渐变了色,但她不忍让旁人看出,仍是将心头倏然涌上的涩痛咽了下去。
“咦,我还以为里又装了一堆花纸片儿,原来还有一幅字画。”
“这个”
“不能看么?”
“不,不是的。”
“那就回家再看,时候不早,早些睡。”
姜恺之体贴地没有强求,将画放进包里,为她掖好被子,便拉上了帘幕。
夜静无人时,她偷偷拿出包,展开那幅画,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奇,那本就是她曾经亲手绘的樱花图。只是当她目光移到曾经由向兰溪题的字上时,目光却直直定住。
题着:
樱吹香浓粉靥轻盈笑婉约
雉雀啁啾声声你语轻盈
忙不迭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
真迹绝真心能给谁
同乘共飞耳旁欢语共几程
夕阳余晖你的羞怯似醉
摹本易写墨香未退与你同留余味
一行朱砂到底圈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