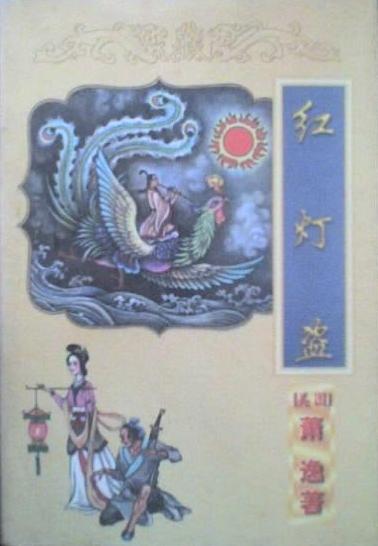红灯区的国王-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名警察此刻进了夜总会,径直冲鲁迪而来。他们要鲁迪跟他们走一趟——说得明白无误,但是彬彬有礼——也就是请他去警察局。
“是不是把人搞错了。”鲁迪没有把握。
但他马上得知是有人告发了他,原因是他打了人并且造成那人重伤。莎洛特和尤丽雅很担心,从厨房冲出来。鲁迪耸耸肩,跟随两位警察朝外走。他对尤丽雅不屑一顾。当他离开夜总会时,尤丽雅低声对莎洛特说:
“他这样待我,好像我是空气似的!”
莎洛特耸耸肩,冷漠。
“任何一种关系到了某个时候都是令人痛心的。”这是她总结漫长一生的经验之谈。
警官装出一副忧虑的表情。那个被鲁迪殴打的人颌骨骨折,住在阿尔托纳医院里。是他斗胆告发了鲁迪。
鲁迪咕哝:“这家伙这么快进了医院,这是他的事。我只在他头上浇了点香槟酒。他很放肆,后来揍了他一拳,那是明摆着的。”
“有两个证人,鲁迪。”警官遗憾地说,“很多人可能怕你,但这个人却不怕。”
鲁迪审视警官,感觉到对手在幸灾乐祸,毫不掩饰。警官手里终于攥住了把柄来对付这个圣保利大人物。
“我想,我得请一名优秀律师。”鲁迪·克朗佐夫说。
“得请一名出类拔萃的。”警官附和。
鲁迪至少在这时已明白,自己落入别人设下的陷阱了,犹如愚笨的黄口小儿被骗上当了。
奥尔嘉打电话约罗伯特吃晚饭,罗伯特很高兴。他期待着奥尔嘉再给他提一些有关夜总会被关闭的问题。他一门心思希望她这样做,因为他担心默尔岑有可能随时收回他的许诺。然而,当两个人在泰国小餐厅靠窗的桌边一落座,关闭夜总会就不再成为谈资了。电视台总编辑此前决定,至少不要为电视台节目谈这些。
“嗯,请原谅,对您,我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了。”奥尔嘉说,一边擦辣出来的眼泪,“天啊,真辣!”
“快吃干面包,”罗伯特催她,“这管用。”
奥尔嘉赶紧往嘴里塞了一片面包,略有止辣的作用。罗伯特觉得,奥尔嘉未施脂粉,其玉骨花颜也俊俏绝伦。
“我觉得您原来的打算很好。”他说,并且给她披露一个秘密,“存在着一线希望:我们可以暂时重新开业了。”
他给她看有关当局的文件。奥尔嘉微笑。
“可喜可贺,”她说,“咱们得庆祝庆祝!”她朝菜单匆匆一瞥,“我请客。这有点儿像工作会谈,一切由电视台付钱!”两人大笑。可是当罗伯特蓦然发现“三明治”保尔出现在对面街上的时候,那笑声就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三明治”保尔正朝他这边张望呢。两人目光相遇时,“三明治”保尔扮出怪脸笑,并且漫不经心地弹了弹帽子。这是在向罗伯特致意呢!罗伯特对此根本弄不明白,他怎么料到“三明治”保尔会注意他呢?
鲁迪要是脸色不悦,就最好别打扰他。“蓝香蕉”的住户全都知道这个,所以大家这时就让他静静地喝汤——此前米琦特意为他把汤热了一次。他要是想讲什么,就会边喝边讲出来。
苏加尔同他说悄悄话,告诉他,泰国舞女们每晚坚持要现金;服装裁缝催促卡琳结账;啤酒厂来电话催着要钱;新的音响设备首次付款的日期也到了。
“对一个赤条条的人,就不要再去掏他的腰包了。”鲁迪·克朗佐夫说,同时端起汤碗,把剩余的汤咕噜噜一口气喝下,然后起身,朝海伦大街走去。苏加尔尾随其后。
莎洛特摇头,抓抓胸口,又去抓烧酒瓶。她有些难受,从昨天首演起就一直难受。
“把烧酒瓶搁在这儿。”米琦伸手抓瓶子。
莎洛特把瓶子握得紧紧的。
“这没有用。”米琦嚷叫,郑重其事地夺下莎洛特手里的烧酒说,“咱们必须节约!”
外面,人们的夜间活动开始了。到处闪耀着霓虹灯,各酒馆和酒吧响起响亮的音乐,惟独“蓝香蕉”一片昏暗。
“你们得‘感谢’警察啊。”苏加尔对一群热衷夜生活的人吼叫,这些人太想看新的脱衣舞表演了。
鲁迪·克朗佐夫慢慢腾腾地朝罗莎丽的小摊儿走去。她太惨了!
“你想吃点什么?”罗莎丽问。
“来一杯啤酒。”
“给我也来一杯!”鲁迪身后响起这声音。原来是尤丽雅一面尴尬微笑,一面靠拢来。“看样子又是我在跟踪你了。你感到特别窝囊,是吧?”
“你就大大方方跟嘛。”鲁迪喝了一口。
“我一直想弄清,你为何突然要甩掉我。”她说话声音很响,以至于其他食客都有些好奇,调头看他们。
“也许我对于爱缺乏特殊的本领,”鲁迪自嘲,“这我知道。谈这个没有意思!”
但是她毫不退让:“我要知道这事。我要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不把我当回事了!”
“因为我是傻瓜,因为我每况愈下。你去找别人吧!”鲁迪闷闷不乐,把啤酒推回,转身到街上去了。
“我真要光火了。”
“我看出来了。”鲁迪怪笑。
“你以为你觉得合适,就可以随便蹂躏我?”她跟在他身后。
“你气鼓鼓的时候也是你最美的时候。”他说着就突然伫立不动了。
“唔,这还差不多,听起来舒坦。”尤丽雅闭上眼睛。
他抱住她,和她贴得紧紧的。她抓起他的手,并且将这手导入自己两腿之间。
“你想引诱我?”鲁迪不带感情Se彩地问。
()免费电子书下载
“我正好有此打算,”尤丽雅说,“就在这大街上,在对面黑暗的角落里。好,走吧!要么,在小摊点后面也行。以此相互道别,如何?你把我挤在墙上,咱们站着干。或者你取我身后体位,只要你喜欢;或者你仰面躺在台阶上,我坐在你身上,然后咱们一起进入高潮!”几个醉鬼狞笑,转头看他们。他突然吻她。“对,吻我吧,”她要求,“对,这样就好。我喜欢你吻我。”
鲁迪益发激动,把她顶在墙上。不料,尤丽雅抵抗起来,这真出乎意外。
“不,不要这样!我不要。”
“为什么突然变卦了?”鲁迪后退,气喘吁吁。
尤丽雅竭力恢复常态。
“我渴望这事,它使我激动。可事后你又对我反感,我岂不更加痛苦!”
他想吻她。
“别这样,”她说,“别老是对我亲热了。我可不是石头做的呀!”
“既然愿意在一起睡觉,为何不能再睡一次?”他嘀咕,不耐烦。
“可事后,事后呢?”她问,声音打颤。
“那好吧,”鲁迪说,“那我就再去喝酒了。”他放开她,意欲重新进小摊点,顺便说,“要是你明早肯陪我就好了。”
“上哪儿?”
“现在咱们只拿回临时营业执照,要有长期执照才行。你帮我吗?”
她抬眼凝视鲁迪。
“有时候我觉得你无限温存,以至于我害怕忘记了自我。”尤丽雅说罢,俄顷离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坐上鲁迪那辆旧车去法尔肯施泰因的高尔夫俱乐部。它位于汉堡西边。市府委员维廷在白天紧张工作之前总习惯在此打打高尔夫球。他们一上车,鲁迪就夸尤丽雅穿红色连衣裙漂亮。她的相貌将有助于再次获得长期营业执照,要紧的是她不能忘记给维廷频送秋波。
倘若这一招失败,鲁迪还有几条东方国家制造的昂贵地毯和一些一公斤装的鱼子罐头可送,当然不是白送,白送就有点贿赂的意味,那么就一公斤鱼子一百五十马克吧。维廷自然知道远不是这个价,他多少付一点,感觉会好一些。圣保利以外的世界全都这样,鲁迪怪笑。圣保利的人们知道要人的嗜好。当维廷瞧见尤丽雅时,眼睛瞪得像牛眼一般,把开球没有打好的懊恼马上吞到肚里了。
“您的千金小姐?”他挖苦地问。
鲁迪气得脸都变了形。
“可以想见,您对于崇拜者的冲击简直受不了。”维廷笑容可掬。
“我们有个问题,维廷先生。”鲁迪插话。维廷似乎置若罔闻。
“您成就了令人高兴的事,”维廷说罢转头问尤丽雅,“您在圣保利干什么工作?”
“跳舞。”她回答。
维廷欣然对她打量,但见她拥有芭蕾舞演员的优美身材。“在‘蓝香蕉’跳舞。”她又补了一句。
维廷的表情一下子冷却下来,一个跳脱衣舞的!这个,他没有估计到。她没有丝毫的鄙俗气,倒不乏闲雅与矜持,外表是多么迷惑人啊。维廷快步前行。
“眼下我们的营业执照出了问题。”鲁迪跟在他身后。
维廷不再注意他,而是继续打高尔夫。
“我又有廉价商品了,”鲁迪附带提了一下,“上等东方地毯,便宜得出奇。”
维廷把球打得又高又远。
“不需要,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都布置好了,一切陈列品都有了。我个人认为,这类地毯只能造成房间的不安定气氛。”维廷说。
()
“我明白了,”鲁迪含糊其辞,失望,“鱼子呢?白鲸鱼子酱呢?”
市府委员耸耸肩,表示遗憾。
“那是美食,”他说,“可惜医生严禁我吃,”他叹口气,“胆固醇太高。”
他又做出准备击球的动作。鲁迪茫然。蓦然,一只信封飞落在地上,鲁迪猫腰拾起递给维廷。维廷正想把信封塞进口袋——信封好像是从他口袋里落到地上的——岂料尤丽雅掺和进来说,不,她亲眼看见是鲁迪失落的。维廷似显恼怒。鲁迪给尤丽雅递眼色,一筹莫展。
尤丽雅感到自己做错了事,这时只好细声细气地补充说:“也许我看错了。”
“给,维廷先生。”鲁迪边说边把信封递给维廷。
维廷只是稍作迟疑便收下了,然后向尤丽雅微微鞠躬表示歉意,把鲁迪稍稍拖到一边,低语:“劳驾您帮个忙吧!”
鲁迪打量他,等候下文。维廷一直等到一个树丛挡住了其他高尔夫球员的目光才说出他的问题:一位女友——非常年轻、非常讨人喜欢的甜妞儿——离开他走了。
鲁迪设身处地能深切理解对方的痛楚。这老头儿深爱那妞儿,现在有失落感;自己年纪大了,对于别人这次新的挑衅无能为力,深感痛苦。可是,鲁迪怎么帮忙呢?
维廷清了清喉咙,问鲁迪:“难道你在圣保利就没有人际关系了吗?”鲁迪依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维廷欠身紧挨鲁迪说:“教训教训那个夺走小妞的无赖,让他懂得规矩。”他问,干这事要花多少钱?鲁迪的脸变得冷酷了。
“斩掉他几个手指头比割掉棒棒花钱少一些。”他冷冷地说,“您可以马上雇个杀手,杀手干起来得心应手。”
维廷呆望着,对方是在开玩笑吗?他心中十分不悦。
鲁迪气坏了,这位贪官把他当成什么人了?当成杀手?打手?仅仅因为他住在圣保利?维廷刚才对他要求的恰恰证明了,圣保利以外的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他一把夺回维廷手里的信封,说:“她说得对,这封信是我的!”
维廷还想指责什么,但鲁迪背过身去,怒斥维廷,骂他该舔他鲁迪的屁股,说罢就步履滞重地走开了。
“咱们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最亲爱的朋友!”维廷朝他嚷嚷,斥责他粗野。
尤丽雅听见责骂的声音,心里益发担心。两人会见的结果不是鲁迪所预期的那样。他气恼地从尤丽雅身边走过,后者紧紧相随。营业执照的事怎么办呢?一个相貌英俊、被日光浴晒得黝黑、常搞体育锻炼的四十来岁男子迎面朝她走来,并且突然驻足,十分惊讶。
“是尤丽雅吗?这简直不可能!”
她惊呆了,以至说不出一句话。这是真的吗?
“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吗?”他走近一些,样子很时髦,穿一件淡黄|色高尔夫毛衣。“我拐到这边来,看见你走了很长一段路!”
真的是克里斯托夫,她当时的慕尼黑男友,她的伟大之爱,堕胎婴儿的父亲。她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才逃到圣保利来的。
“你好吗?”克里斯托夫问。
“很好,”尤丽雅答道,“你呢?”她见他瘦了一些,“你在汉堡干啥?”
“找你呀!”
“不是真的!”她周围的世界全都下沉了,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是来接她的。
“附带也处理一点商务,”他微笑,顺便补充了一条来意,“但主要是找你,这么长时间你呆在哪里呀?”
难道他真的不明白,她之所以离开慕尼黑,就是为了摆脱他吗?他真的不知道,这事给她造成多大的痛苦吗?她把这些讲给他听,使得他很难堪。他推诿说是不幸的环境使然,他们俩从根本上讲颇为投合。天呀,他是多么惦念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