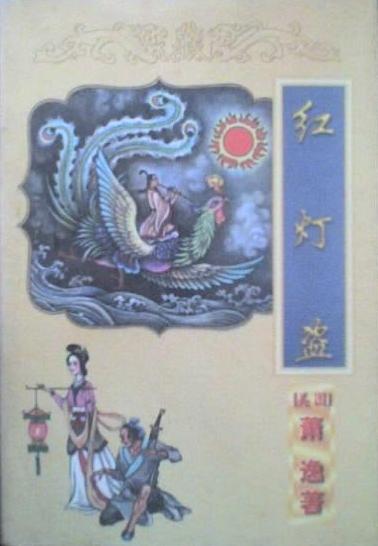红灯区的国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拉雅娜怪模怪样地笑了:“是呀——我很吃惊。您是有声望的律师——干这种事不正大光明吧,对吗?”
菲舍尔的声音骤然变了,变得冷冰冰:“谁也不能指责我们什么。”
秃顶的房管员从角落里的那张桌子瞥来毫无表情的目光。
“如果一切顺利,”菲舍尔继续说,“我们公司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您的份额——咱们就说定吧——百分之五?加上您的投资。”
拉雅娜凑近菲舍尔,他已能窥到她的领口里去了。“您估计,补偿费有多少?”
菲舍尔做了一个轻浮的手势:“三百万——大约吧①!”
①加点的词原文为英语。
拉雅娜对他凝视,无语。蕾吉娜笑道:“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会大吃一惊的!”
一辆出租车载着拉雅娜拐进海伦大街,这时天色已晚,马路上冷清了许多。只有几个醉鬼懒洋洋地站在夜总会的大门口,盯着一些不知疲倦地拉客的妓女看。一辆红色赛车急速地超过出租车,“嘎吱”一声煞车,停在“蓝香蕉”夜总会前。马克斯把钱塞给两名咯咯浪笑的女郎,急忙催她们下车。一位骑摩托车的警察显然是来指责他超速行驶的。他认出是马克斯,便立马招手道歉,旋即骑上摩托,呼啸而去了。马克斯狞笑着,目送那警察绝尘而去,说:“哈利路亚②!我们生活在金钱大行其道的城市里呀!”
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
他挡住刚刚下车的拉雅娜。后者避开他。
“真可恶!滚开!松手!最好还是关心你的那些小猫吧。”
马克斯紧随她来到“蓝香蕉”大门口。
“刚才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是谁?”
拉雅娜耸耸肩:“一个熟人。”
“他找你干嘛?”
“给我提供机会做生意。”
“什么生意?”
“生意就是生意。这是我的事。”
她要打开大门,马克斯挡住她。
“你如果要钱,就吱声。”
“我不需要你的钱。我挣我自己的。”
拉雅娜语气虽鄙夷不屑,却突然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开始合著夜总会传出的音乐节拍同他跳起舞来。尽管歌曲节奏很快,但两人跳得慢慢悠悠,温情脉脉。
“你跟踪我很久了吧?”她温柔耳语。
“我同某人在一起使你难受了吧?傻瓜,你!”
街上一个妓女瞅着这对情侣,颇有点嫉妒。拉雅娜尴尬地微笑着,对那妓女嚷嚷:
“你眼睛发直地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啊?”
她偎依,他紧搂。霎时间,马克斯突然怔住了:在隔着一幢楼房的地方,停着一辆没有开灯的豪华轿车。此刻驾驶室的门开了,司机“三明治”保尔下了车。马克斯惊惶,丢下拉雅娜,慢慢腾腾地朝奔驰车走去。左边的车窗玻璃被摇了下来。格拉夫坐在后座上。
“你陪维廷到‘阿芙洛狄蒂’去了吗?”父亲厉声问。
马克斯乱了方寸,但也十分恼火,好像当场被抓住的罪犯。
“你真会找麻烦。”他试图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内心感到极不舒服。
“你有年轻漂亮的老婆,还有孩子,为什么要怠慢自己的家庭呢?”
原来说的是这个。这老头儿还是这么个臭味儿。马克斯劈里啪啦地说道:“我老婆嘛,愚不可及,又不听话。”
“她可比你聪明。”格拉夫唧咕。
马克斯奸笑:“她对你这么重要,你就娶她嘛。这样我也就省去烦恼了,没完没了的烦恼!”
老头儿的话语变得冷峻了:“在你发火之后?上车吧!”
马克斯十分反感地遵从了父命。老头儿今天对他很和气,颇有点反常。就在这当口儿,老头儿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好呀,蠢货,你不想活啦?”老头儿这一下真的火了。马克斯心想,还是屈从为好,就说:“刚才是我发了火,请原谅。你也大可不必为这点小事像暴动一样!”
父子沉默,面面相觑,犹如打完第一个回合的斗士。马克斯实在难于控驭这种厌烦情绪:老头儿总是善于突然袭击,每次都令他火冒三丈。
“真浪费时间,小子,最好让我把你的脑浆‘吹’出一点来!”
在这种时刻,人们很难猜出老头儿说话到底是真是假。
马克斯做了个空口吞咽的动作:“别这样,爸!”
老头儿今天怒不可遏,最好别说话。“来,咂一咂这个吧!”老头儿强有力地挥动着上了膛的手枪。
马克斯感到手枪正贴着上唇,所以只好避免任何动作。父亲益发生气,挖苦,不依不饶。真危险,这已不是游戏,也不是什么“代沟”了。“要么,是把大炮塞进你屁眼里开炮?!”
马克斯面无血色,结巴着说:“可是,可是,我是你儿子呀。”他很懊恼自己每当这样的时刻说不出得体的话;有时,比如眼下,他觉得父亲不可理喻,又阴森可怖,这,他实在无法接受。
“你,不要脸的玩意儿,把嘴张开,让我对着你臭不可闻的嗓子眼儿开一枪?不许吭声,否则老子的手指就抠扳机了。想尝尝死的滋味吗?宁愿受折磨吗?”
“不,肯定不,爸!”
他感到自己哆嗦得像筛糠。这个老妖怪可是说到做到的。
“那就别再折磨你老婆!”
马克斯嗅出警报解除,就长舒了一口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老头儿对他审视良久,心里在捉摸着什么。“别忘了噢!”然后他藏起手枪,就好像那是一个公文包。
马克斯大口大口地吸气,双膝的哆嗦也渐趋平和,偷偷地用手摸了一下汗涔涔的上唇。今天这一关总算逃过来了。
拉雅娜虽然从远处没有完全听清父子的对话,但根据她看到的情况却能断定是父子反目!她像一只腾跃中的豹子看见这一场景,表面上毫无兴趣,实则随时准备伸出利爪出击。
格拉夫看看她,似在称誉:“多有魅力的女娃儿。属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一类,麻木不仁,只知伸手拽男人的棒棒,另一只手拿钱。”
奔驰车开走了,拉雅娜目送着车子远去。尽管她劝慰自己这些都无所谓,但马克斯不辞而别,就这么让她傻乎乎地立在马路上,还是伤了她的心。她极度气恼,在身后重重地关上房门。此时天色渐明,清扫车的声响已清晰可辨,城郊列车已朝四面八方开出。圣保利红灯区此刻方才入睡,媳灭了灯火,打烊。
数天后,在一个清晨,鲁迪·克朗佐夫坐在他那幢老房子的居室里,所有的窗户都关着,没有一丝流动的空气,令人气闷,这氛围造成神经紧张。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带皮鞘的旅行刀、一根钢质短棍和一把手枪,稍作迟疑后又放回原处。不,对他来说,用武器解决意见分歧和冲突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衰迈老朽的阿尔贝特·希尔歇出现在他身后的门里。此人是对面的房主,他的双手像铲煤的铲子,布满老茧和皱沟。他一辈子都在海港干重活,一幢多家合住的出租房成了他养老的依靠,靠可怜的房租为生。他是可靠的朋友,人们都很愿意同他喝酒。
“最好我同你一起去,”希尔歇说,“这种事你不能单枪匹马。”
“这种事”鲁迪还从未遇到过。他这是第一次不得不乞求债权人延期还钱。这就意味着一星期百分之十的高利贷。红灯区别的人已不相信他的诺言了,致使他告贷无门。这情况在以前从未有过!银行的小伙计打发他走,借口说分行行长一星期都不在。人们到处搪塞他,整个红灯区都知道:鲁迪·克朗佐夫还不起赌债了。
他与希尔歇外出时在走廊里遇到了拉雅娜。她穿着一件轻飘飘的衬衫,站在壁龛的电炉前煮咖啡。
“今晚你还得跳,知道了?”鲁迪·克朗佐夫咕哝道,还在她的屁股上亲切地拍了拍,“不能因为舞伴不争气就中止合同啊。”
“你得把那家伙塞到别处去!”拉雅娜匆匆走进她的房间。她对鲁迪·克朗佐夫颇为尊重,可是又不得不找个机会对他明说,她不想再跳了。她觉察到鲁迪突然出现在她身后,不觉一惊,便转过身来。
“几年前,我从大马路上把你要来,作为首席舞蹈演员在此登台,你不是很高兴的么。”他轻言细语。
拉雅娜浑身哆嗦:“那是以前,鲁迪!已经很久了。你在我身上大捞钱财。我并不欠你什么。”
她听见阿尔贝特在喊,他们必须快走,说偏偏在今晚迟到可不好。等到鲁迪无语地丢下她,转身同老友飞快地下了楼梯,她才倒吸一口气,如释重负。鲁迪对她比预期的要温和、体谅一些。
格拉夫每天早晨有个例行的碰头会,今天会上气氛有些紧张。原来是昨晚库尔德人在他的一个娱乐场所里争吵闹事。他气势汹汹地命令手下人把库尔德人的头头抓起来,并且说,要么是那个家伙尊重格拉夫所在地的警署,要么是格拉夫亲自把他的肠子掏出来。马克斯急不可待,自告奋勇要去揍烂那家伙的臭嘴,也好让父亲看看他是完全可以倚重的。可是,老头子只是冷冷地瞅瞅他。
“你还是关心关心我们的投资吧,去炒炒股。我需要的是金融顾问——有头脑的人——而不是打手。”
“打手”这个词他是用低声说出来的,语义双关。显然,马克斯在中餐馆打老婆的那一记耳光他仍旧没有忘怀。老头子不再瞧儿子,而是翻日历:“克朗佐夫何时还债?”
“耳语者”在他身边忙这忙那,殷勤服侍。“今天——谁都不给他贷款,他压力可大啦。”
格拉夫志得意满,朝“耳语者”点头,以示鼓励。“耳语者”在这天早晨请求格拉夫允许他陪同那个土耳其人与鲁迪·克朗佐夫会面,并且还可以允许鲁迪·克朗佐夫延期还钱。但样子还是要装的,一定要让他看出我们也不是不通人情;但是,倘若“色子鲁迪”到期仍无力偿还——这是求之不得的——那么,位于海伦大街的那幢老房子以及“蓝香蕉”夜总会就是格拉夫的了,也就是说,扩建“爱神中心”的道路上就不再存在障碍了。
在不见人影的停车场,“耳语者”上了一辆黑色吉普车。开车的是那个淡黄头发的男子。两人都戴反光的墨镜,彼此看不见眼睛:简直是没有灵魂的面孔。
“格拉夫不希望克朗佐夫老头碰到点啥?!”
淡黄头发的男子只是干笑,并且镇定自若,几乎被逗乐了:“耳语者”真是瞎操心,格拉夫同老克朗佐夫一样马上也得完蛋,此后,对他重要的是找个可靠的安身立命之处。
()好看的txt电子书
“耳语者”受到了感染,也怪模怪样地笑了。
“你同那个大个子陌生人谈过了?”
淡黄头发的男子打量他,不动声色。每个人的脸部都映在对方的太阳镜的镜片上。空气像凝固了。汽车排出的废气真难闻。“那个陌生人希望淹死克朗佐夫。”
阿尔贝特·希尔歇与鲁迪这时来到静悄悄的海港码头。那辆旧车停在水边。这地方是老渔港的一部分,远离汉堡的经济脉搏,是陡峭而破旧的码头堤岸的终端。听不到叉式装卸机的鸣响,惟有几只海鸥发出尖厉的叫声。远处,可以隐约听见科尔布朗大桥上来往交通的嘈杂,大桥雄伟飞架,把海港和南面的工业区连接起来。
鲁迪·克朗佐夫深吸一口气,下车。前面远处有两个人倚在吉普车上。他们的形体在铅灰色天空的衬映下显得格外醒目。长时的寂静仅被海鸥的嘶哑叫声打断,它们在海港上空盘旋。
鲁迪·克朗佐夫先后向“耳语者”和淡黄头发的男子打招呼。他心乱如麻。这个人怎么来了呢?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耳语者”来谈判,而不是那个土耳其人?三人沿着海港堤岸走了几步,说话的声音很难听清。希尔歇下了车,听不清他们谈话的详细内容,只听见鲁迪·克朗佐夫的语气越来越激动。那两个人当中的说话者使劲儿摇头。
鲁迪不加理会,走到陡峭堤岸的最外沿。
“我会付钱的,可我在银行里至今没有找到人,请告诉梅默特,钱不会少他的,至迟下星期。”
“耳语者”的面孔扭曲了,可鄙地奸笑着。
“土耳其人马上要钱,”他说,“干脆把你的房子卖了吧!”
“我的天啊,我会搞到贷款的。真倒霉,可倒霉也不能卖‘蓝香蕉’呀!”
淡黄头发的男子上前一步。克朗佐夫益发情绪激烈:“明天我再试试,说话算数。”
“耳语者”根本不为所动:“钱到期该付了,拿来!”
“我的天呀,你们也得让我喘口气嘛!”
老头子背靠堤墙。
鲨鱼时代(二)
争吵愈益激化,各自申述理由,你来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