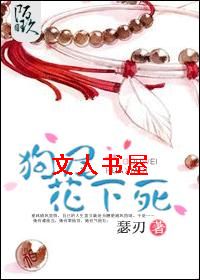一根狗尾巴草的浪漫-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路无语。
阿菊回忆那一眼时,这样说的,“古有飞鸽传书,现有眉目传情,这个世界,可真乱。”闹了个莫名其妙,黄卦对着我们抱歉,“前几天,学成语学疯了,”又拍了一下她的头,“不会说话别乱说。”我看着,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维护,竟有点羡慕,若红莲在旁,我也会对她极好。
寡然一笑,摸摸小姑娘被黄卦拍乱的发丝,“你们回去吧,天不早了。”
小姑娘乖巧地点点头,黄卦拉我至一旁,“今晚……若是以后没去处,就来找我们,住个两天没问题,包吃也管住。”
我点头,“晓得了。”他才放心地拉着阿菊,走向了岔路口。我背对着他们漫不尽心的摆摆手,催促他们快走,一想,这样的情景何其相似。
我说:“到了,明天见!”
然后等一等,等阿菊从我的黑云下飞到那朵红花下,对着我言笑晏晏:“今夜有雨,门窗关好,多加一**被子,万不可学我家少爷,只会给人添麻烦。”
“游子冶,也要替你家主子加一**被子,万不可学我家姑娘,虐待自家主子。”
“晓得了。”我背对着他们漫不尽心的摆摆手,催促他们快走。这二人郎有情,妾有意,终成眷属,老天爷也给了畅快晴天。不得不说,真好。
“笑够了?笑够了就去做你的事。”
这是我首次盯着他,没有丝毫退缩,“公子,小的十年寒窗苦读,十年寄人篱下,十年舍生忘死,如今,院考将至,厚积薄发,正是小的该做之事,怎能妄言其他?”
“哦,我是忘了,”他罕见的笑了,或为咕哝,或为嘲笑:“你卖身十年为奴,当初所求之事,不为葬父,却为读书,我当你有凌云的抱负,冲天的气概,一直携你一起,若不是五年前,我还真想不到……也不怪,有了十两银子,却让老父葬身乱坟岗,却使寡母做新娘,这样的忘恩负义,这样的狼子野心,是我眼拙,错看了你这只金凤凰,”他彭地推开大门,“你也看到了,这小小的病梅馆,栖不下你这只金凤凰,不如,您另寻住处?”
“小的不是什么好人,小的晓得,用不着您年年月月,日日夜夜,一刻不停地提醒小的!小的丢在乱坟岗的,是小的老父,人死如灯灭,再多繁华富贵装扮,灵堂也不过光鲜一时,小的不如省着这点钱…”
“省着十两银子,替你娘再找个人家是吧?”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娘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以前的事,难以张口,“公子,妄你还是读圣贤书之人,却张口闭口皆是龌蹉至极,劝你还是莫要张口,免得熏着旁人。”书生意气,总是忍不下那一口憋屈。
“见异思迁的婊 子!忘恩负义的小杂种!”
我想了好久,这一巴掌,我想了好久,这一巴掌,我想了十年,十年,十年那么久,也没有勇气,可终归是让别人替我打了去。夫子指尖颤抖,难得生气如此厉害,“说的什么话!你跟老子说的是什么话!白寅,你……你!你气死老子了!”
“别在这里充老子!我没老子,都死光了……”夫子又给了他一巴掌,打得来左右对称,红光满脸。这乱中,我还在想,越是平静越受不了伤害,越是躁怒越是疯狂。白寅,又犯病了。是否忘记,人皆有双面,白寅也无法例外,极度冷静似冰山,却又极度疯狂像火山。我想,我是笑了。
“死光了又怎样?!他没在你生命中出现过么?他少了你吃,少了你穿,少了给你的关爱?!他打了你,骂了你,还是赶你滚出这个家门?!艾宇有么?清年有么?”
两位先生自然没有。反而**着他,**成了这个样子。哈,给我一把刀,我要去磨磨他的肠子,看他是不是真的、肠硬肚肥?
☆、A14
白寅头疼得抱头蹲在地上,喃喃自语,“别说了,别说了。”夫子也蹲在地上,揽着他的肩,轻轻细语,“艾宇没有,清年没有,他们都没有。你有两个好父亲……”
“他们好?!”白寅近似癫狂,“我感觉不到!感觉不到!我的亲生父母,自私地生下了孩子,又怕成为他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千方百计的想要摆脱!我只是多余的那么一个,我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我的这两个好父亲,捡了我来,标榜着爱我的标准,却给了我满身的枷锁,你以为有了吃有了穿,不打不骂就是爱?你以为给买件衣服就是爱?!你以为没被赶出家门就是爱?!我告诉你,这不是!都不是!我要的,他们不想给,也给不起……”
“你说得对,他们不想给,也给不起。对他们来说,你只是延续了一个希望,却没延续血缘的脉搏,对你来说,你也从未真心把他们当做你的父亲,当做你的至亲。你们都只是双方的一个寄托。他们也许感觉到了你心里的苦楚,却没更多精力在意,可你知道他们在一起付出了多少,又耗费了多少光阴?”
“世间人只道故事的精彩,从未想过背后遭了多少罪!他们给不起你最多的爱,却又给了你更多的爱。你没感受到,是因为你的心里只有排斥,只有反感,哪怕他们死了,你念着的只是他们未对你付出多少,不曾想过,你又为他们付出了什么?”
“你没有!寅寅,我有没有说过,你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你要求着别人永远毫无保存的付出,却吝于自己的一分一毫!包括艾宇,包括清年,包括阿平,包括游子冶,包括我,包括你身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人你舍得付出过丁点儿!你只是只缩在壳里的乌龟,作出了厚厚的城墙,包裹着,伪装着,抵御着……你不信任,不相信别人。即便你在笑,你身体里流动的血,却是冷的。白寅,你是真心在笑么?白寅,你快乐么?”
“你快乐不起来!你自己锁死了自己,紧闭了那层丑陋、难看的龟壳!地球只有那么一点地儿,人口却像猪崽子那么能生,说句不好听的,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思考,哪有人毫无怨言陪你做着美梦,的确,身量在长高,面貌在成熟,可是你却是那么幼稚,你知道么?白寅,你知道么,你有那么的幼稚?”
公子彻底崩溃:“我不知道!我幼稚?那又是谁,为人长辈,却非要参与后辈的是是非非,为人主人,却顿顿为了一餐饭摇尾乞怜,为人夫子,却唱着童谣,拿着本破书‘脑筋急转弯’满大街转悠!轮不到你教训我,没那个资格!”
夫子沉默片刻,“人若时时刻刻像只炮筒,我倒认为是在演戏;又时时刻刻都在怜悯,我也认为是虚伪。你这般压抑不住,倒觉得实诚。至于你看不看得起我,这是我的生活,而你自己想走那条路,是你的生活,从今以后,我会尊重你……游子冶,把你的血给他吧。”
“嗯。”袖口滑出锐利的光芒,刺啦一声,血染的风采,可这把利器并非杀敌的宝刀,却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血流尽,一霎那,泄了气,白瓷盛着红汤,溢满了满室妖香。
“夫子,请您按住他。”乌青的嘴唇,乌青的眉眼,酱紫的脖颈,酱紫的手臂,绵软的青衣下,应是墨黑的大股,墨黑的脚底板。那双一向清明的眼,此时浑浊不堪,布满了红血丝,含混着千万只毒蝎子,蝎子伸出毒刺,不轻易近人,“滚。”
外强中干,犟驴,这人有些好笑,便是我所有的想法,嘲讽道,“公子,您病了,吃药吧。”
他也笑,“是药三分毒?你确定你给我吃的是药,不是毒?”
“是药非毒,是毒非药,二者总得占一样,公子,选吧。”
“药非药,毒非毒,我选的,你给的,谁是谁非,谁辨得清?”
“花非花,雾非舞,看清之时,幻灭之际。这红汤您喝了十年,是酒,是香,您辨不清?喝吧,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脸色突变,“滚!”黄斑似藤蔓,渐渐缠上了他的脖颈,绵软的青衣下,应是布满了黄疮,再等一步,黄疮流脓,再等一步,口吐唾沫,再等一步,全身抽搐,再等一步,他就……
“寅寅,别闹。喝吧。”姓艾之人皆是这般自私,维护着自己的一切,又引诱着他人的祭礼。满嘴仁义道德,到头来,这一碗红汤,也不由毒药变成了仙丹。白寅,这血的滋味,可好受?这病的滋味,可难过?这被报复的感觉,可享受?我多么想引吭高歌,却也只能在心里冷笑。我的血里养了药,可这药却救不了我自己,我替自己难过——生来做一件器皿的工具。
脖颈上的黄斑渐渐退却,面色逐渐恢复正常,被灌了含着血的药,他睡得这般安稳。我想,下一次,他更是学不会逞强,一定早早拿了刀,半夜摸进我的门房。取走一碗血,留下一条疤。交错纵横,好似树杈。然后他再逼着我抹掉,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喝过人血似的。
掀开灯罩,吹灭烛火,由内而外的发出一声轻叹,这人若是多那么几条手臂,又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犯得着,受这份罪。
你看,你已发现,我开起了玩笑。聪明人,我告诉你,这就是人性罪恶的一面,自己遭殃,还要拖着别人下水,才能心理平衡,才能觉得老天公平,才能……压抑魔障。
我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伟丈夫,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这是我的双面,无辜做着表象,欺骗世人,阴暗养着毒蛇,冷眼旁观,却又伺机咬上一口。你是否觉得反感?也许吧,我只是入味比较慢,一旦进了味,你也会喜欢上重口味。
有时,我憎恨此种情态,有时,我又恍然觉得,该更狠一点。既然不满这样貌似顺风顺水的航行,为何不淋漓畅快的倒行逆流,既然不逆流,为何又不安稳的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直至风口浪尖,引领潮流?我笑苟夫子,世间安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是迂腐,我这样的甚至谈不上迂腐,因为懦弱,丧失了参与生命的勇气,受不住任何批判,因为懦弱。
吹灭了蜡烛,掩上了窗户,拉上了房门,夫子在外等着我,我知道,我们需要一次倾谈。也许乏味,也许压抑,却不会喜悦,也不会欢欣,总之不会让人好受。看着我快乐,听着我悲伤,这就是故事。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这就是人。人,远比故事复杂。
他在唱歌,“……一曲怪异的乐曲在人世间降临,宛如水流以及风聚,或像簸谷的人扬谷时的模样,有节奏的摇转器具。形式已消失,唯有梦依旧,一张晚来的草稿图,遗忘的画布上,艺术家的成就,仅仅凭着记忆出现。石头上躲着一只焦躁的母狗,瞪着我们,满目怒火,抓紧时间从尸体上取回那肉,它刚放开,但仍想嗲……”
“您将在草地和鲜花下面安葬,在白骨间慢慢腐臭。然后,哦,我的美人!告诉那群虫,接吻般啃您的蛆子,我已保留,虽我的爱不再汇总,爱的形式及其本质。”
我不胜唏嘘,“这曲写得不错,望江楼的画舫姑娘一定爱唱。”
“波德莱尔恶之花,听说过腐尸么?”
我惶恐不安,“学生听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写的腐尸情态。夫子为何想起这事?”虽说有一些阴暗的心理,但从未做过亏心事,夫子这是要将我哪般?
“游子冶,我说你小子能别装了,算我求你了,行不?!”
我不甚惊慌,慌忙稽首,“学生不敢,夫子明见!”
“……你还记得本夫子第一天来这儿,是何样子,穿何种衣物,梳哪种发式,讲什么语言,如何与人沟通,用何物换取包子,且住在何处?”
我疑惑不已,也得如实相答,“夫子来此,模样…甚怪,”抬头望他,见无异样,续答,“衣不蔽体,发不胜巾,语焉不详,居无定所,换物以冥币,沟通以手势,唯有怪车一辆,叫骂不动,鞭策不动。时人鄙薄,丢汝之包,弃汝之衣,砸汝之车。须臾,汝着一身新衣,巧带冠帽,竟与常人无异,时人满意,尽赠汝美食,且使汝居病梅馆,后三年,巧知你有些许才华,并作学院先生。如今,已有七年。”
“十年,不长也不短,可我却完完全全变做了这个时代之人,新时代毫不可惜地抛弃了我,旧时代却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我,除了这个地方,我还能去哪儿呢?”
我更是不解,“夫子?”
“嗯?”他呆愣于旁,忽地笑靥如花,毛骨悚然,“……游子冶啊游子冶,你可知晓了本夫子所有的事,你说这夜黑风高时,放火…嗯哼?”周身起了三层鸡皮疙瘩,这嗯哼二字莫要随便说的好。
“冷?”他拔高些灯蕊,“火来了。”杯水车薪,无用功,我默然。
“哎呀呀,又冷笑了,被我逮着了吧?你小子就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往肚里塞,坦诚点不好么。”晓不得他什么时候倒上了两杯酒,喝得有些眩晕,起身欲走,却被拉住,“五花马,千金裘,与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冷么?喝酒啊,喝了酒,一醉解千愁。”言语中说不出的怅然。
嘴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