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x小姐-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情就这样一丝不差地发生了。她说,“哦,我们只躺在一起,仅此,她这样说,尽管她脱下了白色罩衫。你什么也没说,她试图把冰冷的脚移开但被你紧紧地钳住。
“唔“她说。
她仍旧要蜷缩起来。蜷缩,过一会儿再伸直,她终于停下来,确切地说,她不再动她的脚,你说她身上有种神秘的气质和气息,但她的性格要更丰富,更神秘,更复杂。
她低声说着话,或者说是讷喃,她讷喃道:“每天晚上,就我一个人,不像这样,像现在这样……我感到幸福——这是所谓幸福吗?我感到愉快。
“黑明”她抬高音调说,“这就够了,像现在这样”。
“放松,”她说。
你说,你真香,阿×。你抚摩她的头发,像过去一样,轻捏她的胳膊,似乎,幸福也在重复。
沉默片刻。
“哦,记住黑明,”
“记得”。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
“我也是。”
“唔,过了这么多年了,你看起来仍显得那么忧郁,而且有时还像个孩子,黑明”。
沉默。
第五部分无尽地抚摸
她重又抚摩你的脸颊,和一段时间来没有刮掉的胡髭——发出沙沙的杂音,你转过头,眼睛对着她,“我看不见你了”,她说,“距离这么近,我反而看不见你了。”她格格地笑起来,很轻——
“但我感觉得到,我喜欢你身上的气味。”
你说,把台灯关了吧。
“不,我想这么看看你,”继而她又说:“好吧。”
那么,在黑暗中。她稍稍蜷缩起来,她的脚开始变暖,她轻轻地呼吸着,热气扑到你脸上,房间里又黑又静,她说:“静”,她紧紧地将你抱住。又松开,她抚摩你的胸膛,“抚摩让人愉快,”她说,她细腻而温柔地抚摩,像温水一样流过你的胸膛。
她喜欢抚摸,一直是。
“你抚摸我呵,”她说。
静静地,抚摸,你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她的背,然后,不经意间你捏了捏她的胸,发现它们不如以前那样饱满。你试着触摸它们,你皱了一下眉头,眼前一片灰黯然。
她说:“是不是变小了,黑明?”
你什么也没说。
她说:“是了。”
她接着说,“我知道……我甚至已经不能湿润了,好像身体在收缩,整个失调了……”
她这样说,似乎觉着有些悲哀。然后,她不再作声,你一手抓着她的肩,另一只手立起来是不合适的,你抱紧她,同时把嘴唇贴上她的唇,她热乎乎的、柔软的舌头就分开了你的嘴唇。你心慌意乱,似乎为自己不能做得更专心而愠怒。
她仍旧抚摩着你的背,并轻轻地扭动着,你于是往下钻,迅速地解开她胸衣的暗扣,含住了她的胸。她的脚跟痉挛,双脚只好乱动,迫使她浑身发抖。
“别这样……”她讷喃道,“别这样,黑明……”
你没有回答,而是把头埋在她的锁骨间,随后又藏进她的腋窝里。欲望变得按奈不住的时候,你试探地摸到了一些滑腻腻、湿漉漉的地方,她不停地动着,蓦地,她莫名其妙的镇静下来:“唔,别这样,黑明……我们不要做好吗?”
她继续低低地说:“我们要纯净的爱……”,说着,她似乎哭了。她忍住了哭。她的胸脯紧靠你身上,仿佛在汹涌,在澎胀,似乎就要胀裂了。有一会儿,由于她的扭动,床铺被弄得唧唧喳喳作响。继续写下去:你用力地呼吸着,你的肺部膨胀起来。你茫然不知所措,抚摸她。抚摸。抚摸啊。无尽地抚摸。而整体在枉费心机地试图忘却其局部。那湿润的身体,貌似在休息,放松而超脱,表面上心不在焉的样子,其实是在呼喊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即:“我进去,不,完全地和阿×融合在一起!”但定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你把那令人作呕的内欲表演的中心情节埋藏在心灵深处。你的心绪逐渐归于平静。当那可怕的图像重新恢复稳定和清晰时,看到的已是罗曼蒂克式的拥抱了。你这时应轻描淡写地说,你搂住她,在他的嘴里攫取了她的舌头,一条柔软、饱满、肉感同时动个不停的舌头。她紧地抓住你,好像缆索突然就会断掉。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乌黑的夜空,你因而推断明天的天气不会太阴沉。屋里一片寂静,尽管她全身都在战粟,手臂颤抖得好像突然之间就要脱落下来。你因勃起而疼痛,事实上,此时没有什么比你所谓的“假正经”或“伪君子”倾向来指责你更令你自己开心的了。你甚至隔着衬衣数起她的肋骨来,或者是,你隔着衬衣数起自己的肋骨来。
她说:“是不是难受,黑明?”
突然,她向下滑去。
她滑下去了。
她含住了你嚣张的部分。轻揉,抚摩,吸吮,但它在她的口中胀得更加粗硕。她的头发落在你的肚脐上,摩挲着你的皮肤,在恍惚与缥渺间,你感到皮下的每一个细脆却在融化,并参加了一个古怪的阴谋。她从喉间输上来的热流,仿佛使的你的整个躯脱离了神经的支配。根据这些编织的情节,生活中慢慢地离你而去,心肌痉挛却越来越频繁,四肢的活动都慢了,就像幼稚的观众看到长长的纸卷。你叫着她的名字,阿×。但她说:“不行了……”。你说你想要她,你爱她。她说她知道,她摇摇头。你感到她在黑暗中摇摇头,她的头跌到在你的肚皮上,她说:“我弄不出来,我不会……黑明……”她似乎哭了。你的腹部被泪水濡湿。没有。你感她在发抖,就像感觉到她的牙齿碰到你那根东西上时你的颤抖一样。你将她揽进怀里,黑暗中,她说对不起呀黑明,你忍不住饮泣。我爱你,她说,但我们不要做爱。你臆想我,我属于你,她说,只有臆想的性是最纯洁的。她继续说,让我们在想象中来完成——使精神的爱终于摆脱阻拦它的顾虑。
想象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愉悦。在描述中,在幻象中精被力竭。她说:“对不起呀黑明,”她把脸紧贴在你的脸上,一切都朦胧而灰暗。她重复说对不起啊黑明,因为我爱你,爱,她强调说,而不是……。是结洁的爱。她将你搂紧,现在她紧挨着你并像高潮来临的一样战栗,你能听见她的心在左侧乳房下怦怦直跳。
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夏天,她不再动,躺平,腿伸直了紧挨在一起。她的头发蓬乱,你轻轻地抚摩并理直了。她把头靠在你的肩上,而你枕着她的手。她一直小声地说着话。
你必须虚构,你必须用形象来自我陶醉,你必须忍受接下去的情节并求助于神形分离的能力,你必须毫不怀疑你的脆弱并不深刻,你必须忘了你是谁。你是黑明,你听着她如梦幻般的低语,你在这本书中逐步出现在形象,同不偏不倚的别人眼中的你的形象遥相呼应,你说爱她,然后突然从内部猛烈发作——但绝没有一般人看色情影片时所抱有的那种纯粹的功力主义态度。你说你感到愉快,你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三类,但你突然说不下去了。而且停下来的一阵沉默暗示着你对一切冷静的否定。接下来你说,肉体清洁和心灵的自在无时无刻不在测定比例。没有,是她在不停地说,仿佛梦幻般的低语。你听着她说,并轻轻地拍着她的头想要让她入睡,结果你自己却睡着了。
第五部分寻思着要不要手淫一回
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不再提及,并且,大概今后也不会再提及。回到现在。
现在。我独自在书台前,在一屋子的黑暗中,闭目躺在椅背上。菲儿还没有回来,快两个月了,她总是这样:外出,演出。
她也不往我这里打电话,或者说几乎不打。
那台电话是哑了。白天我捶了几下,扔出窗外,又捡回来,我一路小跑下去,结果它摔坏了。我索性踹了两脚,沮丧的脸拉得很长。我差点喊叫起来,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我肯定会喊叫起来。
现在我闭目躺在这里,或者说歪斜在这里,头下枕着两个枕头,我寻思着要不要手淫一回,结果,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但很快我听见脑中两个声音在对话:
声音1:我为什么把屋里的灯都弄灭了?
声音2:我喜欢黑夜。
声音1:我为什么喜欢黑暗?
声音2:我不知道为什么。
声音1:我出了什么事?
声音2:我服了一药丸,刚刚睡着。
空白。
静谧在扩大,有时,在人们的谈话中会显得更静,这静谧裂开了缝,墙壁在缓缓地游移,做着准备从缝里溜出去的举动,我紧闭双眼,身子稍微颤抖了一下,在膀胱里的水荡起一圈波浪以后,又睁开眼睛,确定它有没有偷溜走。
自白:我现在变得很嫩,准备长出新芽来。
声音1:我为什么会长出新芽来?
声音2:因为我好像被剥了一层皮。
这就等于说我在消耗生命,写作,时间几乎停止,我也曾嫉妒别人生活的平静,但现在一些小毛、小病和完全能忍受的虚弱却足以打乱我的平静,我老了——我说:眼睛,脑袋瓜,肚子,腿,连下身都不中用了——一天我得跑十几趟卫生间,我有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连菲儿的鼻子或嘴巴是什么形状都再也回想不起来,尽管一股强烈的对她的眷恋之情在我心中升起,她,在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越来截止模糊的影子,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一尊塑像,我大概不知不觉地哭了……
我十分清楚菲儿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打开门,这一点我狠清楚,就像清楚现在是夜晚一样。今天白天,或者是昨天白天,受杂志之邀我到编辑部去了一趟。白天,在一个固定的时刻,一群夹着饭盒到工厂上班的男女急急地把公交车、电车挤满了,还有一些没挤上的在嚷嚷,而且自行车叮铃作响,悠忽而过。我挤上公交车,站着直打哈欠,想伸伸腰和腿,可怜的是车内连伸腿的地方也没有。天还阴沉沉的,像夜幕降临了一般,我的脸色略微变得苍白,但令我惊奇的是,我马上就平静了下来,因为有人从后面撞我的臂部。我注意到每张挤在一起的面孔看上去都很忧郁,仿佛都有一门子心思似的。这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
但我很难看到行人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影。我,从杂志社带回来的问题就是:写作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主义。我觉得我应该耸耸肩膀失望地离去,而不是让读者听我顽固地继续我那可笑无聊的独白——我的表述与“自我意识”的怪癖不相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懦弱就在于我从未吹嘘过我有什么能力和见地,尤其是当我张口发呆时,我只好用铅笔的两头写东西,我还不断地舔它们,咬它们,啃它们。但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虚假的描绘不过是一副只会谈情说爱的(或相反)的逼真的因而也是可鄙的形象。事实远非于此,我所努力的是我的生计,或者说,仅仅为了一吐为快就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更让人奚落挖苦,甚至把我的整个心掏给陌生人。哈哈,这只会招致伪君子们的冷嘲热讽品头论足和引起恶人们一片放肆的诅咒,而且,往往会幼稚地觉得愉悦。当然,这都是真话——我顽固地维持这种思蠢而又不幸的嗜好。写作。在瞎扯的过程中,甚至没来得及谈点笑料——这是可悲的,我在观众的眼里越来越不值钱。确实,这是在瞎扯,扯着扯着就扯到别处去了。我其实一直试图用巧妙的虚构设法让大伙儿上当,用挑衅的办法来掩盖我内心的空虚,同时,又为我的自相矛盾进行辩解。我现在好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人家眼里会是副什么样的可鄙嘴脸——这显然是在吹我的洞察力,但随着愈来愈多的废话的累加我在公众眼里就会形像大损,我从来不顾及们的尊贵的情绪,很可能树敌太多。我写什么?我应该写什么?我只好相信那句话:作家不是道德公务员。文字表露了一种生理需求,以致我完全控制不了它的产生,它由我而生,但又有点不受我的理智控制。这时有人发话了:“那谁……够啦!见鬼去吧。”不过请稍等一下,现在我正等着有人向我提出迫不及待的想提的问题呢——可是大话说在前面,我准让讽刺挖苦全都站不稳脚跟!注意:写到这里我已决计将男读者和女读者统统抛弃了——不过,在我走得更远之前,我不会变成一个卑鄙的不法牟利者。再重复一遍:现在我正等着你们向我提出你们想不及待的想提的若干问题。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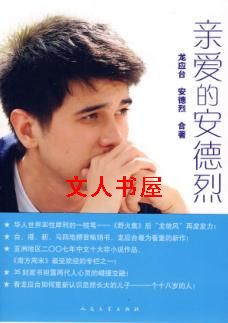


![[韩娱GD]我亲爱的小冤家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92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