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虚伪固执-第9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家缄默了。
打心儿里,她不同情弟弟,他这是自作自受。火车站毗连西陵湖,景色迷人,夏季里更是人们纳凉的好去处,然而那里又是一个是非之地,什么样的人都有,南来北往、中途转车的旅客,乞丐,小商小贩……全都云集在那里,是社会治安重点防范地段。他不会不知道吧!他干吗跑到那地方弹琴,这岂不是引火烧身吗!不单烧了自己还害得魏思林背了一身黑,自己也受到了牵连。好在大家都不吭声,默认了父亲的教诲,父亲火也发完了,气也消了,暂且不再追究了。
她担心,父亲执著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他不单会彻底查清小云和谁学琴,而且会追究谁帮他认识的魏思林?一旦查清楚,他会去公安局告发他,用下流歌曲,黄色音乐腐蚀,毒害青少年。
这一夜,她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着晚上发生的事,并联想到自己和魏思林。如果父亲知道她和魏思林……这怎么办?他是惩罚她,还是把事情闹到魏思林的单位?还是把她赶出家门,还是去找魏思林算账?一晚上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只能听天由命,任其发展。
第六部第八十一章
第二天上午9点钟,她打了一个电话给魏思林。电话是在距离家不远的小商店里打的。家里虽然有电话,但那是军用专线,是通过总机向外转接。电话只供父亲专用,并有记录。平时除了父亲,家里任何人不许向外打电话,只许接电话。如果遇到军区打来的公事电话,父亲不在家的话,谁接电话,谁要将姓名、家庭关系告诉总机,并记录在案。若是父亲打电话要外线,必须报出密码和姓名总机才会转接。
电话里,魏思林把约会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小时,把碰头地点改在西陵湖公园的南大门。至于什么原因,魏思林没说,她也没问。
西陵湖公园的南大门与西大门不同,南大门设在鸣山山腰处,没有城楼,只有门洞,分南面、西面两道城门。进了南门洞口,向东十几米,再进入西门洞口,穿过西门洞进入西陵湖公园。鸣山山峰、寺庙,离南大门西南面不足100米。西大门虽然只有一道城门,但有三个门洞口,城门洞上建有殿楼,显得城楼宽阔,气势宏伟。
她迟到了10分钟。她不是有意迟到,而是魏思林提前了一刻钟。
“今天你来的早吗?”她惊奇地问道。
魏思林笑了笑,说:“上次你来的早,让我内疚。今天特意早来表示一下歉意。”
她作了一个怪样子,然后挽着魏思林的胳膊走进西陵湖公园。他俩顺着阶梯下到湖边,来到近水的护堤边。护堤距离湖面高约40厘米;一排柳树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排列在湖边,一阵微风吹过,枝叶轻轻抚摸湖水,溅起阵阵浪花,好似推动船在航行。
树下有一长条石凳,紧挨着湖水。从阶梯往下望,能看见柳树枝叶却瞧不见树干和石凳子;下了阶梯临近湖水,隐隐约约可见到石凳子,枝叶时常遮掩石凳。
这里距离连接各洲岛的湖堤大道约200米,距离最近的洲岛约500米。从最近的湖堤大道了望这里,也只能瞧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人在做什么?
石凳子后面的阶梯上面是一条通往东大门的柏油马路,路不是十分的宽敞;路左边种植着蔷薇、冬青……右边是树林,穿过树林便是高大雄伟的古城墙。
从公园的南大门到东大门约两公里,一条柏油马路直线连接。东大门与南大门和西大门不同,南大门和西大门是整个城市的北大门和东大门,而东大门只是西陵湖公园的东大门,设在郊区,平时不开放,游客大多从南大门和西大门或者火车站乘船进入公园。从南大门进入公园的游客大都沿着湖堤大道前往各洲岛游览,除极少部分外地游客由于不熟悉环境,误入这条路,很快就会折返回去。这里大多是谈情说爱或者苟且的人云集的地方。
魏思林用报纸掸了掸凳子上的浮灰,把报纸分成两份铺在上面。
她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期待他的拥抱,亲吻。
魏思林被她灼热的眼睛诱惑的不能自持,血液一起涌向了心房。他情不自禁地把她拽到怀里,嘴唇贴着她的嘴唇,第一次隔着衬衣用手抚摸她那高耸的乳房,固定不动。她的身心沸腾起来,幸福地倒在他的怀抱里,任凭他抚摸,亲吻……
这时候,魏思林如果向她提出“性”要求,并要求发生性关系,她不会因为世俗之见或者父亲的存在,也不会顾及自己的声誉、前途和他揉成一个整块儿。
他俩相互亲吻,相互抚摸,相互拥抱,时间持续了大约10分钟。魏思林的手始终没有突破那道防线——手没有伸进衬衣内直接触摸她的乳房和肉体,而是固定在衬衣外面,静止不动。
“我漂亮吗?”她抬头问道。
魏思林点点头。
“你不要点头,你说出来嘛?”她央求道。
“漂亮。”魏思林终于说出她期待已久的话。
听到这句美好的词语,她感到无比的幸福,心都要醉了。她捧起他的脸孔拼命地亲吻起来,并把他的双手握着,不让他的手离开自己的乳房。
偶尔一阵疾风吹过,风将她那青色点缀着暗红花的裙子掀起,露出粉红色的内裤,着实诱人,迷人,让人见了春心动动。好在她躺在魏思林的怀里,裙子掀起时,他看不见里面诱人的景色。
“你知道上海人怎样谈恋爱吗?”魏思林抬起脸孔:“像这样一张石凳子在上海起码要坐两对情侣。这边一对,那边一对。”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怎么能坐两对人?这怎么谈恋爱啊?这边说话那边不是听得见,那边说话这边也能听见啊?”她不解地问道。
“他们谈恋爱的方法和技巧特别的高超,互不干扰。有时一张凳子能坐三对恋人。”
“他们怎么说话,怎样谈恋爱呢?”
“你猜猜看?”
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像这样子……”魏思林把脸颊靠近她的脸颊,低声问道:“你爱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声音像蚊子哼哼。
她频频点头,低声回答说:“我爱你!我愿意嫁给你!”嘴唇和嘴唇又粘在了一起。
“你知道为何这样子?”见她茫然的样子,魏思林笑了笑说:
“上海有三多,人多,高楼大厦多,街道多;另外有三少,公园少,住房少,谈恋爱的地方少。由于人口众多地方狭小,年轻人大都在外面谈恋爱。然而外面的天地也不宽敞,大家只能集中在一个地方谈情说爱。好在大家互不相识,这一对不认识那一对,那一对不认识这一对,你搂着我的腰,我靠着你的肩膀,低声细语,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把整个西陵湖全都搬去上海,未必能解决问题。”
“你看过上海人谈恋爱吗?”
“看过。一到晚上,上海的外滩就成了谈恋爱人的天地,石凳子、椅子,护堤墙边大多成了谈恋爱人的好去处。他们做出的举动是超前的。”
“警察不来干涉他们,不抓他们?”
“为什么要干涉他们,为什么要抓他们?”
“昨晚小云在火车站西陵湖弹琴被警察抓起来了。后来警察打电话到我爸爸单位把我爸爸叫到派出所,这才把小云领回家。”忽然,她想起昨晚发生的事。
“小云犯了什么错误?警察为何抓他?”魏思林不解地问道。
“说他唱黄色歌曲,扰乱社会治安。”她把警察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唱黄色歌曲?扰乱社会治安?”魏思林疑惑了。
“这是小云自作自受。他别处不去弹琴偏偏跑到火车站。那地方治安本来就混乱,警察不抓他,抓谁?”她抱怨道。
魏思林一声没吭。
“你在想什么?”她凝望他。
“我在想,我们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公共设施完善,人们生活水平、文化修养,自身素质较高,并有专供大家娱乐,休闲,弹琴唱歌的场所,你说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那样的话,小云也就不会去火车站弹琴唱歌了,不到火车站弹琴也就不会被嫌疑扰乱社会治安,警察也就不会抓他。其实,许多事都是受到时代的限制,这个时代是正确的,那个时代却是错误的,上个时代是错误的,下个时代可能又是正确的。”
“有道理。”他赞同道。
“我父亲可能会追查此事。”
“追查什么?”
“谁教小云吉它?谁介绍他认识你的?”
“你父亲怎么知道是我教他的琴?”
“是小云同学说的。不过,我父亲并不知道你名字,只知道叫魏什么林,在乐团工作。”
“这还叫做不知道啊!这下可好了,琴没学出名堂来,恶名却在外。”魏思林笑着说。
“我只是说可能追查,并没说一定。”她解释道。
“接下来怎么样?去公安局告我,说我腐蚀青少年,毒害青少年?”
“你怎么知道的?”她惊异地问道。
“你觉得奇怪吧,不可思议?我经历过。不出事便吧,出了事全是我的罪过。”
“这是世俗之见,一种偏见。”
魏思林摇摇手说:“不管世俗之见也好,偏见也好,在某些人眼里就是这么一个理。你说好,他说不好,你说没问题,他非说有问题,你说得清吗?”他停顿了一下,说:“上次在我家,不就这样吗!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一身清白,人家却怀疑你做了,不是照样把我抓进派出所,又奈何得了?告他,还是争一个理?我既不能告他,也不能争个理,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更没得理说。”
魏思林说得一点儿没错,那天,要不是她眩晕还不是和他一道被请进了派出所。自己的人格、名誉、清白,被无情地蹂躏,随意地践踏。我们的父母教育孩子为何不能坦诚地把自己恋爱时的经过细致地告诉儿女们?会不会激情似火,容易产生冲动?会不会相互亲吻,拥抱,抚摸?会不会性欲望?会不会发生性行为?愈是神秘——愈是好奇?愈是不说——愈是探究?所有的事情发生了——指责、漫骂;责任、罪过全都落在孩子头上。
这是为什么?
记得班上有一个女生,人长得又聪明又漂亮,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该女生和班里的一位男生谈恋爱,后来发生了性关系。事情被学校知道了,学校把他俩当作“坏的”典型在全校公开教育批判了一番。两人诚恳地悔过。然而学校折腾了人家一番,又把两人除名了。而另外一些做事隐蔽,同样做出苟且之事的男女生,照样好好的,丝毫没受到损伤。她觉得很不公正。年轻人年幼无知,处世浅薄,许多事情没经历过,应该给予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再说他们毕竟年轻又是谈恋爱,对待他们总不能比处理那些明知有老婆,有丈夫而暗地里偷欢调情,苟且的大人们苛刻吧!事实证明,年轻人所受到的惩罚要远远大于成年人,前者被自己所向往的学校开除了,而后者却只受到轻微地处分;前者永远失去了憧憬的学校,而后者却依旧在原单位工作。一个只不过没按照规定偷吃了属于自己的禁果;一个却是吃着碗里的偷着别人锅里的。谁应该受到指责和漫骂?谁应该承担责任和罪过?
就拿她来说,她躺在魏思林的怀里,他搂抱她,如醉如痴地亲吻,拥抱,抚摸……她并没觉得羞耻,难为情;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欢乐,无可比拟。打心儿里,她真切地希望能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时时刻刻如此。她要把整个灵魂,整个身躯全部奉献给魏思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是无私的,无回报的奉献。这种举动是错,还是对?是幼稚,还是成熟?是轻率,还是慎重……
忽然,她脱开魏思林的身体,把身子坐直,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大约一尺有余。她想尝试一下所谓正规的,成熟的,慎重的举动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魏思林见她半天没说话,以为她在想问题。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话啊?”她把头额向上一仰,妩媚地一笑。
“汤老师回来了,我的使命也结束了。我得把你原本地交还给他。你认为呢?”
她心里感到强烈地震撼,不过很快又平息了下来。她认为,他说得“送还”是指“教琴”。既然汤玉安回来了,他也该结束自己的使命,用不着再教她弹琴了,她应该回到汤玉安那里去学琴。其实,她心目中,今后由谁来教琴已无关重要,紧要的是她已赢得了魏思林的心,赢得了他的爱;她与他可以无所顾虑的交往,以后还要结合,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大快人心的呢。
“你是不是想抛掉我这个包袱?”她有意这么说,看看魏思林如何回答。
“不是。”魏思林起身,忽然他又将身体快速地弯了下来。原来有根树杈子正好横在他的头顶心,要不是他反应敏捷,那高大的身躯早就将头颅撞在低矮的柳树枝上。
她心里猛然一惊:“碰没碰到?”
“没有。幸亏让得快,要不然撞到头了。”魏思林笑了笑说。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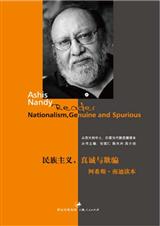

![[海贼]虚伪的暴徒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