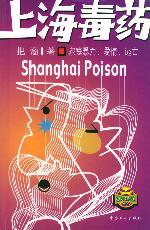香雪海-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我一定要看清楚她的相貌。”我非常固执。
赵三说:“那么下星期三,我在这里等你,你权充我的私人秘书。”
“荣幸之至。”
我目的已达,起身道别。
叮噹,叮噹去观卡通片了。
赵三会容忍他的女人去看动画片与学蜡染吗?叮噹并不适合他,享受是有尽头的,我一样有能力使叮唱的生活舒服,她既然没有更严重的虚荣心,何必跟赵三?
叮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郎。
我们约好在大酒店咖啡店等。
伊准时晃动着风姿的“马尾巴”来了,穿沙龙布的裤子,腰系印第安银束带,摩登如一幅新派画。
我替她叫一杯矿泉水。
“如何?戏可精彩?”
“太精彩了,”她拍拍胸口压惊,“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的戏。”
我扬起一道眉,“卡通片?”
“叫《银河铁道九九九》,这部戏足可看三次。其中有一段叙说未来世界的人已炼得金刚不坏之身,突破死亡之门,但是却活在无情无欲、冰冷的世界里,他们反而向往过去脆弱的躯体,留恋不已。大雄,真令人震惊,你想想,这暗示些什么?”
我微笑,“一一人们付出昂贵的代价,换取他们的理想,成功以后,随着而来的是失去自我,无限的寂寞。”
“呵,太棒了。”叮噹睁大眼睛。
“老天真,为这么肤浅的信息而兴奋。”
“肤浅?嘿。”她很气。
我拉拉她的马尾巴,“这种似是而非的哲理,这么容易便欺骗了你那敏感的心。”
她一怔,“咬文嚼字。”
“我刚见过赵三,同他学的。”我凝视她。
叮噹果然马上护着赵三,“他是好人。”
我点点头,“所以才怕他构成威胁,如果他是坏人,我怕什么?”
“关大雄,你也懂得怕?”叮噹哈哈大笑。
我瞪她,真乐,女人最高兴的时候,恐怕就是知道男人怕失去她的时候。
“你去找赵三干什么?”
“跟他去见香雪海。”
“呵,原来如此。”她点点头,“黑衣女叫香雪海。”
“纯粹好奇心。”
“省省吧,越描越黑。”
我说:“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可能再爱第二个女人。”
“你这么说,大雄,我很感动,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我绝不会为感情要死要活,你是自由的。”
“他妈的。”我骂,“我同你交心,你却嫌腥气。”
她仰起脸笑。
我们结帐,在街上散步,叮噹忽然说——
“香雪海这个女儿,是香企国跟一个女人在外国所生。那年香企国已经五十岁。”
我怔住,“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她耸耸肩膀,“为满足男友的好奇心,四处打听。”
我喜悦,“再说下去。”
“香雪海一直住在苏黎世,不与他们本家的人来往。”
我说:“赵世伯也这么说。”
“她三十二岁那年,香企国去世,将香港给她。”
“一一香港?”
“也不算夸张了,此地有什么事业背后没有香氏?人家一向处在幕后,不喜出风头而已。”
“那么说,她今年约三十三四岁。”我顿一顿,“结过婚没有?”
“没有,查不到资料。”
真没想到叮噹知道得比赵世伯还多。
“如今香氏可以改变作风,耀武扬威了。”我说。
叮噹摇摇头,“不,香雪海回来已有一两年,她并不喜招摇,你连碰她三次钉于,纯属巧合。”
“真的?”我不置信。
“有时候是你自己送上门去的,”叮噹呼出一口气,“像硬让赵三带你出席会议——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没有这样严重吧。”
叮噹不语。
“她是否非常非常有钱?”我问。
“那是不用说了,赵三以前说过一句话,那是:要上班工作的人,全部不算得有钱。还在挣,当然是不够,到够了,自然不再赚。”
“也许有人像你,叮噹,少少也认为足够?”
叮噹微笑,“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咄!从没有听过一个人如此赞美自己,文人的通病。”
叮噹说:“你应该知道我从不与其他文人来往。”
“文人相轻。”
我同她抬杠是抬定了。
有福气便抬一辈子。
见香雪海的日子愈近,我便愈兴奋,明知她也不过是一个女人,两只眼睛,一管鼻子,一张嘴巴,但是却还是止不住地投入。
会议时间九点半。
这说明她是一个能够早起的女人。
赵三说这例会三个月一次,商讨些行政策略,有关航业统战行动必须一致,是以行家与行家事前必须有默契。
我是他的秘书,并无发言机会。
到达会议室,我立即明白赵世伯的意思。
屋子全部窗都被封密,以人造光线代替。
现在一般的办公室流行以盆栽花卉装饰,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只备一张宽大的桃木桌子与相配的十二张椅子,除此之外,只余必须的纸笔烟灰缸等杂物。
一件装饰品都无。
墙壁上连画都没有。
多么诡异的办公室。有人把写字楼装修得似温室,也有人全套粉红,看上去像厕所洁具,口味各有不同,无可厚非。但这一间,坐久了就浑身不舒服,说简陋呢,家私明明名贵非凡,但却像处处告诉人:此非久留之地,故此一切从简。
不到十分钟,各路大亨纷纷驾到,分头坐下,留下首席,看来香雪海是今天的主角。
九时三十五分,全体人马到齐,独欠这个神秘的女子。
我很替在座诸君叫屈,全部年近古稀、身家过亿,有福不享,早早跑来巴巴地等待一个刁钻古怪的女人向他们发言。
我把脑袋晃了两晃。正在这个时候,大门一响,一个女子踏步进来。
我立时提起精神,发动眼部全体神经细胞,尽情吸收。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中等均匀的身材,颇见苗条,一身黑衣,不戴首饰,赵世伯可说得对,她长得并不漂亮,平凡的典型的东方面孔,平扁的五官,但是……。
但是赵世伯忘记提及她的眼睛,她的一双妙目不但晶光四射,而且蕴含着说不清的复杂感情,在短短数十秒内便看出阴晴不定。这样的眼睛衬在一张普通的面孔上、更显得突出。
我呆视她。
她的目光一扫会场,在主席位上坐下来。
不知为什么,她的黑发是湿的,更衬得皮肤有一种阴沉沉的白腻。她没有化妆,面孔与嘴唇都没有血色。
香雪海开口:“会议宣告开始,有话请说。”
声音也并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几乎每个发音正常的女人都有这样的声音一一甚至不是难听,沙哑喉咙有时候更见性格。
我大大的失望。
几次三番刁难我的女人,竟如此不起眼。
蛮以为她长得不美不打紧,至少要野性难驯,穿着皮衣皮裤进会场来,随时取出长鞭,响亮地在我们头顶“啪”的一声掠过。
我舒一口气,反高兴。
在座的大亨老翁们纷纷发言,我打算再坐十分钟便借故告退,刚预备打呵欠,忽然见到大门推开,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对在座诸人视若无睹,提着工具箱走到主席位旁,打开工具箱,取出一方白布,围在主席身上,大伙愕然而视,不知发生什么事,而那小子提起梳子与剪刀,竟然全神贯注地替香雪海修起头发来。
众哗然。
在开大会当儿修头发!
侮辱过于侮辱。
赵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只听得黑衣女说:“请继续发表意见。”若无其事的声调。
我想在她双眼中寻找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找不到。
房内刹那间肃静,只听得新潮少年运剪的声音。
怪异透顶。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什么益处?
赵三第一个打破沉默。
“香女士,如果你没有空,会议可以改期。”他的声音严峻。
香雪海答:“我不是没有空。”
“那么请理发匠出去。”赵三忍无可忍。
“他又不妨碍各位,何必出去。”
另一位会员说:“香女士,这是一次严肃的会议。”
香雪海那宝石似的眼珠,流动一下,微微地笑,“理发不是不正经的事,戚先生。”
又有一位中年人说:“香女士,一心不能两用。”
香雪海有点不耐烦,“各位何必固执,会议继续。”
赵三扬声说:“香女士,我退,待香女士精神略佳的时候,我再应召前来。”
他不待香氏答复,向我使一个眼色,我俩一起站起来。
这个叫香雪海的女人冷笑一声,“赵氏不顾损失?”
我忍无可忍,觉得应助赵氏一臂之力,便回一声冷笑,“赵氏损失得起!”
举座皆失色。
我与赵三开了会议室的门,拂袖而去。
我俩一直沉默,直到走在街上。
可爱的阳光炽热地沐浴在我们身上。
“恐怖的女人,”赵三喃喃曰,“就差没在额上凿字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不是我看不起女人,”我骂,“女人实在不是东西,十个有九个患权力狂,一点点抬头,便欺压别人,图做慈禧太后,目中无人,丧心病狂,女强人大半不可理喻,通通应该打三十大板,”补一句,“打在屁股上。”
赵三说:“真是心理变态,亏伊想得出,当众理发。”他闷闷不乐。
我也很挂心,“刚才她说到损失,会有什么损失?”
“失去一手资料的损失,你应知道现在做生意似打仗,情报准确,下手狠辣是八字真言,不过不怕,我们自然有办法应付。”
我摇头,“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哪一个不在本家呼么喝六,巴巴地跑到金玻璃大厦去受她的气。”
赵三莞尔,“活该是不是?有时也觉得很痛快。人到无求品自高,偏偏那些人那么有钱还那么贪,这么大的年纪还看不开。”
“人为财死。”我感叹。
“叮噹是正确的。”赵三说,“一个人穷其生,可以花得掉的钱是有限的。”
“别老把我未婚妻的名字挂在嘴边。”
“你们几时结婚?”赵三问。
“婚后我们打算生五个孩子,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你可知道生育教养五个孩子的费用?天文数字。”我补一句,“钱还是有用的。”
“替我问候她。”
“省得。”
叮噹说得对,这次的侮辱由我自招。
叮噹问我香雪海的真面目。
“除出一双眼睛,一无是处。”我说,“赵世伯是那种老式人,他看女人先要眉目姣好,样子甜,年纪轻,一团糯米似的,嘻嘻哈哈,毫无机心,所以他给香雪海零分。”
“你呢?”
“负六十。”
叮噹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本正经地说:“谁还见过沉鱼落雁的美人儿不成?心术不正,相由心生,就不好看。”
“你看你,费那么多功夫。”
“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把香雪海事件撇在脑后。
“比较金庸武侠小说中女主角之形象。”叮噹说,“很吃力。”
“真的?”我说。
“我画了一个图表,先将金庸笔下所有女主角的外貌及性格都详细列出来,非常的费劲,但异常的有趣。”
“是吗?反正你是天下第一闲人,几时做好给我瞧瞧。”
“才做了一小半,就发觉金庸笔下的美女首先要有雪白的皮肤,白得透明白得吹弹得破。”
“呵?新发现。”我有兴趣。
“略黑就成为次货。”
我忽然想起香雪海的肤色,白中透青,像博物馆中陈列的宋瓷,白得透明,应该是那个意思。
“此外就是要有一头长发。”叮噹笑,“越长越好,最妙是碰到地。”
香雪海的一头黑发……我回忆着,心中不禁一阵凉。聊斋志异中的女鬼,香雪海浑身就是带着这种诡秘的神态。
“……所以现代的女性,蓄短发,晒成太阳棕,全不合规格,不入流。”
我心不在焉,“你做妥这项研究,最要紧给我一份。”
“一一你在想什么?”叮噹问。
“没什么,我累了,一疲倦就心神不能集中,恍惚得很。”
“公司很忙?”
“公私两忙。”我说,“我想我们也该结婚了。”
“结婚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要筹备良久,我懒得很,提不起那个劲,最近我找到上海申报的一叠合订本,正在细细查阅,没时间。”
“三十年后,你是会后悔的。”
“后悔什么?”叮噹问,“余生晚也,只能在申报上看到阮玲玉出殡的情况?”
叮噹的嘴巴,谁够她来呢。
当夜我送她回家,在长沙发上看杂志,忽然觉得客厅太大太静,如果有三五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奔来奔去,大呼小叫,未免不是乐事。
小孩真值得同情,他们被生下来,历劫生老病死,不外只是为了令大人获得些乐趣。
然而也顾不得了,与众不同是行不通的。
花花公子杂志“啪”地落在地上。我朦胧地想:他们每年选出来的玩伴都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金长发、雪白的皮肤,长挑个儿,覆碗似的胸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