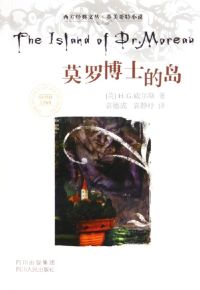两个博士-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我抓紧你,抓的牢牢的,不给你机会变心。'说完,我用力吻上他。
他热切的回吻我,迅速扯开我的睡衣,不等到卧室,就将我压倒在沙发上。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激烈的做爱,久到我适应不良,微微有些疼痛。激情过去,我趴在他身上,搂着他汗湿的躯体,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我怎么了?在刚刚被他充实之后,在紧紧抱着他的时候,我竟然感到空虚。我抬眼看他,他闭着眼,神色疲惫,好像要睡着了。此刻,我多想看他的眼睛,想找到新婚夜后那个清晨,在他眼中洋溢的爱和柔情。
'雷。'我推他。
'嗯?'他半睁睡眼,有一下没一下的撩着我的头发。
'你张开眼睛。''干吗?''看看我,我要你看看我。''看什么啊?你身上哪一块我没看过?'他将我拉上来一些,正好对着他的眼睛。没了,那满的即将溢出的温柔没了,剩下的只有淡然和习惯。甚至,也没有激情过后的波澜振荡,只有欲望满足之后的平静。
空虚之外,我又感到一阵悲哀。难道,这就是时间加筑在婚姻之上的必然结果?
分离
我答应了雷,要抓牢他,不给他机会变心,可是我竟不知道,怎样才叫抓牢他。我只能有空的时候给他打打电话,但通常,他都没时间接听,等他下了手术台给我回电的时候,我又忙的没时间了。一次次的错过,一次次的沉默,让我觉得无能为力。他的笑容变淡了,时常站在阳台上抽烟,一抽就是一整包,仿佛有无尽的心事。每当我想问的时候,他就露出那种缥缈如春风的笑容,恍惚的让我害怕,似乎,一旦我问出口,就会失去他了。我害怕,我好害怕,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样胆怯和懦弱。曾经,我因为好妻子的问题放弃过,沉默过,但那时我笃定我的做法是对的。而现在,我完全没有把握,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
德国新能源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函过来了,导师要带我和师弟王建设一起去。我在犹豫,这个时候离开,对我和雷会产生什么后果?
建设将申请表格放到我桌上,问:'听说你不打算去了?''可能吧,我还没有决定。'他急切的道:'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错过了,对你损失有多大你知道么?''我知道,可是,家里最近出了点问题,暂时离不开。''别傻了,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被家庭负累的女人。'我惊讶的看向他,建设对我一向尊重,今天为什么会说出这么没分寸的话?他坐在我对面,热切的望着我,我在他年轻热情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闪烁的东西,那种在雷眼睛里消失了很久,找不回来的东西。天啊!不会吧?建设!他是我的师弟,比我还小两岁,我一直拿他当弟弟般的照顾和爱护。我流产那次,还是他背着我去的医院,怎么会这样?
'池芮,'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不叫我师姐,'我知道我没什么资格说话,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关心你。从以前到现在,甚至今后,我都会一直默默的关心你。你为了你那个丈夫放弃这次机会,不值得,一千一万个不值得。''建设。'我急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他是我丈夫,他值得我为他放弃一切。'是,雷值得我为他放弃一切。当我喊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一丝犹豫,可为什么做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呢?
我仿佛一下子充满了力量,抓起表格来,冲到导师办公室,气喘吁吁的道:'导师,我不去德国了,让三师弟去吧。我有点急事,必须出去一下,您帮我向系主任请个假。'我抛下满脸不解的导师,一口气冲出校园,拦了车直奔雷的医院。我要去告诉他时间并不能冲淡我们的感情,告诉他有什么心事就坦白的说出来,告诉他我对他的爱永远不会退色。
我在门诊室没有找到雷,护士长告诉我,他可能在院子里。我满院子乱找,越过三三两两的病人和医护人员。我看到他了,同时也看到了站在他对面的女人,施医生。我兴冲冲的声音卡在喉咙里,脸上的笑容凝结。
雷的脸上是深沉的无奈和沉重的疲惫,却没了那晚的疏远。施医生的脸上带着希冀,紧紧的抓着他的手。我走近一些,听到雷沙哑无力的声音:'是,我承认,我的确对你动心。但是动心不等于变心,我不会对我的妻子变心,不会背叛她,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不等于背叛,你对她的爱已经消失了,你有权力寻找新的爱情,不能因为婚姻和承诺绑死自己。''不。'雷甩开她,声音更加苦涩:'我爱过,承诺过,就不可以改变。我对她的爱没有消失,只是被时间冲淡了,但是我依然爱她。我受你吸引,可是,那不是爱情。你很聪明,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分别。放弃吧,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不,我不会放弃。放心,我也不会逼你,我会等,等到你对她变淡的爱情消失,等到我对你的吸引变成爱情。'雷的脸苍白了,我的脸也苍白了。原来,他已经动心,否则那天晚上也不会把她带到家里;原来,他对我的爱已经淡了厌了;原来他死守着的只是对婚姻的承诺;原来,他不能承担的只是背叛的罪名。我悄悄的后退,悄悄的走开,狂奔而来的勇气在刹那间消失怠尽。我甚至不敢光明正大的出去质问他,指责他。何况,我要指责他什么?他并没有背叛我,他宁愿自己痛苦挣扎也不愿伤害我,他宁愿守着那退了色的爱情也不愿去寻找新的契机。这样的他,我还能指责什么?难道怨他对我的爱被时间冲淡了么?我呢?我又何尝不是?无奈啊!
我像一抹游魂在大街小巷游荡,也不知游荡了多久,最后还是回到家,回到那个没有人气,却是我唯一想要停留的地方。我蜷缩在沙发上,给系主任打了电话:'甘肃酒泉能源基地的技术支援,我去!'我忽略系主任惊讶的抽气声,直接挂了电话。我需要放逐,需要找个荒凉而安静的地方仔细的想一想。
午夜一点,雷回来了,打开柜子收拾东西。
我坐起来,呆呆的望着他,他要走了么?他终于决定背叛我了么?
他回头,表情依然温和,声音依然平静:'吵醒你了。我明天要到上海出差,凌晨的火车,先收拾下东西,不然怕来不及。'我冷冷的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了。''哦。'他看了下表,目光中有些心虚和愧疚。
我到浴室将他的洗漱用品包好,装在他公文包里,平静的道:'后天,我去酒泉。''酒泉?'他皱眉,'不是要到德国参加交流会么?酒泉那种荒凉的地方,去做什么?''放逐。'我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冷静,而我,需要一个荒凉的地方放逐。''小芮,'他一把攫住我,'你怎么了?''没怎么,'我痴痴的笑,'不过就是白天到你医院去了一趟罢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惊的不能动。
'雷。'我看着他的眼睛,诚恳的道:'分开一阵子,对我们来说,或许更好。'他的眼光突然暗淡了,缓缓放开我,默默的扣上公文包。
凌晨四点,他踏上南下的火车,36个小时之后,我登上西去的火车。
相思
坐在军用吉普车里,望着窗外漫天黄沙和茫茫戈壁,我突然发觉,我想雷,正确的说,从他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想他。以往我们也曾天南地北,两地分离,可是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思念他。因为我知道,当我回去的时候,他会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家里等我,或者我可以等到他。然而这次,什么都是未知。同来的小刘一直唧唧咋咋的跟接待人员宣传我的丰功伟绩,什么最年轻的副教授,什么主动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自愿来这里支援。我听的特别刺耳,我对感情的逃避,换得的就是这些虚名么?难道这些年来,我和雷牺牲了时间、爱情、婚姻、家庭,换来的就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称赞么?即便如此,我发现我还能够对着小刘和接待人员微笑。我的灵魂仿佛抽离躯壳,无论表面怎样满足,心灵依然空虚。雷应该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吧?所以,他对那个施医生动了心?
接连数日的风沙把我们阻隔在基地,根本没办法出门,我只有上网打发时间。卫星接收设备受风沙干扰,网络和通讯时好时坏,我已经把新闻都看烂了,QICQ挂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头亮。我起身倒了一杯热水,风似乎停了,透过脏兮兮的玻璃,隐约可以看到星光。我回到显示器前,永不放弃的头像居然亮了。我有一刻不知所措,他来了,这条断了五年多的线又连上了,该跟他说话么?说些什么?告诉他即将枯竭就是我,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刺探他的想法?
我正在犹豫,他的头像开始晃了。
'永不放弃:嗨,这么晚了还没睡?'
他的口气是那样熟稔,仿佛我们五年来没有断过联系。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迟疑,最终敲了下去。
'即将枯竭:嗯,睡不着。
永:我也是。'
我仿佛能够听到他的叹息声。
'即:为什么?有心事?'
良久,他那边才传回信息。
'永:相思难眠。'
我脑中轰然一响,相思难眠,我又何尝不是?只是,令他相思难眠的是谁?我还是她?
'即: :)什么人这么大的威力,可以令你相思难眠啊?'
我的手指不停颤抖,打出来的笑脸符号仿佛在哭。
'永:我妻子。'天!我感觉眼眶火辣辣的,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了。
'即:妻子有什么好相思的?回到家里不就能见到她了?
永:这一次,我无法确定,她会不会愿意在家里等我;我也无法确定,我能不能在家里等到她。
即:你们出现了危机?
永:对。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当你确定拥有什么的时候,会迷惑,会疲惫,会厌倦,会被其他东西吸引。当你即将失去的时候,突然就清醒了,才知道你曾经拥有的,就是你一辈子想要的。
即:你说的——是你的妻子?
永:是。还有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爱情。'
我的泪已汹涌如潮,霹雳帕拉的滴在键盘上。还说什么呢?本就相似的两个人,连感觉和顿悟都如此相似。我爱他,一直爱他,可是我也曾疲惫和厌倦。那么,他当然也会。
'永:你哭了?'
我一惊,急忙回信息。
'即:乱讲,我干吗要哭?
永:我感觉得到你哭了。别哭,你哭,我会心疼。'在一行字的下面,画着一个手指形状的图案。
'即:去,你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么?
永:不,我只哄你,你知道的,一直只有你。'
我的心乱了,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早就知道我是谁了?要求文件传输的请求发过来,我接收了,是一首老歌: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
激昂的歌声在午夜回荡,下面传过一行信息。
'永:我在等你,等你回家。'
我将脸整个埋进手掌,细微的抽泣声在空荡的机房中分外清晰。风声渐响,淹没了缠绵激荡的歌声,显示器屏幕一阵激烈的波动,稳定下来时,小企鹅已经暗了。我急忙上线,企鹅晃啊晃啊晃啊,始终也不亮。天亮时,警卫员告诉我,卫星接收仪器被风吹歪了,必须重新调试,我们跟外界暂时中断了一切联系。
等待等待再等待,除了等待,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六年前,坐在急诊室外的长凳上,也是这样发抖和等待。然后雷出现了,给了我信心和希望。现在,谁又来给我信心和希望?我站起身,走进机房,站在观察信号的女兵身后:'我可以帮忙吗?'
女兵回头,露出灿烂的笑容,递给我一个耳机:'好啊,你戴上,像我这样,不停的喊'喂喂'。如果听到回音,就喊'收到,基地收到',明白了么?'
'明白了。'
两天之后,通讯恢复了,气象预报说近两天内气象稳定,不会再有狂风和沙尘暴。支援组和基地的技术人员一起乘上吉普车,向2号风能测试实验站出发。天公做美,这几天风向稳定,强度适中,测试进行得很顺利,可是理论结果跟实测结果的效率差了15个百分点。我一遍又一遍的检查程序,却始终找不出结症所在。望着40多米高的塔架,我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什么?你要上塔架,还是在开机状态下?不行,太危险了!'基地总工坚决反对。
'你们请我来,就要相信我,我有把握,上去一定可以找到结症所在。'总工等人面面相觑,最后只能点头。
做好一切防护措施,一个技工跟我一起爬上塔架,风轮的速度很快,强大的风力令我们无法站稳。感受到风速,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向技工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下去。他点点头,朝下面的人挥手。突然一阵猛风吹来,他没有抓稳,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