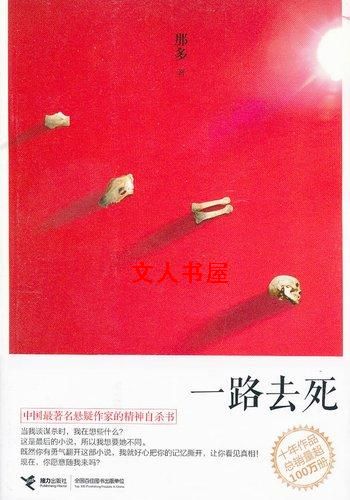一路嚎叫-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生气地问他在学校时为什么还要坐在无数人拉过屎的坐便器上拉屎,那多脏啊。why一听这句话脸立马变白了,他眼圈潮红地对我说:“我是被他们逼的!”
现在我坐在稿纸前回忆这段往事时心中只有对这句话的无限敬佩,根本不像当时光想操why他妈。
我们洗澡之前,我去水泥的家里找他,他还蒙在被子里睡觉。他的屋子里很暖和,可我的心已经成了一堆碎冰块。
开始时我们只有三个人,气氛还算热烈,可在路上时尚女孩、照片、砖头、礼花炮和他的两个老乡也参加了进来,就没有人再搭理我俩了。他们走在我和why的前面谈笑风生,一副艺术家闲逛的状态。我们有些失落地看着他们的背影,why终于也按捺不住寂寞跑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了。如果你当时路过那条像根劣质的雪茄烟的乡间土路,你一定能看到一支穿着奇异手提卫生用品的青年男女组成的队伍在浩浩荡荡地移动,它的后面有个垂头丧气的胖子,那就是我。
澡堂里所有的人在我看来都是湿乎乎的。我像一条正在捕猎的毒蛇一样用冷峻的目光去倾听人们的语言,我想象每一个人的裸体是什么样子,不论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肥是瘦,是美是丑。一旦我想到一副美妙的躯体也可以被毛巾搓出泥垢时心情就会变得异常舒畅。我又一次交了双份钱,why心安理得的样子让我又一次涌起无数的不舒服。
我们进去时宽敞的男浴室里空无一人,几个没拧紧的水龙头往地板上滴水,稀松的“噼哩叭啦”声让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闷热的地狱。脱衣服时我仔细欣赏他们身上的刺青,那些躯体上的图案在雾气里就像魔鬼一样。这个地方肯定是地狱!水泥发现了我正在欣赏他的大腿,他想做一个更阳刚的动作,踩上从自己手中跌落的香皂,滑倒了。
我走进了轰鸣的水流之中,它就像一座铁匣在关闭时由于金属磨擦而发出的怒吼;水跌落在我头上时有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像只拳头般捶击我,这股力量带有滚烫的血腥味。我闭上了双眼,用香皂抹擦身上每个地方。我闭上了双眼,水珠沿着我的眼皮顺流而下,它刺痛了我里面的圆球。我听见了犬吠声,眼中的一切又回到了暗夜。我拼命撕扯自己身上的肌肤与毛发,无数毛孔也在强而有力的攻击下渗出了渺小的血珠,它们让我全身存满了渺小的伤口。在心碎之前我担心没钱买衣服、CD和书,担心会考不及格,担心考不上大学,担心父母离婚,担心自慰有可能导致我终生不育,担心身边的某个朋友因实在受不了而自杀,可它们并不是我痛苦、压抑与郁闷的源泉。我怕死,可现在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离家出走,我毫无畏惧,我终于洗干净了我自己。
水泥在穿衣服时仍然在无休止地嘲笑砖头,我发现水泥把这当做一种乐趣,他脸色红晕用最刻毒的也是最搞笑的话语攻击砖头。我从内心厌恶嘲笑,可我已经被他逗得嗓子也笑哑了。砖头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面无表情的缄默,和我一样。大家反而笑得更大声了。水泥得意地抚摸砖头的脑袋:“砖头,你就是燕庄的搞笑英雄!”
“你妈逼烦不烦啊!”砖头急了,他把水泥的手甩开说,“少他妈碰我!”
于是没有人再笑,难堪地穿各自的衣服。
我们出来时时尚女孩还在里面,礼花炮站在女浴室门口大声叫喊她的名字,一个用浴巾把自己缠成个木乃伊的老女人出来说:“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叫我?”
大家愣了一下,接着哄堂大笑。
时近中午,大家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时尚女孩出来,我有些困了,深厚的睡意蚂蚁般在我身上乱爬。礼花炮烦躁地在众人眼前来回踱步,他大声叫喊:“姐,您赶快出来吧!我一个星期才洗了一次澡,现在身上又热出汗了,这等于白洗了。”另一个陌生的家伙在对照片描述自己对女浴室中的人们的下流幻想,他的话逗得我和why面红耳赤,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水泥拍了他肩膀一下:“你注意一下影响,这里还有未成年人呐!等回去了你跟砖头讲,砖头特热爱这种事情!”
砖头突然睁开双眼,用指证犯人般的腔调大叫了一声“格瓦拉!”
水泥踢了他一脚,说:“有毛病吧?格瓦拉怎么了?格瓦拉让枪毙时也尿裤子了,他也怕死!”
砖头激动地站了起来,双手握着拳头喊:“格瓦拉?打死我也不信!”
他认真的表情让我们又是害怕又是恐惧,水泥则不屑地吐了口痰:“你爱信不信!傻B!”
后来老F在一次劝我放弃无谓追求人类大同信仰时也说了格瓦拉尿裤子这件事,但他说格瓦拉那是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表现,并不是怕死。那时我已经放弃了做个真正革命艺术家的梦想,知道美帝国主义太他妈不讲人文主义了,他们应该先用二锅头把格瓦拉灌得大醉,再找个“山青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听丫唱两个小时“我的心在流血,今晚无人入睡”之类的咏叹调。或许他还要喊几句口号,也许他还要冲上帝的老脸吐口老痰,那也没关系,等格瓦拉瘫成一堆烂泥时再把人家给崩了。
时尚女孩终于像只香喷喷的花瓶一样从女浴室出来了,她比去时更性感。大家两眼发直地跟在她后面走。我开始嫉恨时尚女孩身边的照片,他在我眼中又瘦又矮又老又丑,而且有一口相当骇人的牙齿,我想到时尚女孩和只鲨鱼亲吻惨不忍睹的情景便不由地黯然神伤,似朵海棠般凋零了。
太阳挂在正当空中,已经是中午了。砖头说:“今天俺又搬了新家,请大家去吃牛肉面!”人群一阵欢呼,可我没有,因为我想我们是不会吃上这顿牛肉面了,它不是AA制。事情果然像我预料的那样发展,人们对凑过去的why越来越冷淡,后来干脆没人和why说话了。why只好跑到在他们前面埋头走路的我身边。我们简直比被大太太和恶婆婆赶出家门的小老婆还要可怜,即使我们已知道我们根本无法混进这个圈子,可仍然在期待后面会有个声音说:“why,不倒霉,等等我们啊!”
小时候我曾经画过两个表情相当严肃、刻板、白痴的人脸,事实上我们两个人当时的德性比昔日画中的脸还要严肃、刻板、白痴。事实是人家把我们晾到前面好甩了我们,当我们发现后面没有声音时再回头一看——他们已经排好队谈笑风生地进了路边一家面馆,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最其码已经有一百米了。why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接着讲他刚才被自己打断的话,我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接着听why讲他刚才被自己打断的话。我们仍然在笑。
5。爬窗户
在家门口why找不到家门钥匙了,他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了足有一百万个小时,绝望地长叹一声。我问他究竟把那个该死的小铁片放在什么地方了,他说有可能丢在屋里的床上了。
“你这个傻B!”我狠狠咒骂,“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一脚把门踹烂就行了嘛!”why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怎么可以?踹烂门我们不但要换新锁,房东知道还会骂我们,甚至罚我们钱。我告诉你丫,现在我们的钱可是我借来的,花一分就他妈的少一分了!”
why嘟哝着问我应该怎么办,我他妈哪里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盯上了门上面的那扇窗户,它四周的木框斑痕累累,它以前应该是绿色的,可油漆掉光以后木头裸露在了外面,长期沾染灰尘让它变得像污水一样肮脏,因此也更加美丽了。重要的是它是开着的!这窗户大张着嘴。why看出了我的意思,他说:“不倒霉,我告诉你丫,你打死我我也不钻窗户!”
“那么你总不能让我这个160斤的大胖子爬墙上房吧!”我怒吼,“更何况是你把钥匙给丢了的!”
情急之下我还推了他一把,why看出了我的愤怒,没敢还手。当时他若是还手,我会毫不考虑地给他两个大嘴巴,也许我们会因此分手,各奔东西。可why像个害怕的小鸽子,只会说:“我不管,我不管,我从小就有恐高症,我爬上去肯定会摔死!”
他的眼睛都闪出泪花来了。这时,布谷从他房中走了出来,他问我们是不是进不去家门了,我满腔感激地认为他要帮助我们,可当why说明情况之后这个混蛋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噢!那可就麻烦了!”接着他又拿着水盆去浇那几盆烂花了。我感觉他的微笑里有很大的成份是在幸灾乐祸,我正处在为一件小事就能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青春期里,我在心里恨恨地咒骂他和他的摇滚乐。
我苦苦哀求了why足有一万年,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去钻窗户。一只黑色的鸽子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它滑翔时翅膀与风摩擦的声音尖锐而且迅速涌进了我的嘴里,我对why嚎叫:“你这个狗杂种,你去死吧!”
我跑到院子里找到一把椅子,踩在它身上后双手触到了木框边沿,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神仙皇帝英雄偶像楷模榜样之类的东西,没有人能带我回家,我自己回家。
后来我又上了高中,语文老师出了个叫《窗口》的作文题目,有人写眼睛,有人写服务行业的态度,还有人写言情小说和鬼故事。我则叙述了一个小胖子在屋外从窗户翻到了屋里的过程,我把他当时的动作、表情、感觉、心理活动等都做了逼真的描写,在我的笔下它并不比攀上世界最高峰容易多少,因为我平常总是神神叨叨。我的老师误以为我热爱后现代,他把我的作文仔细看了一两遍,也没有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着什么深奥的意义,他给了这篇作文十五分,评语是:无聊!跑题了。我写那个胖子因为体积太大,骑在窗框上折腾了很长时间,下来时被木头里的钉子划破了T恤,钉子在他的胸口上留下了一道长而浅的伤痕。
这道伤痕现在还躺在我的皮肤上,有人问我是怎么弄的我就骄傲地说是被人用刀砍的,他会发出惊叹声。
我终于进了家,可我受伤了。why在外面急促地敲门,我没有理他,那个该死的杂种一直在下面嘲笑我的狼狈,我的愚笨。我脱下了T恤,擦拭干净仍在流血的伤口,这才为why打开了门。他还在指着我竭尽全力地大笑;我俩像讲道理一样吵了起来。布谷偷偷的向我们家报以讥讽般的扫视,我没好气地用力把门给丫踹上了。
why说:“哥们,你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弄丢钥匙的,下次我注意,现在我要出去玩了,一会儿我找你去吃饭!”说完话他就像只正在发情的兔子一样滚蛋了。
我坐在床上抽烟。没有音乐,任何声音都没有。天突然黑了,我像是回到了黑夜,烟雾飘到我心里吟唱不知名的诗句,院子里的狂风把烟头上的火星弹在了我赤裸的肚皮上,一股焦臭的青黑色烟雾升腾而起,我大叫一声,从床上摔落下来。
6。离别
我走出家门。燕庄的路口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就看见了老F、why他爸和几个陌生男女。他们也看见了我,老F手臂的挥动幅度让我相当感动,我没有逃走,我知道一切该结束了,这就是宿命。我们向对方走去,老F紧紧地把我搂在了怀里。
可我毫无感觉,我身体处在莫名奇妙的麻木之中,心中暗自惊叹这个世界可真是他妈
的奇妙!老F说老M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守好些天了,我相信老M她会的,我们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可老M在电话对面泣不成声时我竟然还是毫无感觉。我只是在想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当时我只发了一次脾气,他们提出要和我一起回家去找why,我瞪了这些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一眼,死活不同意。
“你们要去的话我就不去了!”我甩开老F的手。老F的手有些颤抖,我知道他怕我一去不回头。一个老女人走过来劝我也要考虑父母的立场,老F介绍她是学校专门处理这种事的工作人员,她已经跟我们颠簸好长时间了。于是,我只能争取做个听老师话的好孩子了,我怕老师,我别无选择。这一切都让我不高兴,惟一庆幸的是老F没让我气得瘫在床上。他有高血压,这我知道。
当我回去时why刚要出门,我对他报以苦笑。我们正发愣时,水泥的家里突然爆发了骇人的巨大哭泣声。所有人都拧紧眉头,只听水泥在大喊:“二虎,你怎么就这样突然死了!”
我对老F解释:“没事,昨晚一个与我一块睡觉的家伙,老死了。”
老F脸色煞白。这时水泥抱着那只紫毛狗的尸体冲出了我们组成的人群,哭泣着消失在了远方。why盯了他爸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不是在演电影,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爸,你怎么来了?”
why带着大家参观这个我们生活、学习与战斗的地方。我想我们一定要回来,我们一定会回来。我趁他们为我们生活的简陋而唏嘘时,急忙拿出四百块钱塞进被子下。那时,我仍然不愿承认这一切都结束了。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