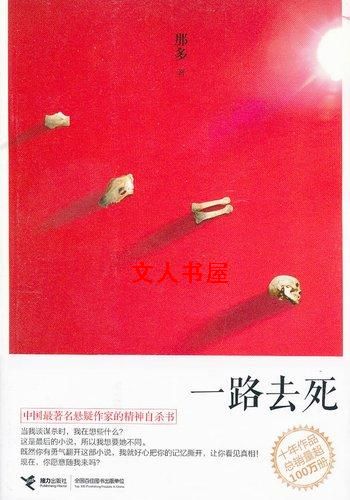一路嚎叫-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强过,而现在我和生活一样软弱了。
通往演出场所的道路两旁到处林立着良劣不一的大学,那些让我又恨又怕的校门下面进出着各种奇怪的家伙。一想到老F、老M竟然希望我变成这些家伙里的一员,我就难受得想死。坐在我旁边的照片若有所思地盯着这些嘻嘻哈哈的大学生们,他少年老成的脑袋让我泛起了一丝忧伤。我突然很想念我的朋友剑子,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用什么样的游戏打发青春。我想我应该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做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了。我永远无法了解这些和我一样痛苦的孩子们终究为何而痛苦,我对他们充满了恐惧。
照片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上高几,我回答了他。丫满脸沧桑地说你们真好,竟然还上了高中。我问他:“难道你没有上过高中吗?”他说:“没有,我初中毕业就找了个单位工作了。”然后照片开始向我开始述说他的往事……
现在我们要回到五、六年前,那个摇滚乐做得跟流行歌曲一样的年代。照片从事着一种穿上制服专门抓马路边无照经营的小贩的职业,他那时和现在的我一样少年轻狂每天乐呵呵地冲着面前的弱者耀武扬威,可心中对成人世界的勾心斗角充满了焦虑与恐惧。单位里的帮派都不愿意接纳这个毛头伙子,没有爱情进补的照片只好把吉它也扛到了单位,一闲下来就像疯了一样的练琴,因此他家老头子和单位领导没少说服教育他。在一次欢迎上级领导参观中照片目睹了一件让他永生都不可能忘掉的事:那个看起来足有百岁的老家伙一下汽车还没等站在两旁的同志们鼓掌致敬就迫不及待地向门里冲去,当他跑进门时,照片的顶头上司一头扑进了领导的怀里,顶头上司哽咽着说:“您老人家可来了,我们想念您啊!”领导铁青着脸勉强微笑着,正当他准备拔脚进去时,顶头上司却拉住他开始为同志们讲述这位老先生的丰功伟绩。据照片说最棒的一件事是此人曾经在那个所有人都争当傻B的年代代替一个不愿当傻B的大官挨过许多砖头和口水,当大家热血沸腾的为领导鼓掌时,老头突然蹲下捂着脸哭了。照片心想:“多好的老同志啊!听别人说自己事迹竟然谦虚得哭了!”然后所有人就闻到了一股来自老头身上的奇臭无比的味道。照片说那时的上午,天空还滞留着昨晚的月亮,它颜色苍白,像个伤口,大家望着拉裤子的领导手足无措,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在自己还没被围观如何拉裤子前辞职不干了。
照片忧伤地唱起歌,一个中年妇女和她的儿子站在我跟前瞪着我脖子上挂着的钢锁发呆,那条路上车流像恶梦一样向我眼前奔涌而来。平坦的马路让我突然想起剑子好像还谈过一次恋爱,女朋友高挑瘦削犹如一只筷子,我曾经说过心脏飞机场跑道都比她的胸部饱满,为了这件事他把一个完整的冰淇淋使劲掷在了我的脸上。
此女还和我的另一个朋友英雄好过一段时间。英雄那时每天都要去她家接丫上学,通往学校的路是一个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的大坡。每当英雄累得吐出舌头时她就会莺声燕语的问:“累吗?”然后英雄气质豪迈地说:“不累”。后来有一次从学校回来下这个坡时两人摔了下去,双双骨折,然后分手。我不知道他俩睡没睡过,但剑子说睡了,剑子说话总是颠三倒四。有一次他喝醉了之后说:“我根本不相信二十岁之前谈恋爱的人是在寻找什么爱情,就是为了上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口口声声希望你理解我的女人,我凭什么去理解她?我自己都没人理解,我他妈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又有一次他喝醉了又说他想找个受伤比他更深的姑娘好好安慰她。这种话和那些演讲稿一样,听一两遍还挺感动,可听多了就会厌烦。
6。旱冰场在演出
我们要去的那个演出场所在一条铁道边上,我下车之后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七拐八绕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那个地方。门口的路边蹲着许多人,他们手中拿着啤酒相互说笑,我发现他们用眼角余光盯着我时我相当不舒服,就好像被一个跟我一副操性但心高气傲的浑蛋教育了一样。进去时我在照片后面心惊肉跳,生怕有人把我拉住买票;而那帮家伙不理我了,可没有人管我,门口那两个查票的脸贴在桌面上好像睡着了。
这儿不是酒吧,而是个旱冰场。塑料轮子碾压木板的声音让我撕碎自己耳朵的心都有。我在外面的长椅上看见了时尚女孩、砖头、水泥等一大帮人,他们坐在那里用同一副表情闭目养神。时尚女孩对照片开玩笑似地说:“你丫还领着两个小弟杀进来啊?”这句话让我有些难受,以致于她和why要烟抽时我怎么看她抽烟的姿式怎么像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歌女。
我和why也坐在了长椅上,可里面流行音乐改的迪斯科舞曲让我无法入睡。why看着对面墙上那些演出照异常兴奋,他时不时的捶一下大腿说某一张照片上的是某一支乐队。我盯着眼前这些衣着或者怪异或者时尚的青年们来来往往,一想到是他们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我就难受。我走进了冰场,里面有许多穿校服的学生张狂得像驴拉磨满场转圈,我想他们都是逃晚自习出来瞎混的。一想到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心里就更难受了。我看见砖头突然扑在了水泥身上,水泥眼睛都没有睁开,而是用毛片中黑人般粗重的嗓音夸张的大叫了一声:“哦——也!”所有人都笑了。
why说:“水泥真逗,我觉得我性格和他特一样!”我没有理他。去厕所时,两个去还旱冰鞋的士兵与我擦肩而过。
演出是十点半左右才开始的。
出场的第一支乐队是“狗吃狗”。砖头因为没有抽到好签而被礼花炮踢了一脚。当他们试音时我发现台下站着的观念竟然大多数都是在杂志露过面的乐手,他们的第一首歌是《杀死复杂》。我没有参加台前的pogo,如果把眼镜撞烂了连修它的钱都没有。时尚女孩为这首歌加进了飘渺的女和声,我却已经失去了黑裙红发的激情。
“狗吃狗”乐队演完之后上台的乐队都没有煽动起激情,台下的观众冷静得像手术刀,而台上的乐手却个个活蹦乱跳。我在吧台边上遇见了看拳头他们排练时的那个白领,那个一下赚了十万吹牛给拳头扩大排练场的家伙。这家伙告诉我他想开一家音像店,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他的店里打工。当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why时,他一边随着音乐摇头晃脑一边鄙夷地唾了一口痰,大声说:“听他吹牛B吧!”why说他渴了,刚才托拳头到外面买水去了。这时砖头满身大汗地走了过来,他冷冷的对我说:“给我五块钱”。许多人停止了蹦跳看着我们。我给了他钱之后why骂我是个傻波依你丫给他钱干什么?我被骂湖涂了:“这不是人家拳头买水的钱吧?”why说:“你有毛病吧?拳头想要钱自己会来要!”我愤怒地想冲出去找砖头问个清楚时why又把我拉了回来,他说为五块钱撕破脸不值得。当我们坐在长椅上休息时我想把钱还给拳头,可他笑着把钱又塞回了我手里:“那两瓶啤酒是我请你俩的!”当时旁边有许多人冷冷的盯着我们看。我很难过,因为杂志上说燕庄许多乐手一天三顿饭都成问题,我真的不愿意让比我更穷的人请我的客,真的。
高潮还是“腐蚀武器”。当第一个字从拳头嘴里蹦出时,整个屋子都爆炸了。我不由自主地被撞到了台前,所有人都使劲蹦,我不时被撞倒在地,各种奇怪的物体在我头上飞来飞去。我哭了,我拼命挤出人群后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种感人的力量不是台上炫目的乐手,不是音乐,甚至也不是艺术,而是我们,是台下这些脸上什么表情都有的孩子!我知道这种火药般的情绪可以很快地传染到我们身上也可很快地从我们身上消失,但我还是要在我没有完全学会虚伪做秀之前为每一个不朽的孩子大哭。演出很快就要结束了,听音乐跟上课正好相反,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个乐队似乎在做行为艺术,主唱让大家跟着鼓点一起数数,而他在吉它手胸前挂着的黑板上写了许许多多形容词“美好的”、“纯洁的”、“倔强的”、“善良的”只写到台下所有观众懒得再数。有人开始不满地催他们下去他才突然疯了一样用拳头猛击黑板,吉它手和他一起摔倒在地。why不喜欢这个乐队,因为他们没有脱光了衣服在台上拉屎或者手淫。
我和why跟着众人涌出了那个地方,当我和why把音箱往出租车上搬时,砖头和一个小伙子打了起来,他是一支音乐相当凶悍的乐队的吉它手。当我们把砖头从他身上拉起来时,丫竟然斯斯文文地哭了!他说:“砖头,对不起,我真的是没钱还你!”砖头好像喝醉了,他破口大骂:“去你妈的,那是我这个月的房租钱,你让我明天住哪儿?”
水泥起哄似的嚷嚷:“跟我一起住吧!”可是没有人笑,大家都很劳累,战争很快结束了,当我和why在铁道边撒完尿回来时门口空空荡荡,只剩下了拳头和水泥。我们又七拐八绕的想早些走完这条肮脏的小路。我饶有兴致地走在他们后面听拳头和水泥讨论刚才演出时,why在旁边的溜须拍马,但我并不恨why,我们都是机会主义者,只不过他比我更不要脸罢了!拳头说水泥有一首歌打鼓时打错了两个地方,水泥则死活不认帐。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我蹲在路边腹中痛如刀绞。此时那个在音乐节晚上出现过的女孩又出现了,她怀中还是抱着那条狗,我们的目光和当晚的天空一样虚无,除了我身上散发着臭味的汗水之外这个世上空无一物。
回家的路上灯火辉煌,天空也被这种该死的浮华气息染红了,我们坐在轮胎已经干瘪的出租车上听电台播放的流行音乐。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用我弟弟的声音说我总是心太软,他说错了,我的心一点都不软,我他妈为了自己把老F老M剑子以及所有爱我的人都丢弃了,为了能让自己快乐我甚至都想自杀,我和你们这些虐待狂不一样,我是个自虐狂,我无比自傲,只有我自己才配当我自己的地狱。回到家时我给了拳头二十块钱,我说十四块钱是我们的车费,六块钱是那两瓶啤酒钱。拳头再一次把六块钱还给了我,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他说我说过是请你们喝酒,你不需要还。拳头和水泥从车上扛乐器时why小声对我说:“我觉得你丫不至于这样!”我恼羞成怒地让丫闭嘴,他在我后面小声说:“你别以为你壮我就怕你,其实人要是让逼急都会拼命,谁也不比谁弱多少!”在寂静肃穆的夜里我停下脚步面带嘲讽的微笑指着why说:“你不满意吗?别忘了要不是我你还在那个傻B学校受苦呐!”
why不说话了。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背影都犹如八十岁老人曾经拥有过的青春一样脆弱。而我的夜晚是最像成人笑话的那一种:无比可笑,无比无聊,无比孤独,无比凄惨。
7。最难以启齿的事
月光洒遍我们的小屋,我躺在床上开始发愁在燕庄怎样渡过冬天,睡在我旁边的why的手突然拍在了我的裤裆上,痛得我放声大叫。why嘻皮笑脸的提议做为至交好友我们应该坦诚布公,不应该不听朋友的批评。我叹了一口气,说:“好吧!那么你说说我到底有什么缺点?”why严肃地说:“我认为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不知道,但就是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否则就不是个人了!”
why说我们是至交好友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坦诚布公还对我讲述了一件他认为最难以启齿的事。他说十一岁那年有一天去邻居家玩,两个大人都上班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两人打了一阵电子游戏之后觉得索然无味,小女孩提议玩一种解剖尸体的游戏,why面对着平躺在眼前的小女孩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手掌胆战心惊地在她身上移动,男孩因为兴奋呼吸开始变得粗重,他莫名奇妙的褪下了她的裤子,一个新奇的,既没有在现实中也没有在幻想里出现过的世界出现了。why说自己当时都傻眼了,他似乎听到了一种自己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在why抚摸那个小女孩下身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呆呆的望着无花板。why等待着一声惊如天雷的喝斥,在它里面心碎,在它里面瓦解。他所希望的一切都没有出现,只有手指与身体摩擦时的声音,他说他其实在潜意识里真正希望的其实只是这些。
我问why当时有什么感觉,why说那时他希望自己要么能这样做一辈子要么赶快爆炸,可小女孩又爬起来去看动画片了。“我恨她,我一直到十六岁时只要女生和我说话我脑海里就会浮现我刚才跟你讲的那副画面!”why在如刀刃般尖锐的黑暗中冲我大叫。
那一夜why折腾得不亦乐乎,他会突然用手去探摸我的下体,在被我一脚踹下床后他哈哈大笑着说你怎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