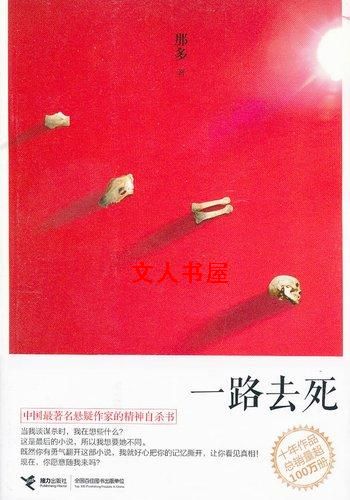一路嚎叫-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只想回家。
“摇滚大排档”里面没有几个人吃饭,枯瘦的老板和几个样子傻乎乎的服务员围在柜台上那个黑白电视边上一脸僵硬的冷笑。时尚女孩也在那里,可我们并没有打招呼。我越来越烦,这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可我想象中的燕庄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忘了。两只苍蝇在烟雾中四处乱飞;它们的眼睛里充斥着淡紫色的光;它们在空中相互撞击后很快的分开;它们是一对既将相爱的情侣;它们终于落在了我们的桌子上,一只压着另一只,像是从一出生它们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why嘻皮笑脸的让我看这对桌子上的黑色天使是如何做爱的,可话音未落一只菊黄色的苍蝇拍就拍扁了它们。我在一刹那看见了两个生命是如何把自己与对方混成一堆,流着黄色汗液的肉泥。满脸杀气的服务员走时瞪了我们一眼,why很不自然地咧着嘴对她傻笑。
牛肉面里没有一块牛肉,吃到最后我面对着满碗菜叶子绝望了。why的面里倒了许多辣椒油,他原本苍白的头皮现在喷射出了原子弹爆炸时的冲天烈焰。why说照片让咱们下午进城去买个节拍器,我根本不知道那玩意是什么鬼东西,可我仍然微笑着说买吧,买吧,不就二百块钱吧?你别着急还我。why听了这话愣了一下,顷刻,他抬起头:“是啊!到时候咱们能一起用。”我想我应该承认自己是个白痴了,并不是我在此时还没有看出why的意图,可我无所谓了,我只想把他留在我身边,只有那样我才会感到安全,为了这个目的我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有一个声音在我们进来之后一直讨厌地侵占着我的耳膜,当我和why已无话可说时它的体积便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晰。那个混蛋正在和一群笑声像狗叫一样的家伙们讨论强奸的意义。
“强奸……做为人类性活动的最高形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它将快感、恐惧合为一体……即使是被强奸者,她的快感也是其它……这种方式是感情的终极”!
我并不是一个卫道者,可我憎恨这段话。如果在几天以前我会走开不去理睬,可我现在只想打架。我站了起来,向他走去,我见过他,在音乐节上这个疯子对我的命运妄加评论,害得我在那个伟大的节日里像踩上了大便一样整整恶心了一天。我面带着微笑,说:“您既然这么喜欢这种形式,为什么不把这套理论讲给您的母亲听呢?或者您干脆把它用在您母亲身上,不是更有体会吗?”
他们一桌人都惊呆了,我目睹了那个疯子脸色由红变白的全过程。他突然一声尖叫,踢开椅子向我扑了过来,我伸出拳头让他又从空中爬回了地面。他的朋友们也向我扑了过来,可我惟一的朋友why只是结结巴巴的说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燕庄的,就别打了;更可恶的是他不去拦阻那些打手们而是紧紧的拉住了我的衣角。我们俩最后一起被踢翻在地,我与why紧紧捂着彼此的脑袋。那些衣服颜色艳俗的服务员们的惊叫声响彻天际,我听见了玻璃在我后背上爆炸的声音。世界是桔红色的,上帝在燃烧,why大声对我喊:“不倒霉你千万别起来,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们的拳打脚踢中我闻到了一股苔藓的气味,这种新鲜的味道让我的颓唐与懊恼一扫而光,我好像又重新诞生了另一个大脑,里面的世界时而雪白时而漆黑,它就像一颗流星般迅速闪烁,每一个镜头在消失之前所有的景物就已经爆炸、坍塌并且毁灭了。
4。摇滚大排档(二)
疼痛是另一个人所能给予我的全部感情,可耻辱产生在我自己的体内,让我厌恶。我躺在地上,眼皮底下是发着污水般绿光的痰迹和还挂着肉屑的鱼刺。我像一个正从糟蹋了自己无数遍的罪人体内挣脱的灵魂,毫无罪恶感可言。其实我们谁也不用赞扬心中的神,我们自己就是神,当我被几十只脚踩在地上时我便用一种吃了苍蝇的感情去观察我身处的环境。可在我呕吐时我才发现那只苍蝇飞进我胃里时它的胃里已经有了一块黄金,这枚指甲大小的黄色金属在迅猛而又急促地敲击着我自己的荷尔蒙,这时我就是世界的黄金,世界的神。
这一切很快消失了。凶手们在时尚女孩的尖叫声中随风飘散,大家脸上的表情就像少年们面对大街上的姑娘的口哨声。她对那个混蛋说:“你们要是再打的话,我现在就让你还你他妈上次跟我借的二百块钱。”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当时尚女孩把我们拉起来时我看见why的手上在流血,被玻璃渣划伤了。why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我是个爱被人打的暴徒。时尚女孩盯着我们似笑非笑地说:“你脾气怎么这么冲啊!这个地方有些人就是这样。”我想对她说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和他打架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老君子或者女权主义者,我只是想自己痛击自己,但自己又没有胆量罢了!可“大排档”那个面目诡异的老板拉住我让我赔他的损失,他的手指在我的胸膛上狠狠捅刺,口水喷在了我的脸上。我从已经很薄的钱里抽出五十块钱扔在地上,对人们大喊:“你们谁都别他妈碰我,谁都别管我!”我推开why和时尚女孩从“大排档”跑了出去。
我跑在路上的时候哭了,我想为什么我会难过呢?路边墙上的白色标语象医生的微笑一样让我感到难过。我一直在心碎,从一生下来我的心就碎了,我额头上布满了祖先们的皱纹。现在我停止了奔跑,心脏像将要爆炸一样在胸膛中狂跳。我发现视野中的每一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写满了发布谎言的文字。我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看着路对面的女人向行人们散发这些广告传单。
女人面无表情地将她手中的广告塞进一双双手里,当有人拿到粉红色纸张看都没看就扔了时,她的瞳孔里就会有痛苦在瞬间内闪烁。我坐在冰凉的石头上不再哭泣,可我仍然气喘吁吁,从鼻腔里吸入的烟雾让我的感觉好了些,沙滩上那些崩溃了的城堡在重生。我无精打采地看着那个女人双手像飞一样把广告塞进疾弛的车里,心中盼望这种危险的游戏赶快成为一场血肉横飞的悲剧,可所有的动作像一场事先已经排练了无数遍的戏剧毫无美感可言。就连她的双手,像天使一样跳跃的双手也只不过是两只身上沾满了灰尘与泥浆的乌鸦。我看见了一个小男孩,他戴着黄色的帽子与红领巾,低着头像个小精灵,来来回回在女人身边走了无数遍,有时甚至只是绕着女人转个圈,但每次走过女人身边时女人都会给他一张传单,男孩手中的传单越来越多,渐渐超过了女人。当他再次走过女人身边时她一把拉住了他,她瞪着眼睛象乞求一样对男孩说着什么,女人的唾沫顺着风喷在了我的脸上:“孩子,你手里的传单就是拿回去当手纸也够你们全家用半个月了!”男孩微笑着甩开了她的手,他说:“你太小气了,昨天我从那个叔叔手里拿走足有三百多张传单,人家也没有说什么!”他们站在那里争论,撕扯,无数张粉红色的传单飞上天空,随风飘散。
我的烟燃到了尽头,焦虑迫使着我回家。一辆到处都是青锈的三轮车侧倒在村里土路的旁边,铁锅也扣在了地上,里面的肉汤流向我的脚下。我看见那只紫毛老狗陶醉地舔着。一个面目肮脏的男人咒骂着准备抬脚踢它屁股时它突然暴躁地吠叫着转身扑了过去,男人在它的狂吠声中落荒而逃。
回到家里我已不再那么颓唐,甚至可以说变得兴高采烈了。why正趴在床上一个人狂笑,他手上缠着一层光芒刺眼的纱布。why说时尚女孩带他去一个小诊所缠上了这堆布条。“诊费五十块钱,那女孩先替咱们交的,你下次见到她一定要还她!”说完这话why继续大笑。也许是他的声音太大了,水泥在隔壁敲墙:“why,你打扰我睡觉了,我晚上还他妈有演出呐!”我压低声音问丫为什么笑,why说刚才在诊所里时尚女孩给他讲了一个特别逗的笑话。
“我讲给你听,”why捏着嗓子模仿时尚女孩尖声细气地说:”以前我上的那个女子学校校规特严,连男厕所都没有。学校开始流行一种传染病,好多女生都面黄肌瘦,憔悴得犹如骷髅。校长害怕了,找来医生,医生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对校长说:‘你招一个班男生,我保证她们的病就都好了’!校长听了医生的话,招满了一个班男生之后就出国考察了。等她从国外回来,一进校门吓了一跳:女孩们又恢复了往日天真活泼的生气,快乐地嬉戏奔跑,可阴影遮掩着的角落里三三两两躺着一具具骷髅般枯瘦的肉体,他们的皮肤比影子还黑,而眼珠和地上的石头一样肮脏。校长找来医生,问:‘这些是什么?’医生叹了口气:‘这些都是用剩的药渣。’”
why讲完之后紧皱着眉头哈哈大笑,兴奋地用脚捶击床板。我纵身压在了他身上,我说why,对不起,我特烦也特害怕。why在下面乐不可支地说:“没事,咱们是朋友,你也是为了我烦,可现在已经这样了,想也白想,我们应该高兴!”我想我也只剩下高兴了,但只要我还拥有高兴这种感觉我就还是个英雄。我说:“走吧!我们去心脏买节拍器!”why大声欢呼了一阵,然后嫌我土得掉渣,让我换上他的衣服。正当我这样做时时尚女孩和照片闯了进来。时尚女孩总是在我穿衣服最少时闯入我的视线。我穿上长裤后把why的诊费还给了她,照片说:“你们下午是去买节拍器吗?”why点头称是。“那么你们帮我发今天晚上演出的传单吧!”照片把一叠复印纸扔在了床上。
“去哪儿发啊?”
“你丫傻吧,”why抢着回答,“书店,音像店,琴行这些地方都成!”
“还有老外和那些一看打扮就是同志的人。”时尚女孩补充。照片让我们尽可能快些回来,晚上可以去看演出。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始激动了,我热爱摇滚,但可笑的是我竟然只看过一次摇滚演出。
5。拳头的家
从城里回来;我们直接去了拳头的家,“狗吃狗”和“腐蚀武器”的乐手们都蹲在院子里。“腐蚀武器”里那个从没有跟我们说过话的贝司手正在和砖头说相声般的吵架。有人大笑,有人瞪着眼睛像秀逗了一样,有人无精打采地抽烟,还有人把这三种状态都显示了出来。他们在玩弄从我手中夺过去的节拍器,冰冷的声音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凝聚力,我全部的幻想在此时都被他们剥夺了,大家都不愿再听那两傻波依越来越索然无味的争吵,纷纷拥进房东家像教室一样辽阔的客厅看电视。有一个知识分子打扮的中年女人在一个谈话节目里对台下
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们说:“当同学们看到荧幕上男欢女爱的镜头时就去外面踢踢球或者唱唱歌,这样你感觉自己心情好多了!”
我身边的人在欢呼。
“没错,所以我们就来燕庄了!”砖头兴奋地说。当那个看起来无比清纯的主持人问女心理学家应该如何避免中学生早恋时,我听见砖头对着地板小声的自言自语:“干嘛要避免?学校给学生发放安全套不就得了嘛!”
大家都笑了。鹤发童颜的房东老奶奶坐在我们旁边面无表情的用搓板洗衣服。水泥的紫毛狗这时蹓跶了进来,面目凶悍的冲礼花炮吠叫,砖头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你丫这条狗怎么还没死啊?”它卧在了水泥脚下,水泥大喊自己认识的人越多自己就越喜欢狗。我开始抽烟,快乐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论我逃到什么地方心中却只想呕吐?
当我们看了足有十万部弱智电视剧之后大多数人都已东倒西歪快要睡着了,这场演出的策划组织者拳头终于回来了,乐手背着自己吃饭的工具兴奋地冲了出去。三分钟之前还乌烟瘴气的客厅现在只剩下我、拳头、照片和why四个人了,拳头听我说完我们下午所做的事之后很兴奋,他说你丫行!
天色已暗,那条狗在街道上像我们这些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四处游荡,我脸上的神情似乎很兴奋,可我已明白快乐永远是假的;其实我们和这个夜晚、这条街道、这条狗是同胞兄弟,脸上都写着光荣的忧伤。
我们蹲在公共汽车站牌底下等车时,拳头和照片说起了他们以前的一次演出。拳头说那次观众特别多,可主办者规定一支乐队上台只能唱三首歌,中间不能跟观众说话。我们一起用最富想象力的脏话恶毒攻击主办者。两个高中女生频频低下头不无厌恶地观察我们,红着脸偷笑。上车之后车厢里昏暗的灯光浸沧着人的脸,在时隐时现的尘埃中显得晦涩不明。有个女孩把脸靠在玻璃上双目阴沉地望着外面的世界,在她一半思考一半幻想的梦中我曾经倔强过,而现在我和生活一样软弱了。
通往演出场所的道路两旁到处林立着良劣不一的大学,那些让我又恨又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