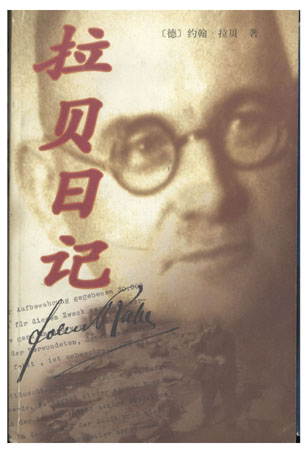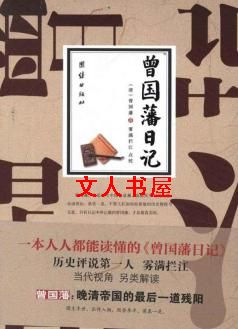莫非日记-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好。像我这样又有什么好处呢?穷其一生只是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罢了,而且没有导演告诉我下一个镜头是什么,我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角色。
我想我属于玄虑型人种,放着好日子也不会享受,好像来到这个世界是专门为了找苦吃的。愿天下人皆不像我,都能闭上眼睛一觉到天明吧。
晚上刀农必须回剧组,我带他去吃了“皇城老妈”之后就送他回去了,然后一个人在府南河边坐了很久。桥边各有一棵大槐树,每棵都有两抱粗,黑黑的树干散发着湿重的雾气,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走来走去的,就走到了一条繁华的街道,有一家做旗袍的店铺还没有打烊,里面悬挂着各色各样好看的旗袍。我竟以为我又走回了自己的那个年代,就是三百年前那个年代吧。稀里糊涂她们就给我量了体、裁了衣,让我五天后过来取衣服。也好,或许我的确应该有这么一件月白色的旗袍吧,让我可以在某天某个晚上,体会一下关于自己的过去。
这个地方,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的,头顶没有月亮。
第四部分:风往北吹褪色的年华
2000年10月7日 阴 褪色的年华
像个游魂一样在这个散淡的城市晃悠了五六天之后,穿着那件月白色中长袖旗袍站在镜子前面端详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和这个城市飘忽不定的云雾的天空一样,浓得像一团雾,仅仅是一团雾,没有化开的雾。
刀农从背后抱住我,说,“你真美!你比我们女主角漂亮多了!”他口中的哈气吹得我耳根痒痒的。突然间,我就心酸了。这是怎么了?好像年龄越来越大,而心性却越来越像小姑娘了,多愁善感的,难道是更年期提前到了?
路经一个花店的时候,他跑了进去,一会儿又抱了一束马蹄莲跑了出来,说,“我一直想送你一束这样的花,你看多洁白啊,像你!”我忽然就想起自己也曾经这么抱着一大束马蹄莲想送给一个人,她却不在了。紫烟,你在哪儿呢?你真的就像一缕紫色的烟雾消散在空气中了吗?你在空中有没有想到过我呢?我不明白女人们为什么一开口就说自己喜欢百合花,是因为它美丽的名字吗?要说香氛,还是粉色的香水百合好,若说洁白圆润,当属马蹄莲啊!为什么仅仅因为名字就迷恋它呢?或许因为紫烟,因为想念紫烟,才喜爱上了马蹄莲吧。直到今天,才有人送我。在他的心里,我真的如马蹄莲一般洁白无瑕吗?怎么可能呢?马蹄莲那厚厚的、润泽的花和叶,就像我的梦想一般毫无瑕疵,真能读懂它的人有几个呢?我,也是读不懂的。只是,这花映衬着我一身的白衣和一张素白的脸,一定是相得益彰的,如梦似幻的苍白罢了。
我就这么抱着一大束的马蹄莲,告别了刀农,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应该告别的一切。刀农又像孩子一样流了泪。我说,“再哭又要下雨了。”
这一次,我亲吻了他的额头,在关上车门的刹那。
我感觉到自己也落了泪了,终于落了泪了。
我坚持不让刀农送我去机场的原因是,我害怕分离的场面,无论是谁的,都让人看着难过。若说来红尘一遭不容易,人们为什么还总是要轻言离别呢?往往一别后,再无相会之期,他们想到了吗?
岁月并没有让我变得坚硬、麻木,却让我更加柔软和儿女情长了。这完全有悖于人类的生命发展史啊!好像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屡见不鲜。刚一出生,别的孩子在哭,我就在笑了;在我还没有学会爬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走路了;不到五岁就掉了大牙,直到十八岁那年高考时才脱落最后一颗大牙,我把它扔到房顶上了。就是这样,我的存在就是有悖于常理的。难怪从小母亲就说我,“这是个怪物,邪着哪!”或许吧,我的血液里秉承了母亲的怪异,父亲的执著,于是就长成了我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吧。如果我曾经有过前生,我想我一定是只山怪。面对险恶的山,我总有着狡黠的生存智慧,而迷路到了城市,也只有惶惑不安了,看到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影像,有时也会哇哇大叫,“怪物啊!”现在,我的眼睛已经被城市异化,我只相信我能看到的,一切有悖于常理的,统统被斥为“异物”,理当被消灭的。
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
华灯初上,整座城市流光溢彩。一座座的高楼大厦,流影的立交,彩色的霓虹灯,一切是那么美轮美奂,然而有生命的活物却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是我,也像一个幻影,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幻影,就像这个城市的附属品——垃圾。我的身体奋不顾身,毫无选择地跟着这些机器来到了二十一世纪,我那可怜的末世情结以及谜一样的梦想却早已摧枯拉朽般的一地狼藉,留在了远古的某个世纪。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开始对自己的过去质疑。然后,绝望的未来在不夜的灯火中凄然离去。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觉到,我终将对自己无能为力。
月朗星稀。
我从行李箱中取出那件月牙白的旗袍,穿在身上,伫立在窗前,一如我想象中的那般孤独、空寂。
第四部分:风往北吹丰富的空洞
2000年11月5日 晴 丰富的空洞
北京的秋天很短,好像只需要一场风就可以吹落所有的树叶,只需要一场雨就可以迎来冬季。又看到光秃秃的树干,十指向天的样子,晴空无云,终于确认自己是在北方了。
有人在放风筝,花花绿绿的,一片一片,忽高忽低。我仰头望天,痴迷于那片空阔。我想,这就是久居于城市的人们惟一放飞自己的一种方式了,风筝带着他们的心在天上飞,虽然他们被禁锢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小方格里。跳格子的孩子是不懂的,在他们心里,从这个格子有计划地跳到下一个格子就是胜利。人的心究竟有多大啊!想在这个城市有一个格子属于自己,又想整片天空是自己的就好了。他们不懂,飞上天的风筝又怎能在地面上占据一个格子呢?占据了一个格子的风筝又怎能飞上天呢?
一片云朵的影子坠落在地面,被南来北往的车轮碾碎了。
或许我更喜欢夏天,夏天的主旋律是晴朗,每每热浪扑面,我就会被提示自己是在红尘人间。有雨,只是阵雨,有风,只是阵风,有云,只是为了装饰蓝天,我会安心于时光的流转。然而,秋和冬却总是给我骚动。
被树阴遮蔽的天空一旦被展露就会刺伤我的眼睛,我那已然退化的翅膀就老想扇动,虽然它早已成为我身体的一件装饰品,诸如我的脚链。这会让我很悲哀的,我知道。
日子似乎很空洞又很丰富,跟这座城市一样,说不清到底是空洞还是丰富。每天努力工作,勤奋学习,隔上几天就会有人对你说“我喜欢你”,该来的来,该去的去。如果你不想失身,那你也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了。朋友?女人,都在男人的怀里,有谁会愿意离开自己的温柔乡陪你呢?男人,是做不得朋友的,他们只想跟你上床而已。算了吧,这世界谁不是一个人呢?表面上,相依相偕的,好像真的能够相伴到永远的样子,可是,怎么可能呢?永远到底有多远呢?只不过是暂时的一个伴儿罢了。大家在这条路上碰见了,同行了一段,到下一个路口,还不是你东我西?然后,在下一条路上,你或许还能碰到另外一个人,因为孤单,再结成伴。在下下一个路口,又你南我北了。谁和谁能一生一世呢?
我觉得我是在等待,等待刀农回来,或者刀农改变,应该是改变吧。我确定刀农是不会再回来了,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局。时光就像一把刻刀,它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雕刻出它想要的东西,所有不够坚硬的都将被刻画。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雨天,我已然忘却了如何用笔来表述自己的心情,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能够。
刀农打电话说春节回来。我说,“今年春节我必须得回趟家看看父母了,不如你也回趟版纳看看父母吧!”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回去。”我说,“再说吧。”
成都应该还是绿树青天的,冷是冷了点儿,但还不至于落叶。刀农说很冷,阴冷阴冷的,快要把他的骨头都冻碎了。如果这时候他在北京的话,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呢?在暖气没来之前的这些日子,谁不是畏畏缩缩的,像只乌龟,没事儿只想晒太阳呢?这个没有见过冬天的孩子,今年一定大开眼界了。
不知道自己整天都在忙什么,除了工作,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了,各种各样的书,甚至杂志、报纸,电视却戒了,总觉得耽误时间,没完没了的电视剧总是引诱我每天像个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一坐几个小时!所以,在我看完某个电视剧之后,就狠下心肠,戒了!但是,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广告栏不是更浪费时间吗?唉!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只是天上地下地看着。
我又开始喝酒了,有时候是跟老板出去喝,有时候是自己去酒吧喝,有时候也在家喝,边喝边看书,然后醉醺醺地倒头就睡。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来到北京就开始失眠,可能是夜深总不能人静的缘故吧,半夜里轰轰隆隆的车轮总是搅得我不能入眠。干脆给家里买了一个蓄红酒的、很漂亮的酒架,这样可以同时摆放四瓶干红,还不至于碍眼。我讨厌去超市,超市里货卖堆山的架势令我眼晕。
生活就这样不咸不淡、不紧不慢地向前滑动着,只是滑动着,毫无意义地滑动着。
我跟刘冬说我搬家了,新的住所没有电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了,就是不想说了,没有原因。所以他也只是偶尔打到我手机上问候一下,隔三差五吧。所以,整个晚上都很清静,只是我一个人的了。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
既然我不能带给别人幸福,那就不要带给别人痛苦,就让我存在着跟没存在一样吧。
第四部分:风往北吹繁荣的生活背后
2000年12月12日 晴 繁荣的生活背后
阳光很清冷地透窗而来,就像不存在似的。
我添置了几件冬装,虽然我并不想添置。早晚我会搬离这里的,而越来越多的东西将会给我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现在,我已经是总经理助理了,在我工作成绩被肯定的同时,我的智商也被验证了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我整天穿着那件破旧的滑雪服去上班是不是太对不起老总了呢?也对不起广大的人民观众吧?老总一定会问我,给你加了薪,还是不够买件衣服吗?我也不想给任何人巴结我的机会,无论是老总还是谁,“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还不想稀里糊涂因为几件衣服就让别人上了我的床。况且,即使你捉襟见肘,经济紧张,也没理由让别人出来吧?城市生活其实真的很累人,好像连活着也是为了别人,那么,要自我何用呢?所谓的自我,早已被城市人演绎成了“自私的我”的代名词,早已与其本意无关了。难道我不是这样的吗?原以为我是为着自己的理想才离开刘冬的,现在才明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我还不能够真的爱他,又怕他的爱约束了自己,所以才逃跑的。和王昊离婚,说他有外遇不也是一种借口吗?难道要一个不爱你的人忠诚于你?可能吗?而李明清,原本就是为着那几封情书而存在的,情书都没有了,情又依据什么而存在呢?他,或许应该算作我心中永远的痛吧。后来,我到了昆仑山口打电话给他,他一听是我,就挂了线,无论我怎么打,他都不接。竟然不听我说完一句完整的话!即使还心痛也麻木了,现在又想起他,说起他,写到他,连一丁点儿的心痛都没有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即使曾经有爱,如今也烟消云散了。或许那根本不能叫做爱吧,是爱就不会忘记的。记忆怎么可能像匆匆的步履一样不留踪迹了呢?连他的样貌,也早已是完全模糊了的,曾经的情书,那些缠绵的话,谁又能真的记得呢?
刀农的电话越来越少,和先前预料的一样。他算是我疲惫旅程之后最温柔的一笔回忆了吧?而在别人眼里,我是那样一种不苟言笑、勤恳努力的职场女人,不懂风月,不可理喻。我想,今后也不会有人如此诚诚恳恳赞我如花了。现在,每一句赞美的背后语都是:你能否脱下衣裳来,让我看一看你是否真的如花呢?
三十岁之后才明白,谈情说爱的年龄真的过去了。即使有心找个男人嫁了,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