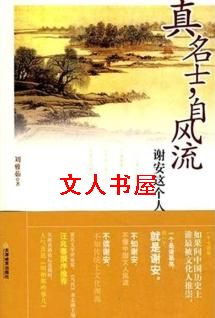要一起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久,仿佛自我宽慰般的,不知是为了制止我此刻心中的忐忑以及深切的恐惧还是反过来安慰身旁的少女,我有些想要逃避般地轻声喃喃:
“是么?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移换骨髓也未尝不可行啊。你哥哥不会那么轻易就死去的。”
仿佛知道这个理由连自己都无法说服似的,我的话语音量调得很小,宛如蚊哼。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嘴角甚至不忘记轻轻拉出一条僵硬的弧线。我想那时我的笑容有些扭曲。
仿佛再也克制不住般的,少女的眼中此刻已充盈了晶莹的泪光,声音都有些颤抖:“你的血型……是‘Rhesus Macacus’!”
“是么”,没有丝毫惊讶地,我随口接话,神思仿佛却已飘向很远的蓝天、碧海。
其实我早已知道。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在我回答的一瞬间,她也明白了一切。
她避开我的目光,独自拧门出去,步出房门的一瞬,她丢下一句话:
“天亮了,你妈快过来了,她会留下来照顾你。”
十、母子
父亲建议我暂时休学,已经不再年轻的妈妈希望我能多些时间陪陪她。妈妈正坐在我床头柔声细语地同我说着话,厚重的腮红粉底的遮盖下是她苍白几近没有一丝血色的憔悴的慈母的脸,和那双明亮温婉奕奕闪烁着慈母的光华的眼睛。
母亲就这样坐在我的床前对我微笑着讲述那一个个仿佛在很遥远的昨天曾经发生在那个小男孩身边的故事。母亲和儿子的故事,平淡但却让人感到温足。
我宛如十多年前的那个孩子这么依偎在床前细心听着她的每一句话语,脸上浮出安然宁静的笑。面前那张脸已不再年轻,眼角悄悄爬上几尾皱纹,在厚重的粉底的遮盖下亦毫不留情显露出岁月在她脸上刻画下的印记。
我知道明知是那么微渺的一点光亮,母亲仍在努力为我寻求那最后一线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为此她已身心力乏,几日几夜没有阖过眼。
我怎能不体谅她,不肯满足她这一点慈母的平凡而渺小心愿?这或许是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最后所能够给予她的作为一个儿子的敬爱和理解。
母亲一直是这样一个女强人,在事业上独立撑起一片天地,不需要倚仗男人,也不需要多余的感情的牵畔和束缚。然而最后连心的母子亲情都要离她而远去而她已没有能力挽留的时候,她只能这么看着唯一儿子的生命一点一点在指尖流逝,仿佛感觉到不远的将来眼前这生命最为重要的亲人就要这么在自己的目光注视之下永远地闭上眼睛。
多年来对家庭的疏忽,无限愧疚以及自责的泪水的蔓延在晨曦的曙光又一次划落我病房窗台的一瞬被一道有力的开门声响打断,一个熟悉的男人身影出现在妈妈的身后,是家里的男主人,我名义上的父亲。
“烨,董事长说你今天再不出席股东大会就……”
“妈,你去吧,不用担心我,我们以后日子还长呀。”劝慰般地,我冲着中年的母亲淡淡一笑,凝视着她的双眼,嘴角轻轻一撇,眨了眨眼。
母亲会意,有些感激地轻轻抚摩着我的头,我感到有几滴湿热的液体顺着她的面颊滑落我的唇角,掺杂着淡淡的苦涩和温暖的触觉。
仿佛在安慰一个孩子般的,我拍拍母亲搭在我身上的手,笑笑:“妈你放心。”
我看到母亲舒展地一笑,感叹般自语:“我的小曦明终于长大了。”在舒展开的笑脸下,我看到那一对眉头仍是紧锁着,仿佛她不曾安宁片刻的担忧的心。
十一、情动
梧桐树叶最后一片叶子也已凋零,萧瑟的街道旁站着一个身穿啡色毛衣的年轻人,他的身旁是一个身披白色风衣的少女。
少女长长的衣袂在风中飞扬,淡青色的围巾随风舞动着轻轻拂过年轻人的面颊,掀起一阵轻柔和煦的风,在深秋的夜里。
年轻人的脸色有些苍白,嘴唇干燥而没有一丝血色,伴随着是病态的憔悴,眉头紧缩,眉目间是冷凝的忧郁。对面的女孩没有说一句话,纤瘦的手掌正捧起一个精制的礼品盒,缓缓解开彩带,从里面掂起一个精致的水晶塑雕人偶。
是一对男孩和女孩的水晶塑雕人偶正携手立在少女小小的手心上,依稀能看到它们脸上闪动的简单而纯粹的笑意,面朝着自己。
男孩与女孩的手心间仿佛有一道小小的、细碎的裂痕,虽已粘合,但仍然有着那样明显的裂隙,在他们之间。
“既然摔坏了,就扔了。”年轻人凝视着那小小的水晶雕塑,缓缓道。神情深邃而有些凝重,表情落寞而萧索,仿佛在那一瞬想到了很久以前的往事。
“虽然有裂痕,但已经粘好了,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让他们越来越远离。”少女的表情是沉静的,语气是慎重而坚定的。说这番话时,嘴角洋溢着一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微笑。
年轻人许久没有说话,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仿佛正刚刚想好要如何开口,少女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薄唇轻启,飞速地发出了第一个音节,年轻人便知道再也无法阻止她的决定。
“其实那天,我很伤心。我不喜欢看到你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更不想看到你接受别的女孩子,我希望一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陪在对方身边的,都是彼此。我希望可以一直陪你走下去。”
少女没有低头,说这番话时脸上甚至没有半点红晕,眼神是淡定而坚决的,明亮到有些逼人的目光直视着面前的年轻人,让他一瞬间感到自己无法逃避。
年轻人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然而这一瞬,却让他迟迟无法做下决定。
面前的少女依然凝视着自己,毫不退避,在那样的目光逼视下他感到自己的眼睛一旦对上对方的双眼就无法抽离,而那样紧迫的压力让他心里清楚无论怎样必须尽快做出一个决意。
街区的街道是沉寂的,只有风声在瑟瑟地吹舞着凋零的梧桐树枝,一辆出租车的催鸣声响打破了这片刻的迟疑,在少女全副心神都集中在观测着眼前少年急骤变幻的面目表情时,车轮自她背后擦身而而过,只是一瞬,她感觉自己的衣袖正被一双纤长熟悉的有些湿热的手大力一拉,身体则随着惯性踉跄着带出几步远,来到少年身侧。
雨后初晴的街道旁的凹地中积留沉淀的污水被那飞离而去的出租车带起的点点水珠溅满了少年男女的一身,出租车上飞离远去的司机不忘在车开出约20米的距离停定住,打开窗户破口大骂:“小孩子找死。”
大杀风景的家伙啊。
年轻人都没有出声,少女感觉到自己此刻有些沁出冷汗的手正被另一只略大而单薄的手掌紧紧握着。一向沉着淡定的她在那一瞬感觉自己的另一只手正不受控制地紧紧攥着风衣宽广的袖口的夹层。
眼前少女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红晕,眼波下那双秋水般的剪瞳闪烁着宁静而耀眼的光华,那一刻,少年的心蓦地一动,情不自禁地,缓缓抬起手,撩开少女额上散发,嘴唇轻轻覆了上去,在少女光洁的额上留下了无形无质却伴随了一生的印记。
十二、缘寂
在平静地等待死亡的边缘又徘徊了一年,这一年百无聊赖的有些枯燥和空乏的生活让我在终于得到母亲首肯后重新回归于校园。
我并非是爱那里的多彩的校园生活以及朋友间相处的乐趣,只是因为我喜欢学习。喜欢如一尾灵动的鱼儿在夕阳如血般洒遍图书室内、落日前昏柔的余光正透过微微敞开的明净的窗栏投射在室内的每一刻静静捧书独处一隅,思维随心所欲自由徜徉佯于这片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域。
当夜幕渐渐拉开,天色完全黯下去之时我则会按照惯例收拾好书包跨出校门,乘公车去上大接我挚爱的我的妹妹,然后一起回家——三个月来的大学生活,同我一般的,她过着走读的生活。
日子便如此一天天过去。平淡,却让我感到安足,仿佛身边的亲人包括我自己都已忘记我患下的是绝症,我感觉到幸福,正伴随着我每一天。
然而这如此简单的、平淡的生活却不肯多做停顿,在我迎来二十岁人生那年的某一天将一切都打破了。
那天出乎意料的,在校园门口我没有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刻一种莫名的强烈而不安的预感在我心头燃起。
我飞赶回家。然不知是不是错觉,那天的天空仿佛特别低沉,天色有几分说不出的阴郁,宛如我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巨大转折的命运。我的预感并没有差,在我推开家门所听到的一个噩耗将我坚实如铁的心瞬间冲跨——我的继父,家里十多年来的男主人因为车祸脑骨碎裂,在送院途中已然不治身亡。
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下意识地,我望向厅里沙发上失神坐着的落魄少女,少女的眼神此刻是空洞的,隐含着某种绝望。
母亲正哀声载道埋怨我那不负责一走了之的继父,隐隐含着哭腔。父亲近些年为家中劳心劳力,虽然与我一直感情较为冷淡,可我知道他爱我妈妈的心并不比我亲生父亲少。那一刻,我竟有某种想哭的冲动。
虽不承认,但十多年来的朝夕相处中,我已逐渐接受这位家中的男主人,并不知何时起已将他完全当作了我母亲的丈夫——或者是我的父亲。多年来,基于对母亲的理解和尊重,对作为家里的另一个长辈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某种无法明叙的温情。
然而那一刻,得听这个噩耗之时,我的心在瞬间仿佛被针猛扎一般剧痛,这个看似平淡、平凡的家庭终究是破碎了么?那个噩耗所带给我的打击,甚至分毫不亚于在我得知自己患下的不治之症的真相。
我就是这样一个会为一只鸟儿的折翼而黯然神伤的没用的孩子,何况那个男人还是家中的男主人,更是我的父亲。并且,他还是那个少女在这个世上唯一可以依靠、算得上亲人的父亲。
送殡的那天天空很阴,然而没有一丝雨。我看到她的眼睛很红,却没有一滴泪。整个殡礼上她都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一个面部表情,只是呆呆站在那里,眼神空洞而萧瑟。她是爱着爸爸的,正如爸爸也同样爱着她。多年来在这家里,爸爸对我们的关爱是平等而仁慈的。
无数深沉而悲痛的、怜惜的种种柔软的情感瞬间充塞了我的心,在我看到她那孤寂的身影。那一瞬我甚至有种想要给一个承诺可以一生一世照顾眼前这娇小而单薄但却如寒冰般坚忍自立的少女的冲动。
那一刻我甚至忘了,我本是一个活不多久、时时将要准备着面临死亡、徘徊在生与死边缘的人。
只是那一刻我竟然忘了。在回去的路上,宽慰了妈妈,我走过一路上沉默不语、已多日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的少女身畔,走近时,缓缓地用了只有我俩才能听到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低语:
“别再伤心了,我会一直、永远地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仿佛没有做过思考般的,自然而然,我说出了这番心里的话,尽量平缓着自己的语声。尽管此刻我们的心情都十分低沉、压抑。
然而答覆却是出人意料的,仿佛感应般地,我觉察到她的神情此刻有些异样,不自然地,我抬头凝望着她的侧脸,瞬间心中惊骇莫名,她此刻正冷笑着望着我的眼睛,唇齿轻启,吐出一句冰冷得近乎完全陌生的话语:“哦,是么?‘永远’又是多远呢?你还能,陪我到‘多远’呢?”
她的眼神带着几许轻蔑,唇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仿如-盆冷水对我当头淋下,瞬间将我淡忘或者说逃避了许久的这个恐惧的阴影毫不留情地重新逼近在我此刻本就处于极端低谷的心。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她的眼睛,甚至期待着她能给这样一番摸不透原委的话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忘了这本是事实并不需要解释,然我只是想听她亲口告诉我忽然转变对我冰冷的态度的一个解释。
然而却没有,她已不再看我。那一刻她的态度冷硬得仿如她身边的年轻人只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男子,而她的那番冰冷的话语瞬间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从未与她相识。似乎,这弹指间所发生的一幕已毫不留情将我们这十多年相处的点点滴滴全部抹去。
眼光从她身上抽离的一刻我才感觉自己所有的信心与面对人生那最后一线希望已跟随着她那一抬头间的冷笑与一句冷若冰霜的话语在瞬间崩溃瓦解。
再没有多的言语,心中黑沉沉的大石瞬间碾为齑粉,消融在我的每一处血液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而乏力的绝望,毒蛇般噬咬着我的心。
十三、缘散
短短一个星期,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破碎了又瓦解,在某一个黄昏的下昼。
少女的动作没有片刻停顿,此时正单手拧开了家中厚重的大门,她的另一只手正提着一只黑色大箱子,箱子里空空荡荡叠放着几件旧衣物,那是她仅带走的行李和全部的家当。
仿佛再也按奈不住般的,少年快步奔上去,修长的手搭上了少女细弱的手腕,抱着最后一线企望做出了已重复第十七次的挽留。
每一次的挽留,换来的都是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