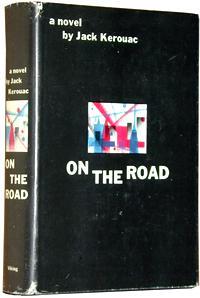跌在路上-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那时高乌再此得到三伍的告诫,他应该阻止这样的好兄弟撩弄他的吉它,那是三伍生活的全部希望所在,如果它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然而所有的规劝哪怕束令都只是转眼消谢的一滩泡沫,恳请那吉它的主人不要专往坏处想——高乌用人头去保证好兄弟们绝对不会损伤它一根毫毛。
尽管这也能或多或少给他带来一些蔚籍,三伍至少认为纵使那吉它有损毫毛,但仍对它整个生命的安全抱有一点希望。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他脑海里不时闪现那群高乌的可恶狗友——他们不仅仅是居心叵测的小偷,还时时青面獠牙,他非常担心自己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们在高乌的开门缉盗之下把那吉它拐走。事后他们一定伙同献计说那是被他人潜偷的,他们一无所知。高乌也一定会无动于衷甚至装癫扮傻地使事情一了了之。他们简直就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无一技之长的社会残渣。
三伍已经告诉我,高乌是如何搭上那群家伙的——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几天过去,高乌不但没有对好兄弟警示一下,纵容程度反倒与日俱增。他们显得很过份——有人竟与高乌“横霸三席”地在那里赖上一宿,他们有时全天二十四小时没有离开房间,鬼鬼祟祟在商量着什么。有的看起来跟高乌一样软弱无力。高乌继续像一只受伤的笔尾蠓那样撩着腿。他们无人显得有任何事情可做,时不时翻着白眼朝着天花板瞥去。有时在三伍的眼皮底下他们的故作懵懂的神情几乎等同于那仍能发出声音的一息尚存的吉它已被无情地拎走。
三伍又再次不计生死地对高乌发出警告,他简直在引狼入室——一切恶果都应出于高乌之手。三伍成天感到忐忑不安,不再拥有安静的环境练琴,先前哪怕仅有高乌一人在哑哑自语的时候,房间里仍能响起优美婉转的古典之音。可如今却化作致人癫燥的嗥叫,这种可恶的声音在高乌的无限撺掇之下永无息止。
后来三伍竟轻言细语地对高乌说,现在他连给那三只学生上课都无法进行,叫他如何生活下去。高乌立即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做出前所未有的虔诚端庄的样子,立刻发誓从第二天起就永远叫好兄弟们滚蛋,永远也不会在房间打搅三伍,让三伍安安心心地像以前那样生活——努力练好吉它以及当好别人的好老师。
三伍似乎从此看到希望的曙光。有时你们有必要努力去相信海盗的话语——你们一定能够抵达幸福的彼岸。高乌也毫无虚假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第二天起,他们果然从房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连那苟延残喘的高乌本人也一同烟消云散。这并不能成为得到宽恕的理由——他最好永远也不回来,他的恩将仇报已使三伍对他的热情与恻隐之心荡然无存,世上再也没有谁会对一个无赖中的无赖继续和睦相处。为了自己那“理想”三伍拥有足够的理由不再欢迎他,不再考虑他的颠沛、凶横、虚脱,不再怜悯他的病困,任凭他在这个城市的街巷旮旯猝然摔倒。在这一点上,你们尽可能地视关三伍为知己。
尽管从第二天起,高乌已经自力更生地消失了一整天,这已完全让人相信他再次扬起生活的风帆。我们早就应该如此懊悔地说,高乌原来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带领一群别样的混混在社会上支天撑地,他们也许正在快马加鞭地奔劳于某一“兴旺的事业”中。一旦我们真的到达了那幸福的彼岸,我们就应该尽量希望善良的海盗一帆风顺地远去。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自从第二天起,高乌依然背着那牛皮袋撩着那软腿返回窝巢。
接着就零星地来了好兄弟们当中的一两个。紧紧再过多一天,他们又一次蛇鼠一窝地在三伍的房间里鬼鬼祟祟商量什么——把“大事业”运筹帷幄。这显然要与高乌自许的“绝对保证他们不再来”的誓言相去甚远。
他们继续不知好歹地抚弄着那古典吉它已使三伍的灵魂落入深渊。他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对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连那条长期以来凶横已久的撩着软腿的寄生虫也一同无情地驱逐出去,就像驱逐牛鬼蛇神一样。
后来似乎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压迫他们似的,他们的滚蛋变得非常友好和乖巧。高乌也没有显露出一点愤怒与恶意,拎着少许属于他的杂物——一个装有鼓棒的牛皮袋吹着口哨离去。他们是否真的能彻底离去……
再后来他们全部都没有返回——这是钢铁的事实,三伍的吉它也因此得以起死回生,在往后的漫长日子里他继续抱住它朝着理想的天堂阔步而去。
第二十三章 01 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二十三章01新官上任三把火
从现在起我就开始藐视一切,我打算搜索枯肠去圣化我的生活。你们在我身上显然注定一无所获,倘若你们丝毫没有动摇内心的初衷——在“笑柄之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就该继续鼓起勇气沿着我的踪迹追索下去,在道途上我会宽恕你们与我化友为敌,同时又将见证你们夹着尾巴空囊而归的历史。
而所有人也没有因此悔过的意愿,更不空囊让命运握控在他人手中,有时你们已经进退维谷了。无疑此刻诚信将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们的忠恳与我的虔诚将珠联壁合。当我生活的诚信已经岌岌可危——友谊走向破碎、理想自我捣毁——当一切已成定局,到时候,你们再阴森地抿笑也不为过。
实际上,你们已经弄懂我是已一个衰蛋班长来酿造定局,你们就比先前更阴森一些。在那整整一年的衰蛋时光,我并不因此而拥有大伙期望的“可观”的德行,事情原本就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他们硬要把一条在陆地上栖息的菜花蛇撵到海洋里游窜于珊瑚礁呢?
到头来所有自我消沉都不能表明学院对个人茁长的徒劳无功,在你们的“教诲”下,我已将学业定夺为——不要为怎样去逃避而劳神费心以及不应该去为“为什么会劳神费心”而去劳神费心。一有事情要做:宣读一张通知单和告知一个任务,它们就会被我语无伦次地公布出去。一旦他们对我在这种状态之下所表达的内容稍有了解,这才宣告我已大功告成,从每个人的眼神中可以证明我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至今我仍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处理得非常妥当,唯有“暂且挪用一下全部的班会费”这一行为成为美中不足。在这一年之内我所做的——诸如在天冷时给模特弄来烤箱,跟着辛老的尾巴去筛选衬布——我并不想在这种事情之上立下辉煌的功绩,问题的关键在于顾老和黄老一直以来都没有弄清,我就是那个率先抵达火山口的衰蛋。
在那段日子,我并不变得充实——只有短暂的光阴,简直就是昙花一现——除却几个不识时务的女生,无人不对辛老的初来乍到感到兴奋不已。事实上他很快就与我们打成一片,而我一下子就生出骑在他的肩膀上玩耍的诡想……某一天,当我们偶尔发现自己变得不正派以后,除了读者们的肆意唆使,还得把一大部分罪恶归于那个魁梧的来自东北的家伙。
我希望你们用对待雨后牛蛙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这位老师,诚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讲师,这比你们认为他是一位教授要开心一些。更多时候,他是一个呱呱乱叫的唠叨鬼。
“你真神了!咋整的,过来一起喝啊!”
“……”
“这——这,你干嘛呢?真神了!”
“……”
“我太累了,先睡一下。”我说。
我独自躺在模特台上,他们却攒聚在门口那边举杯畅谈,在还没有人会把一杯酒喝完的时候辛老就在他们面前鬼话连篇、口喷酒沫,还不时向我睥睨过来,似乎立即要把我定夺为一个卓尔不群的家伙——时不时又喊我一声:“真神了!过来喝啊!”
“……”
但愿没有任何人对我即将打一个瞌睡造成任何一点影响。他一定醉了要不然怎么会麻木到连这一“瞌睡”对我的重要性都不懂了。
“你怎么了,神了!”他还显得如此顽固。
究竟这一切怎么了——他为什么在还没有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就显得刺刺不休,久久没有停止。
在我成为衰蛋的那段时光,这种莫名其妙的刺刺不休竟来得更加厉害一些,就这样永永远远也不能停止。
我感到一切真不可思议。只要你们还能竖起贪婪的耳朵,我立刻可以自豪地说,我与辛老将能成为忘年知己直至日后无论多么漫长的岁月——哪怕光阴苒荏,那一“罗嗦”依然顽固地使这种友谊变得固若金汤。
然而,你们应该大胆地说:“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一个笨蛋对一个蠢材谆谆教诲。”
从我刚刚“执掌班权”的那天起,他已经开始枉费口舌。当宿舍的电话响起,我就会做好从上铺跳下来的姿势,迅猛地把话筒放到耳边。他在电话那边欣喜地露出鳄鱼牙:“真神了!恭喜恭喜!你……”
“……”
“你可真神了——说明你有能力,得到大家的信任呗,嗤!你真神了!好好干吧!”
“你真神了……”我说。
他立即把话打断:“哎——呀!你神了!以后起床的事情——就由韦弟叫醒你呗,不必担心这一点,你一定会改变过来的,是不?”
“真神了!……”
从此以后,勤奋的韦弟得到辛老的通牒——每天早上一定按时、万无一失去地把我叫醒,千万别让班长频频上演迟到缺课以及早退诸如此类的闹剧——这些,甚至可以断定若果我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最突出的体现。同时我也已清楚,你们开始对韦弟恨之入骨。
02俄罗斯模特
你们接着会憎恨院长大人,以及教务处处长——如雷贯耳的顾老。因为你们已经听信谣言——自始至终认定辛老是学院里里外外“领导的宠儿”——立即把学院里的一套房子信手拈来。你们气愤地说:“这一切得益于他与院长大人关系的非同一般,他的工作调动离不开顾老的‘一手操办’。”我说:“日后依据辛老自身的绘画功底乃至艺术造诣,从画展画作中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应认识到,客观上是学院需要他——美术系需要他和以及他需要学院。”
他与其他教授相处得非常融洽——见面相互言笑,跟黄老也是这样。只因他还与区美协主席是多年之交,这使他在摸清我们在李老板那里所捞得的全部财富的难度上不费一点力气,甚至还把我们说美协主席的坏话统统暴露出去。
至于一开始就“信手拈来”的那些东西——从那时起,连同辛老一切生活所需都有必要从头再来,我们彻头彻尾认定我们与辛老共处的快乐时光几乎等同于他得到那套住房后并开始为它摸爬滚打的全部历史。
远离“战火”的你们安然无恙,我和韦弟却每人手执皮尺的各一端,揣度每一个房间的长度宽度以及高度以好让他更好地为摆设家私和装点墙面处心积虑——他本人的作画空间乃至电视机的位置经营。还有一个需要向木工师傅量身定做的大书柜,他需要付出一亿倍的努力去为之煞费苦心。有时,我愿意躲在冶炼厂里寻求安静——关于那大书柜在我耳边被无数次提及所带来的千万分贝的噪音已经对我那脆薄的耳膜造成了不可挽救的伤害,连同他睡房那墙上的一个装配空调的小洞口——它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重视,所有对由此引发的问题的应答彻彻底底地使我喉干舌躁。
我将进一步觉察到这家伙对崭新的生活充满无穷无尽的希望,哪怕大书柜已经久经阻挠地成功地被挪回了自己的房间,并且已经显得落落大方,但这并不能说明希望从此就到了尽头,即使半年后那可恶的空调已经被装了上去也不可说明。
如果有人问:“他缺少一枚螺丝钉怎么办?”答案是:“兴师动众——率领全班人马搜街刮店。”我想,倘若你们都能类似地倾出一点心血,是否比花精力专门去嘲笑他人好一些。
辛老对生活的谨小慎微还表现在其大寸幅的油画作品里。那时——在红楼还没有化为废墟时,我们不须去想象他是如何长颈鹿般站于画架前,他的口若悬河又是怎样去把他那表粗外犷的另一面赫赫呈现——当你们看到其画架上的那幅人体作品,你们的嘲笑之箭将无缝可插。诚然,哪怕我没有亲耳听到他们乃至一些教授在审视那画时所发出的啧啧之声,这也不能更大程度地淡化我对那幅人体习作深刻印象,当我偶尔变得懵懵懂懂的时候,便差点把对那幅画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记全归功于那裸露的侗体出自于一位全新的漂亮的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