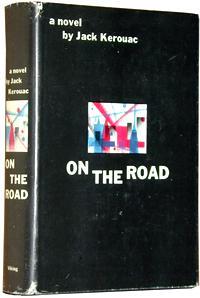跌在路上-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过几天,榕树下的高乌仍然保持着那冬眠的样子,先前说的“有大差事等着他”即便成了一腔废话。但我总是无法抑止对其极力妥协——他显然把那“大差事”的得手的日期整整推延了一个星期,一旦这七天过去便十拿九稳地投入工作。为了使这一事实的嫌疑度降至为零,他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来龙去脉一一呈现。
那是多么值得期待和引以为荣但又多么艰辛且日薪比跑场还要多得多的工作:每天清晨四点准时起床,连脸都来不及洗便屁滚尿流地跑到海鲜市场那里去。在那里等待一辆大货车的来临,之后就非得把人累死不可:一大桶一大桶的大闸蟹和花虾就这样被高乌从车肚里承卸下来,筋疲力尽之后立刻把它们分量装到泡沫箱,这个工序必须精挑细选,麻烦透顶。完后就加冰充氧,调配盐水的浓度……有时还要打干氧——这样更安全一点……这一切势必用去六个小时以上——一旦中午一过,高乌只能花一点时间用来吃饭。奔命的时刻又将开始:把一箱箱装有大虾硕蟹的包装好的笨重的泡沫箱抬上一辆小货车。高乌因过度的用力而发抖之后,便立即随从那小货车直奔到一家火车托运公司去,在那里煞费苦心办完那些乱七八糟的手续后就把货件搬转到另一辆卡拖货车上,他又要立即跳上那车摇撞到火车站里去……
很显然,一个没能对此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就绝不能置身在这一差事中。高乌已经十拿九稳取得了最虔诚的信任(除了你们依然与他讥诮相对),所有人都应该为高乌即将在病困中东山再起而感到高兴万分,连高乌都在对自己羡慕不迭我们还何必站在那里愣头愣脑,又何必带着哪怕一丁点疑虑去待守一个星期之后作出验证——高乌是否已经实实在在地驮着海鲜在这城市里来回穿梭?
可无论如何,过了一个星期甚至再过几天,高乌仍死皮赖脸地趴在石桌上的事实已经告诫:我们有必要对自己一时冲动而作出的信任之状拥有悔过自新的权利,甚至一开始就不应该故意深信那些荒诞无度的鬼话。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然没有发现高乌拥有那份差事的蛛丝马迹
第二十章 01 质的飞越
第二十章01质的飞越
在一个毛毛细雨的中午,许多人悄悄地把雨伞打开然后从榕树底下走出来,倦气沉沉的样子——他们应该继续在荫蔽之处谈笑风声而不应该往宿舍歇息而去。许多人从饭堂里走出来撑着伞,拖泥带水地走着。还有许许多多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春天的午日的美好——一切都显得如此滋润、清新爽朗,这一切都被惰性成癖的人群视为催眠的软枕。他们也没有立即返回那教室,而是行色匆匆地往宿舍那边走去。所有人的行迹总是殊途同归,唯有那个痴情的魅力十足的男生没有陶醉于那催眠的软枕,一切时间都应该用来酝酿一个可靠的时机——他威风地断定(数算)在不久的将来或者一下子就可以将爱情得到。
可她为什么竟循规蹈矩地随波逐流,一不小心就已埋进那催眠的软枕。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春天的一切时间交给小尬,如此浪漫的季节她为什么没有蠢蠢欲动。如此浪漫的季节他一个人驻守在这幽寂的画室,时刻在期待一位心爱女孩的悄然到来。
两眼干巴巴地呆视着什么,也没有感到自身的可怜透顶——他只颤耸起那灵敏的耳朵,洋洋得意又小心翼翼。那时他手里执住一把锃亮的油画刀,把颜料一团又一团地刮到画布上。起初他清楚用什么颜色来表现什么,后来就弄不清那是什么颜色以及表现些什么——一些凭空涂抹而成的古怪形状甚至已经再次全军覆没,而那画布早已成为一块肮脏的调色板。他反而为此高兴,随即走到窗前凝神观望——榕树底下到底有谁在干什么,石桌周围空无一人,远处的屹立在校道中央的那生殖器仍在雨中目空一切。
他顿时变得力大无穷,无法忍受窗前树叶沙沙呻吟的渺小之音,必须凶猛地号叫,周围的幽美恬静一定因此全然销毁。他忍禁不住要嘶声大喊,这样一定被视为正午过后的悲鸣。不仅如此,心爱的女生十有八九于红楼之外放耳谛听,一定认清那是小尬不成体统的咆哮。只有自我惩罚地搓拳捶胸,面红耳赤。
他想紧紧抓住一把空气,使它们成为一个大铅球那样然后被狠狠地往远处掷去,把地面炸成一个大窟窿。身上的能量无法骤然消散,他猛然蹦跳几下,像个神经病人一样,画室因此而微微摇晃。所有高高耸立着的画架和零乱排列着的椅桌,一切一切东西——它们统统败倒在于地、一塌糊涂。他突然感到疲惫,两眼冒闪着星金点点,慢慢地、慢慢地回到画架面前,坐在椅子上,愣视着什么——整个画室昏暗起来,画布上已是一片灰涩、稳晦无光。他轻轻地肉揉弄着双眼,不停地眨了又眨,渐渐地,眼前的一切才变得模糊可见。
他继续耸起企图聆听外面一切天籁之声的耳朵。那时,他突然感到一种内心的新鲜的躁动,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哧哧哧地从窗外传来了声音,小尬一下子变得坐立不安,那个时刻太令人怦然心动——一定有人穿着布鞋从檐廊那里走过,没有步伐喘急的可疑,像一走到门口就要突然停止。
小尬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神速地拾整一切——发型迅速凝固。那熟悉的脚步声没有尽快地消逝远去,就停留在画室的门前,似乎即将朝着小尬的身体逼近,甚至那将成为一种颇具威胁性的袭击——有人在门前透过门缝窥探什么。他已做出小心谨慎的表情,看起来显得那是一只小羊驼坐以待毙的样子。
门突然吱地一声,要来的似乎真的已经来了。
这一切都在小尬的预料之中——总有一天事情必须如此发生。不是今天就是今天黄昏以及不是明天就是明天的夜幕降临。况且,一切可喜的事情已经发生,就在眼前悄然出现——她就这样迈着轻盈的步履。
可是他总是惊讶地向她瞠了一下,以此来让人感到他的确没有在那里时刻埋伏着,并不是蓄谋已久。
“怎么——”他问,“你不午休吗?”
“今天中午我精神好极了!”她合着手说,那穿着布鞋的玲珑小脚被天窗外的春光照射——她的脸仍处在画室的另一半黑暗,“对了,你在干什么呢?”
“哦!我在画——画一幅画。”他向那画比划着,“一塌糊涂!”
“你还没画完——不是吗?”她微笑一下,“我到外面去写生,你去不去?”
什么什么——不睡午觉的宁丽,你究竟对这男生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致此,恳请你对小尬无动于衷的神情作出宽恕,他必须用一段漫长的时间来仔细给他所听到的真实程度验证一番,他是否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惠然邀请。你要到外面写生去,问小尬去不去,请小尬与你作伴——在春雨的沐浴中你们将拿起画笔描绘美好的风景,你依偎在他身边和骑在他的自行车上,呼呼驶过红楼、草坪、幽廊曲径,其乐融融——那曾是白昼与黑夜无处不在的的幻想,现在竟然变得真实可碰……
对于宁丽的虔诚请求,小尬并没有空暇把精力放在“去还是不去”之上,无论是哪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都是一种非常幼稚的表现,简直就是蠢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到什么地方去写生,在学院里——在美丽的南湖——在城市的任意一角。再次,天空泛着微雨的情况下是否已经准备好一切工具,一定要用一把阔大的雨伞遮蔽写生的画架,以及两个黑乌乌的恋爱着的人的头……一切都被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考虑周全,没有任何一丁点漏洞。
小尬尽量使自己不再紧张一些:“到哪里去写生?”
“在阶梯教室旁边吧!”
“哦——就在南湖旁,那个草坪对吗?”
“对的,”宁丽还告诉他她已把全部的画具都搬到那里了。
“好的,你先去吧!我等一下就去,洗一下油画笔就可以了!”
“呆会儿见!”
她一下子转身就走,可她为什么还要留下那个颤晃着手指的动作,再一次毫无留情地把另一个人放到神魂颠倒之中。他只把那麻痹了的右手凝固在空中,久久不舍放下。本应该就要把它放下来,但他竟两眼眨都不眨一下跟自由女神不可同日而语。他应开始着手做好一切准备——扫视全身遍体,检测是否有任何不妥之处。
而他顿然像个僵尸那样跳起来,傻痴痴地一下子把那油画刀扔到一个角落去,吭吭吭吭地响了半天。衣装进一步整洁无暇和发型进一步固若金汤,什么也没有带上——手握一把黑色的雨伞,把画室大门锁上,然后再像泥石流那般从红楼飞速滚下。
小尬就将风度翩翩地来到——不到一分钟就会飞奔而来,孤单无助的宁丽:一旦他即将走近你的身旁他就会装作威风凛凛的样子请莫见怪——他准备到来,一旦他在语言的表达方面有点欠妥你就不要把他当场捅穿,对读者们来说,最好守口如瓶。
那个时候小尬款款而来的气势诚然能令一个女孩怦然心动。他还表现出了对她的关怀备至——甚至已经带上了责训的语气:“你为什么不撑伞?”并指着那幅画说:“湿了!不知道吗?”然后立即把伞遮了过去,又迅速把草地上的调色盘挪了一下,宁丽也被罩在雨伞的中央,一切都干得非常妥当:“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宁丽默然点了点头,继续一上一下地慢悠悠地撩着画笔。
“你画这间房子吗?”小尬指着前方问。
“不,我只画栏杆上栽的兰花——看,我准备把一朵勾勒出来了。”
很快小尬就对她的画作叹赏不已,随即便眼巴巴地盯着它,表现得非常镇静。宁丽也在专心至志地描绘那花——他们的约定似乎已习以为常。
可是他感到老是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个木桩一样很不成体统,说话时嘴巴离她的耳朵高高的沟通起来非常吃力。但这样他能偷偷地俯视到她那悠然的坐姿、那白皙的脸蛋——它一定被小尬尽情地拥有——总有一天一定能把它亲吻,吻得脸红耳赤乃至手忙脚乱。而你们必须在我的警告之下认真做好“悲伤”的准备。
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像个木桩,甚至已经难以忍受。他看起来像有一群锹甲虫爬在身上但又不敢轻举妄动似的,便不经意地转动着雨伞,水珠从树上啪啪地打在伞上,然后就哧地往四周旋溅而出。可麻木的小尬,是否已经意识到,有水珠已无情地撞到宁丽的画面上。
“快点!”小尬立刻叫了起来,可颜色已经开始渗散开。
“哎呀!”宁丽立即拿起另一支干净的画笔,用笔尖小心翼翼把那可恶的水珠撩走。她不敢用力以免把水彩纸磨损,随后就用一丁点卫生纸把那患处吸干。很快,一切都变得完好如初——两人都面露笑容,而那家伙竟莫名其妙地变得紧张起来,只好慢慢地蹲下——他以为这样便能使自己变得格外平静。
“你累了吗?”宁丽说。
“不不!”他斩钉截铁,“怎么可能会累了呢!”他还故作笑态:“我——我是为了听到你的呼吸而已。”
宁丽立即笑了。
小尬还不断地努力使自己变得不同凡响一些。除了偷偷地用手撩弄着头发使魅力得以保持以外,还毫无保留地把他前几天从土匪那里赚到的外快的具体数目捅了出去。宁丽还必须清楚,小尬还跟土匪他们走进一家豪华宾馆,有厅长、环保局局长、县长等等一些大官陪同,玩得实在太潇洒。
“宁丽,你知道吗?那是我进入大学第一次赚到的钱,五十块!”
“真的吗——太好了。”可宁丽显得不甘示弱的样子,马上又说:“我也赚过一些——”
“是吗——什么时候?”
“去年我卖了一幅水彩画,六十元!”
“哗,你太厉害了。”
“那时我太高兴了!”宁丽边微笑着边用画笔把头发撩到耳根里去。小尬用余光把这些尽收眼底,太妙不可言,只跟着浅笑一下。
他感到她将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落入他的囊中。她——整个人整个“思想”将在小尬的“训养”中茁壮成长,纯朴的更加纯朴以及漂亮的更加漂亮,聪明的更加聪明以及善良的更加善良。小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都将拥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众目羡慕的名副其实的女朋友。有如她把栏杆上的兰花慢慢地呈现一样,小尬的长期以来的梦想也将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甚至就像大马哈鱼一定能成功地随着季节的变动慢慢地抵达理想之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