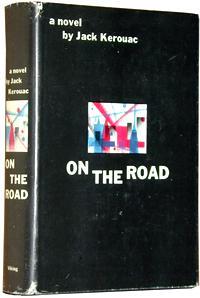跌在路上-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街花店,那里依然使人眼花缭乱。再过一阵我们就暂且停了下来。
“请问一下——”我说,“汤莉回来没有?”
“不在。”
“嘟嘟……”
我再次叮嘱高乌小心一点,我们俩都没有驾照——高乌他可以加快一点,但千万不要双手脱开然后脱下衣服。高乌他逆道行驶。快转车,快快停下停下!
“汤莉呢?”
“没有。”
“……”
可麻木的高乌,这里究竟是哪里——我们就要远远驶出这个城市了。停下!
“汤莉……”
“……”
很显然我们又来到市中心,穿过火车站、一座座桥梁。“高乌。”我凑近他耳边喊,“把那些花领回来,然后‘兜售’出去。”
“我说高乌你听到没有,我已打了足足二十个电话。”我拼命叫喊,“慢一点慢一点,准备没命——你听到没有?那女孩今晚夜不归宿了。”
“高乌高乌,太快了太快了!我的膝盖痛得要命,一有什么差错我就完了。”
此刻你们势必渴望那摩托飞倒于地。而我得马上叫其他女生代领那玫瑰。停!
“请……”
“……”
很显然我们继续在街上纵横穿梭,有时,我又一次对着高乌的耳朵大喊:“太慢了——怎么像头蜗牛似的,快一点,快快!”
高乌就迅速把油门拉到顶峰,我非常需要这样的速度(你们内心也需要),我因此而闭上眼睛,用一丁点时间去想一想,汤莉——那个调皮的女生是如何地从楼上飞奔而下,她把那一大札红玫瑰抱在自己的怀里时是如何地蹦跳上楼,然后甜滋滋得不能成眠。“高乌高乌,你信不信,我一定泡到那女孩,一定泡到。”我就这样闭上双眼喊,任凭外界如何地强光猛射。我并不在意速度、风驰电掣,忘记疼痛。
我还大展双臂。有时,我仅仅偷偷地眨一下眼,看看高乌是否也跟着展臂,一旦还出现解衣脱钮的举动我就势必猛然跳车,这样或许幸免祸死——这有利于我更好地去迎接明天的爱情。自始至终高乌无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亡命徒让我心怀戒备。我甚至忘记速度、风驰电掣,就像要忘记那些闪电般的爱情,忘记日后更多诸如此类的爱情……
第十四章 03 情絮
这就是我所做过的一件并不丢人现眼的事情,我知道,由于我没有在高乌所驾驭的速度下毙命,这就会直接影响了你们的情绪,尽管我仍是你们忠诚的讲述者。当我也自知在某个时候已不能把她们“信手拈来”,就是说我苦寂于没有爱情,你们也会因此心情舒坦一些。为了让大家的高兴程度成倍而增,我姑且编织更多的人(除了你们)都没有爱情,尽管就我们班而言——许多人还会时时刻刻对此抱有莫大希翼。
自从张歪哥在饭堂里遇见那个“饭后用筷子抹嘴”的女生,诚然他曾对她迷恋过一个学期之久,后来,我们就很少能在饭堂见到她,他的希望也就渺茫一片。而歪哥经常跟我们说,只要当时他能跟她聊上一分钟,他就能百分之九十九地得到她。这些你们以为是痴人说梦就算罢。
当我们发现我的“早起的使者”——韦弟跟那国画班的女生分手后,第一个打动他心扉的也许就是那个漂亮的人体女模特,而不是俄罗斯女孩。她二十岁,全身上下白嫩的肌肤并不就是把韦弟深深吸引的原因——与张歪哥一样,韦弟同样乐意在饭堂遇见自己的心目中人,在同一时间,他们都在饭堂里尽情地把幸福分享——不停地滚动眼珠,四处窥望。
很快,仅仅由于我跟他们呆在一起时表现得“无事可干”,为了弥补这一尴尬与缺陷他们干了这样的好事:把坐在饭堂门口售卖饭票的那位阿姨强加为我的心目中人,以致一走进饭堂韦弟就对我说:看!你的卖票情人。
我很无奈于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
刚开始,我以为只用一两天时间就能把这一枷锁彻底粉碎,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已证明那是刊不可改的事。以致在用餐中——他们“搜索情人”的时候,我竟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把卖票阿姨望上一眼,我总拼命转移目光,可又不知为什么,竟一下子明目张胆地往那背影直瞪过去……
那时,无人再愿意看到阿胖与胖夫人的亲密无间,哪怕在公众场合,胖夫人也要紧紧攀附在阿胖的肚腩上,我老实地跟你们讲,他们已到了老夫老妻的境地。即使阿罩同学很少携那个骨瘦如柴的主唱女友到画室来,我也得老实地跟你们讲,他们或许可以生儿育女。
有时,我很想对班里班外的每一位男人说,我们为什么还在闭门造车,不得醒悟;为什么还不尽快地对女生们展开全面的进攻,以致从头到尾都一无所获——还傻痴痴不自量力,有人竟对尹翌莎小姐趋之若骛而落得四处慌逃以及从此一撅不振的田地。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必老是在雷以宽面前刻意把莎莎提起,可这与你们咄咄逼人的目光与狰狞面孔不无关系。
莎莎的辉煌时期使她被置放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位。而你们必须替我保密:就在一年级的时候,莎莎喜欢上一个男生,他有钱以及他长得很帅,风流倜傥以及风度翩翩。刚开始他们俩相互“看好”,后来那男生不再找她了。有一天,黄昏时已人去楼空,她竟一个人在画室里哭了很久。
可你们先不要责怨——这或许是个假消息。有一天,那帮女生透露说:就在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男生看上莎莎,他有钱以及他长得很帅,风流倜傥以及风度翩翩。刚开始他们俩相互“看好”,后来那莎莎不再理他了。有一天,黄昏时已人去楼空,她竟一个人在画室里哭了很久。但我想立即告诉你们真消息,是胸肌发达的雷以宽把她气哭的——你们立即会说:“绝不希奇!”
你们还会急切地说,当时伍小尬那家伙就究竟怎么样了。我立即回答:“对于爱情来说,其他任何人都渺小得像沙漠里一粒不起眼的沙子。”
他发现宁丽对他的每一举止都十分注意,他的每一言谈不再平淡无奇。那种感觉非同寻常,而且,他所雕塑的那个中分式的发型一定光彩耀人。有一天,有人依然感到自身的魅力无穷,在细雨中昂首阔步。旁人抱头鼠窜——她为何还不出现在周围的任何一处,他急切要看到那张天真的脸孔——那女孩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身后,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他显然已在细雨中款款踏步。
她是否已经把这一场景尽收眼底,自言自语,絮叨那只是装模作势的男生的吝啬不已——他对她漠然视之,没有送出那神圣而美丽的《塔吉克姑娘》,他根本没有一点把它交到她手上的诚意,一丁点也没有。
一天晚自修过后,女生们三五成群地走下教室,而她的玲珑背影很快就会消失于一个拐抹处。小尬迅速从一条狭隘的楼的缝隙穿过,那是能与宁丽相遇的唯一途径,没有谁能聪明到对那种不期而遇的重要性一清二楚。就快走到出口处,很有必要像猫套老鼠那样放慢脚步——已经蹑手蹑脚,扯整一下紊乱的衣襟,头发也不会显得很麻乱的时候,就仪态万方地走了出去。一切欣喜激动都缘自于萍水相逢,不会错漏一点马脚。
第二天晚上,小尬并没有从那女孩画室窗前走过,他显得情不自禁要推门而进,先是偷偷探出头来然后就钻了进去。他立即向那里的同学挥手问好,彬彬有礼。宁丽也坐她的小天地里专心致志地画着什么,他的到来仍然使她沉默不言,以使他一下子认为自己仅仅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有人招呼小尬,男的显得很马虎,女的却说:“嗨,小尬!”声音温柔体贴,这立即使他对先前的那个想法又给予全盘否定——他的人气指数自始至终居高不下。他只跟那几个男生寒暄一下,就不知不觉来到宁丽身旁,俯视着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神已把他捏造成一个讨债者。
“许许多多,满墙都是,连抽屉都塞满厚厚一沓。”小尬假惺惺长叹一声,并用手抚摩着墙上的画作,“太勤奋了,那一定是用很长时间画成的——比我自己一个学期积累下来的作品还要多。”
你们要学会对一个哆嗦鬼的忍耐。那家伙又以哗了一声,指着其中一幅说:“那不是南湖里的细叶榕吗?画得实在太厉害!啧——”
很显然,这些吹捧的言辞没能改变他自始至终被当成一尊泥佛的厄运。他还继续问及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有时像婴孩囔语。她仅仅对一切漠然视之,时不时回头瞟他一眼又立刻收回,生怕小尬趁机把某幅画掳走。旁人也没闲理会他干在些什么以及说了某些鬼话。他随便在桌面上拎起一本书,仔细地看着——真是判若两人,她怎么变得如此冷漠没有一点热情,不懂招呼客人——跟她来到他画室做客时的情景完全不同。怎么了,难道小尬的魅力早已荡然无存,你们甚至认定,是他那发型出现严重“故障”,让人讨厌致极。她或许从未把小尬放在眼里,只心不在焉地微露笑容,继续用笔轻轻醮上水,一层层柔柔地往纸上罩染上去。
“整个画室都挂满了,你们太勤奋了!”小尬神速地翻弄那本书一页又一页,然后放回桌上,东张西望一下,再次昂首赞叹,他一幅接着一幅地审视过去,全是画些水淋淋的天空、房子、一草一木,全是学院那些肮脏的风景。他转悠着差点没比蛤蚧走得快一些,时间很快过去,竟又转回到宁丽身边。她仍然表现得无动于衷——她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不蹦蹦跳跳、话语连篇,不再用莞尔一笑来使小尬感到自己头上顶上的发型依然魅力无穷。
“小尬,有什么事吗?”她放下笔并抱住手,轻轻地说。
她为什么竟问这样的话——只再过一会儿,小尬就带着俨然一个女人掉了一瓶昂贵的指甲油的那种可怕的失望逃之夭夭。
第十五章 01 三人行
当你们稳妥妥地撑着一叶叶扁舟,一直沿着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去,你们已经到达幸福的彼岸,从此就不应该用心去质疑,是什么力量让你们看到了希望——更不应该卤莽地认为:那完全凭靠你们自己用双手拼命地划动着那笨拙的双桨。应该侥幸地去肯定那是狂风巨浪的大发慈悲,抑或凶恶海盗的自发狂逃。
我想说的是,你们无法预想得到,热乎乎的馅饼也终于从一望无际的天上掉了下来——自从高乌从我的房间里滚蛋以后,我就变得“有事可做”——一切都应从幸福来临的那一刻起,当我们在一位年轻老师的帮助下(那一刻他竟如此伟大)——把一位老板的电话号码递给我们的时候(只稍稍交代一下情况),便轰然宣告我、张歪哥、韦弟三人有幸获得为一家餐厅绘制壁画的机会。如果你们能聪明地预知自己有极度失落的可能,那么你们应姑且潦草地读下去。
何况我们可以目空一切地说:“我们有钱了!”
但我们的一些倒霉不堪的事会立即改变你们无奈的阅读态度,很抱歉——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想一下子丢盔弃甲地永远地从那餐厅的门口奔逃出去什么也不要了。
一股由化学粘胶所发出的侵肠蚀肚的恶臭扑鼻而来;割木机与气压钉枪同时工作时参差错落混成的催人神经的噪音振聋发聩;泛漫着的木粉尘屑硝烟滚滚地呛人喉咙以及整个空间在几盏横七竖八的千瓦炽灯的照射下黄褐褐热蒸蒸——我们的“希望之火”为何竟在火炉中点燃——一个呆上半个小时就会让人奄奄一息的地方,我们为何仍卤莽前行——装作气高趾扬。是你们的沾沾自喜激奋了我们,以及这样做也许能使我们在与老板的洽谈中或多或少地捞得好价钱。
我得尽快打击性地告诉你们,李老板给我们敲定了工钱一万五千,对于这个数目——你们务必不要把在那刻韦弟毛茸茸的小腿索瑟发抖的秘密暴露出去,何况我和歪哥快要瘫软成为一堆碎烂了的湿棉花。你们必须把一万五千与我们那恶劣的作业环境考虑在一起,这有助于让你们心里踏实一些。
第二天李老板拿来一本据说是花了两千多块从法国邮汇过来的关于餐厅酒吧设计的杂志,里面有一些具有欧洲古典特色的房子的图片——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连成一体。依据他的意愿把它们挪移到这堵墙上实为雄伟壮观,顾客在那壁画面前闲坐一定如痴如醉、留恋忘返。我们有必要附和着说这个图片非常可取,韦弟继续抖着腿说:“好的,好的,就——就这——这个太棒了!”我们跟着认为它们缔造的壮观的气氛简直独一无二。
从此,除了你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