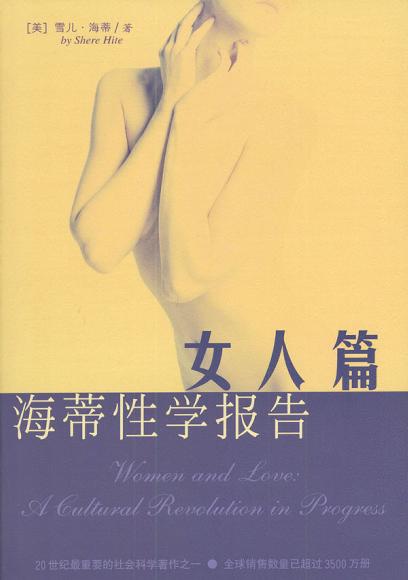报告政府-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火。
他再也不去戏班了。
他只是远远地听着。
后来,有戏班来热闹的时候,他连听也不听了,总是朝着与音乐相反的方向走去,不管自己会走到哪里,不管自己会迷失在哪一片月色。这一天,他走着走着,发现当空皓月照得天地大亮,远近树木简直就是暴晒在白炽月光之下,拖着边缘清晰的一条条黑影。青蛙躲在什么地方一声不吭,倒是公鸡纷纷拉出了报晓的长啼。时辰是有点乱套了。
他瞥见土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走得更近时,发现不是什么水渍,是一个活物在土墙上撞得四处飞溅:是一张钉上墙的牛皮,被钉子拉扯出几个尖角。他熟悉村里的牛,尤其是他放过的牛。伸手一摸,很快摸到了几个熟悉的牛毛旋,忍不住心里一痛:这不就是那个投胎做牛的莫扎特?不就是那头可以应着笛子节拍摇尾巴和摇耳朵的老黄牯?
它的眼睛呢?它湿漉漉的鼻头呢?它那断了一小截的左角呢?天哪,它怎么不去犁田而是挂在这个墙上偷奸耍懒?他猛拍牛屁股,发现它不动,死死地赖在墙上。
他一定是听到了牛叫,听到了这张牛皮的长长叫喊,才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他心里已经炸裂,额头重重砸向牛皮,砸向一张又硬又枯的多角形,在牛血的腥烈气息中流出了稀稀拉拉的鼻涕和泪水。憋了好一阵,憋出了女人的尖声,不像是哭,倒像是咳,一声声干咳。
他跳起来大骂牛的主人:“吃枪毙的三老倌,遭雷劈的三老倌,好端端的牛你把它摔坏,摔坏了你又不好好地治。你歹毒呀,你心枯呀,你明天就遭雷打哇……”
他骂得太聚精会神了,没注意自己这一天正拉肚子,直到发现裤子里热乎乎的一团,才一手提起裤边,尴尴尬尬地回家。
九
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他。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反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坐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看对方还在嗯啊嗯啊,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啊,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啊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啊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
…
山歌天上来(15)
…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没把你调到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只是想同你处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驭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牲……”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了。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他停了停,狠狠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只是……”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是老寅的作品,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能把这首歌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你看我家那个相公,气人不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啊。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只是一杯杯地喝。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噪或者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景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深深吸了口气,很晚才起身。
十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
…
山歌天上来(16)
…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啊,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她急得要跺脚。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只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啊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啊,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楂。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如果没有人从旁打断他,那张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可能很快会流出一丝涎水。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她久久地不再说话。
女人留下来了,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了主人的几件衣物,洗得自己一只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要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