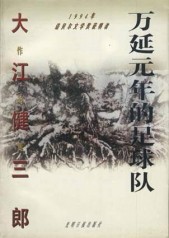1987年的武侠-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垒去安电脑了,电源插上后,周浅浅说:“算了,你还是把劲使在我身上吧。”
两人抱在一起,葛不垒脑海中出现巴西的幻像,木板床逐渐变化成阳光下滚热的沙滩,耳畔响起海鸥的鸣叫。周浅浅身体的色泽逐渐深重,最终变成一个黝黑的混血少女,她闪着一口白牙瞪着两只大眼,好奇地看着葛不垒,葛不垒说了句英语:“你好,我来自亚洲,一个黄种人。”
当葛不垒回到现实,周浅浅又点上了一根烟,闻着烟气,葛不垒的精神慢慢复原。看着电脑闪烁的荧屏,两人聊起了刻薄的书商,又聊到了这个月房租,葛不垒说:“我爸爸以为我在和一个好女孩在一起,准备再给我五百块钱。”
周浅浅急吸了一口烟:“什么意思?”葛不垒:“你是干那个的吗?”周浅浅:“不是。我所作的是——安慰艺术家。”
她在男朋友庆祝考上美院的夜晚后,一度厌恶所有搞艺术的人。但她从高中时代被男友吸引,因为他向往进入艺术圈,隔了两年后,她重新思考那个糟糕的夜晚,觉得自己付出了代价,就该进入这个圈子。她又找到了男友,他一见到她就哭了,两人好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男友看上了一个人体模特,她也被一个美院老师追到了手。
她天性善良,尤其受不了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向她敞开心扉。她听了许多泣不成声的诉说,被人连连得手。一些女画家实在看不过去,出于道义,劝她:“你太容易上当了,干脆收钱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成熟,终于采纳了这一建议。
她将自己视为记者。“记者?”葛不垒有点诧异,周浅浅说:“记者是个保守说法,我觉得我是灵魂的工程师。”收钱后,艺术家们还是哭哭啼啼,这说明他们是真的脆弱。她从一个轻信的纯情少女,发展到深通人情,像哄小孩一样轻抚过一些大艺术家的后脑勺。
她开始爱上了自己的职业,虽然目前只将安慰的范围局限在艺术圈,但也曾想过能将温暖送给更广大的人群。葛不垒趴在她胸口肃然起敬,问:“昨晚那个穿马甲的,也是真的脆弱?”周浅浅:“他就是我男朋友,一个礼拜前刚结婚,铺红地毯照婚纱摄影,他痛恨自己变得庸俗,就找我缓解一下情绪。”
葛不垒:“他也太容易对自己不满了!他家什么样?”周浅浅:“他媳妇在家,没敢去他家,去的是他在郊区买的农家小院,有两棵桃树——”葛不垒想象着周浅浅在桃树下笑容可掬的模样,坐起身,说:“你活得这么丰富,为什么又让我住在你家?”
周浅浅掐灭了烟,说:“你是一个我要拯救的对象。”
因为周浅浅的关系,葛不垒进入了艺术圈,两人常常坐在大巴上层的第一排,俯视群生般地向东而去。葛不垒认识了多位画家,一个老画家指点他:“画画这行当很排外的,不是美院毕业的没人理睬。不如你去搞观念艺术。”
周浅浅又带他找到了一个观念艺术家,观念艺术家说:“别听那帮画画的瞎说,我们也是很排外的。”周浅浅的计划迅速失败。葛不垒还是靠着画插图为生,隔一段时间回家取五百块钱。父母盼他早日结婚,一次给了他一千块钱,要他把同居女孩带回家看看。
这个要求,令葛不垒倍感为难,不料周浅浅满口答应。她穿着一身素雅长裙坐去了他家,自信能博得葛不垒父母好感,不料两位老人看见了她胳膊上的阿拉伯弯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几日后,父母要求葛不垒搬回家住,他母亲甚至还以死相逼。葛不垒离开时,向周浅浅要了根烟,吸完后精神矍铄地搬着电脑而去。
打的离开塔楼时,葛不垒从车窗见到对面街上沈杏花吃着羊肉串溜达,动了想让车停下的念头,但张嘴却发不出声,就让她的身影过去了。
【六、】
回到家后,葛不垒后臀的疱疹就渐渐好了,他全身心投入到画插图中,偶尔受到周浅浅的电话骚扰。她的第一句话是固定的:“我的处男,你好吗——”周浅浅总是在醉酒后打电话,明确地讲述自己在某某饭馆,然后开始对葛不垒痛骂,一说便长达一个小时。
想到和她第一次相见,也是在一个小酒馆,她离桌子几步远处摔倒,应该是打电话刚回来,也许就是在痛骂一个男人,她有把陌生人带回家的习惯。这种女人都是有怪癖的,现在的粗俗骂声才是她的本来面目,因为我的出现,前一个人金蝉脱壳了——葛不垒如此想着,对话筒说:“别骂了!别忘了,你不是个灵魂的工程师吗!”往往这个词汇一出现,周浅浅就挂断了电话。
葛不垒也担心她酒后出事,多次想去小酒馆接她,但没有一次出发。周浅浅的骂人内容多集中在“你是个虚伪的人,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吝啬鬼——”往往以“你是个处男”作为结束。葛不垒如果反驳:“早就不是了!”话筒里就会传来周浅浅的哭声。
后来,周浅浅就不再打电话了。葛不垒又多认识了几个书商,一小笔一小笔地攒着钱,期待着在三十一岁的时候能找到个贤惠女子结婚,在三十五岁前生下个小孩。一个晚上,他赶完了手里的活儿,两眼疲乏不堪,想到又有一笔钱即将到手,忽然很渴望放纵一下自己。
他去了那家素食餐厅。坐在曾经坐过的柱子后,他爽朗地对服务员说了声:“凉拌土豆丝!”服务员问:“就这一个菜?”他嘿嘿一笑:“对了!”
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豆丝,葛不垒作好了遇到周浅浅的打算。她会像上次一样,到我这吃口土豆丝,然后钻进别人的汽车里,不会有麻烦发生——葛不垒如此想象时,一个女人坐在了他对面,她已皱纹满脸,却剪了少女的留海,声音甜美地说:“我在这见过你,你认识周浅浅。”
葛不垒转了转眼,说:“你是个女画家。”女画家含羞地点点头,说:“周浅浅去世了。我们凑钱给她买了个墓地,明天骨灰下葬,你要想参加就也凑一份钱。”葛不垒:“一份多少?”女画家:“一千。”葛不垒:“今天我没有,明天我带着。”
女画家留下墓场地址,转身去了别桌。葛不垒低头将土豆丝吃光,又管服务员要了杯白开水,慢慢喝完,然后走到了女画家的桌前,问:“她真死了?”
所有的艺术家都想去巴西,他们热爱南半球,恐惧上臀肌过份发达。他们熟悉南美洲的植物,近期一人搞到了种久仰其名的植物产品,兴奋地召集大伙尝试,周浅浅也去了,却产生了过敏反应,大伙觉得她能缓过来,没想到耽误一会,再送医院她就已不行了——
女画家说完,含羞地低下头。葛不垒骂了声:“孙子!”女画家迅速抬头,嚷起来:“你说清楚,你说谁呢!”整个餐馆的人都转过头,有几个男子聚了上来,口里吆喝着:“红姐,出什么事了?”女画家一指葛不垒:“他骂我!”葛不垒的衣领便给人揪住了,女画家说:“算了,看在浅浅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大伙知道吗,他就是那个画插图的。”餐馆响起一片惊讶感叹声。
女画家拨开葛不垒衣领上的几只手,严肃地说:“不跟你计较,但你得道歉。”葛不垒说:“对不起。”然后向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回来了,问:“周浅浅对你们说过我?她是怎么说的?”
女画家说:“对你印象不错。”葛不垒转身再次向门口走去,女画家嘱咐了一句:“明天记着来啊!”
葛不垒没有回家,他去了周浅浅家前的小吃一条街,站了两个小时后,见到一条身影从黑暗中闪出,飞快地窜向烤羊肉串的摊位。葛不垒大叫一声:“沈杏花!”人影一下呆住,响起一声“大哥!”的回应,葛不垒霎时泪流满面。
沈杏花扶着葛不垒走入地下招待所,巴西老头得意地说:“今天我们这人又特少,你出一张床的钱,我还能给你个四张床的房。”入房后,沈杏花紧紧地抱住他,说:“大哥,李长征没被砸死,他给我写信了!”葛不垒也很激动:“长征?他还活着。给我看看信。”
两人打开灯,信上写的是:“杏花,你没找错人,我现在已经挣了一万块钱了!我从没忘记你,我一直记得在黄土高坡上有一个洞是咱俩挖的。一直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我想先混出个人样来。经过你想象不到的艰苦奋斗,我有了一万块,给咱俩以后的日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回家乡了,你也快点回来吧,我在洞口前等着你!”
葛不垒说:“你俩的钱加起来有一万六千块了。”沈杏花骄傲地说:“是一万七。”葛不垒大惊:“你又挣了一千。”沈杏花准备再挣三千,回家时正好跟李长征凑齐两万。她不好意思地告诉葛不垒:“大哥,因为要攒钱,我不能对你半价了。”
沈杏花睡着后,葛不垒溜出房,走到柜台前,巴西老头正在听着收音机。葛不垒很想聊天,便搭话说:“大爷,我觉得你是个很不一般的人。”巴西老头独眼闪烁,长叹一声:“被你看出来了。你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我以前是练剑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巴西老头是武术运动员,曾经在全国武术大赛上获得银牌,他创编了一套武当剑对练的套路,不料队友过于紧张,在第一次表演时一剑将他刺伤。老头的坎坷令葛不垒颇感意外,原想安慰几句,但等老头情绪稍一平缓,葛不垒马上说:“你还记得第一次陪我来这的姑娘吗?她死了!”声泪俱下地讲出了周浅浅的一生。
他讲着讲着,发现巴西老头情绪越来越激动,独眼的眉毛挑动不已。葛不垒急忙收住眼泪,压制住语调的起伏。他提着小心地讲完,巴西老头太阳穴处青筋暴起,独眼中一股杀气,一字一句地说:“明天的葬礼你一定要去,把那帮人的眼睛都给挑了。你今晚别睡了,我教你剑法!”
为防巴西老头心脏病暴发或脑血栓暴发,葛不垒拿着一根筷子陪他在走廊里练了半宿剑法。巴西老头累得气喘吁吁后,葛不垒终于回房,摸了摸床上了沈杏花,一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葛不垒起得很晚,没有了回家取钱的时间。沈杏花等着葛不垒付钱,所以醒了就一直躺在一旁。葛不垒说:“杏花,你能借我一千块钱吗?”沈杏花一下坐了起来,叫了声:“大哥!”
经过一番苦劝,沈杏花终于同意借钱。两人交钥匙时,巴西老头从柜台下拿出一把龙泉宝剑,说:“我后半夜回了趟家,特意给你取来的。它喝过人血,所向披靡。”葛不垒:“它杀过什么人?”巴西老头:“我这只眼睛就是它刺的。”想到多说无益,葛不垒就背着剑走出了地下旅社。
沈杏花从街边的自动取款机中取出了一千元,嘱咐道:“你可一定要还我。我今天不工作了,就在羊肉摊前等着你。”葛不垒拿了钱打了辆的士,车刚开起来,司机嘀咕句:“那女的怎么追车呀!”葛不垒向后望去,见沈杏花正在玩命地奔跑。
车停下后,沈杏花浑身是汗地钻进车来,嘿嘿一笑:“大哥,我想了想,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坟场吧!”葛不垒:“行,去完坟场,你就跟我回家,前账后账一块给你。”沈杏花激动得在葛不垒脸上亲了一下,高兴了一会后又焦急地说:“大哥,我不是对你不放心。”葛不垒说:“我知道。”张开手臂,将她搂在怀中。
葛不垒一手拿剑一手搂着沈杏花出现在墓地,很快被女画家发现,走上前要走了一千块。周浅浅的墓志铭是:“得意浓时是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女画家解释这是一个大艺术家专门从《红楼梦》中挑出的诗句。
她的骨灰由两个黑衣小伙子郑重地放入墓穴,封顶后众人肃立,开始烧祭品。沈杏花惊讶地发现,在纸糊的楼房汽车中,还有纸糊的周润发齐秦,指着呀呀地叫起来,站在沈杏花身旁的是一位秃顶的老艺术家,他温和地向沈杏花解释:“是我画的,她生前喜欢他俩。虽然趣味不高,总是她的心愿。”
葬礼完毕后,女画家招呼大家去素食餐厅聚餐。沈杏花想跟葛不垒回家取钱,葛不垒说:“咱们交的一千块里包括这顿饭。”沈杏花也就同意去了。艺术家们开着各式轿车拥挤而去,只有葛沈二人为打不到出租车还在徒步走着,快走出墓场大门时,一辆白色本田停下,是那个谢顶老艺术家。
他优雅地说:“我带你俩吧。”沈杏花叫了声:“老哥,是你。”毫不犹豫地开门坐了上去。
到了素食餐厅后,葛不垒向柱子下的老位置走去,沈杏花说:“大哥,我到老哥那桌去坐坐。”便随着谢顶老艺术家到了人最多的一桌。女画家走过来拍了葛不垒一下:“你怎么一个人坐这?没法给你上菜,跟大伙坐一块吧。”葛不垒说:“我交的一千块里有这顿饭吧?”女画家笑笑:“有呀。”葛不垒:“那就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