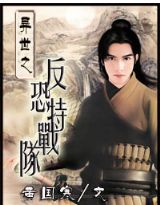特战五处-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整个###院,都没有声音。
每一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众人都被刚才的那几番龙争虎斗所震住了。
“我是铁棒护法僧桑赤!”
又一个人影跃入###院。
我还在流鼻血!
女人美目凝望着我的右颊,青黑了一片,我的鼻嘴,都有一丝血丝,我曾捱受扎吉一记前踢在左胸,又挨了一记侧踢在脸部,不管我是铁打的,挨了这两下,绝不会好过到那里去。
“来吧!”我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
就在这时,桑赤忽然闪电般的一踢——如果我在此时冲了过来,一定会中他这一踢。
我像猫儿一般就地一滚,桑赤飞侧踢就凌空擦过。而桑赤马上起来,立时打出一记“后踢”!
“噗”!这一脚踢中我小腹。
本来我吐气扬声,硬受一拳,正待反击,“噗”地一声,肚子又捱了一脚。
桑赤的攻击太快了,像脱弦之矢一般,前射了过去,在我还未来得及反击之前、他已一拳擂在我的右脸。
这下才真正够我受的。
嘿!永不低头的我,居然还能一声大喝,把桑赤的腿一提,推甩了出去!
桑赤飞落五尺之外,半空一个翻身,居然像猫一般轻盈落地,立时像豹子一般冲向我,动作之迅速,是我平生仅见,
可被斗志激怒的我,充满活力与魄力!
桑赤冲近,我马上感受到这压力,但他右臂已受伤,无法反击,只能用左臂格挡封锁!不料就在这一刹那间,桑赤冲近忽然蹲低,一脚低侧踢就切在我脚胫骨上。
咔嚓!
胫骨断裂!
我一跪痛吼,迎脸就是一记崩拳!
拼命的打法!
“砰”的一击,正好打在桑赤脸部!
桑赤怪叫一声,被打得一晃,却趁机倒卧地上,双腿一撑,“砰砰”踢中我脸部!
这两脚一中,我几乎已丧失所有的战斗力,可是桑赤的脚仍不放过他,已交剪在他脖子上。
“汉人要死了!”院外大哗!
生死存亡。
说时迟那时快,桑赤双脚对剪,我为之窒息,但男儿的血,总是热的!
“砰!”
我居然趁势一曲头栽下去,用前额撞在桑赤的脸上!
桑赤惨叫一声,松开双脚,两人同时爬了起来。
我忍着脚痛摇摆不已,桑赤也一脸披血。
我练过“铁头功”,一撞可以撞碎十块巨瓦,这一下撞在桑赤脸上,由上而下,只怕是桑赤出道以来受击最重的一次。
桑赤脸部二度受创,可是我伤得更重,双脚马上站不住了,脸部也被踢肿了起来。
“够了!”卓玛推挤着院外众人,但她被更多摩拳擦掌的铁棒喇嘛僧挤了出去。
众人很快看见我倒了下去。
桑赤狞笑着马上蹲下来,对准我的心窝就是一拳!
我忽然伸出手,双掌化刀急劈而上!
“地躺拳!!地躺刀!”桑赤一惊。
地躺拳是拳术的一种,也称地功拳,古称“九滚十八跌”,地躺刀是变种刀法,强悍霸道。
我以掌化刀,急似闪电!
“啊!”桑赤不及闪避,一声惨叫!。
“咔嚓”,我一记手刀将桑赤左腿撕裂!
“哗哗”喷血一条小腿,握在我手里。
我是用尽全力。
我把桑赤小腿一丢,用那条好臂拼命支撑自己站起来,刺啦一声吃掉上衣,露出发达胸肌!
嗷……。仰天狂啸!
“好功夫!我是护法僧棒喝师——索南仁波次!”
一个精瘦的西藏棒喝师,冲了上来!
索南仁波次扎出一个低平马,左腿一个侧滑,两臂大鹏般展开,张开三指,小指和无名指紧扣起,双手成爪,“呼”地刮出旋风,卷得尘土狂扬!
“少林鹰爪功!”我一震。
古往今来,练鹰爪者多,而成大器者少,关键在于手指实力阳劲之不足,即手指提、缩、拧三劲之功夫。但少林鹰爪门独树一帜,以内气导引筑基为先导,大成后不用之时,与常人无异,外不露形,战时聚内力于指,五指顿如铁爪钢钩,指劲惊人,可伤敌于不备,败敌于无形。
杀气!
我第一眼看索南仁波次气势和间架时,已知他内外有成。
杀气,从索南仁波次鹰爪里激射而出!
“逼我用猎刀么?”我爆喝中抽出英吉沙猎刀,发起猛攻!
手刀喷出火星,直奔索南仁波次右面。
索南仁波次虎躯左横闪电般伸手,一只左爪叼住我的猎刀,姆指压掌,四指扣腕,一招正宗的鹰爪擒拿。
咔嚓!我右手腕骨当即剧痛,一股巨力随着刺心疼痛开始燃烧,我眉头不皱“刷”地劈出左掌!
“不好!”喝酥油的女人脸色大变。
索南仁波次肩一沉,右爪跟上瞬间对击我左掌。
棒喝师可怕的速度!我心头一紧。
蓬!两人结结实实的撞击上,烟尘过后就见索南仁波次右爪已经卷住我,“刺啦!”鹰爪抽回来的时候,我手中英吉沙猎刀已血淋淋飞到半空!
我猛踢!
左爪连环!第三招鹰爪抽击在我脚上,只听我脚部一声裂帛之响,一道血裹卷着个军用登山鞋荡向天空!
我一声没吭,眼眶冒血,用剩下的单掌猛劈索南仁波次之方位,我的鼻子像捣烂的柿子,血一摊滩的淌,狰狞如犹斗困兽。
交手仅仅三个回合,我,成了废人。
我不甘心。
痛。
还有昏眩。
血不断的自伤处溢出,我甚至还几乎听得见流血的汩汩之声;血水,不断地渗了出来,我深黄色的陆军衬衫已给血水浸湿。
“让你们汉人看看我们西藏棒喝师的厉害!”索南仁波次大喝。
惨景,让观战的卓玛不禁眉头一皱。
她仰头,望见索南仁波次扯着我的头发,化爪作拳,迎面打了我一拳。
那一拳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擂在一只太熟的柿子上。
我咆哮了一声。
我不能忍。
我不忍。
我不忍心在这么多喇嘛面前,没有尊严地死去。
所以我死命抱着索南仁波次的身体,奋力击打。
我像尊焚烧着的神魔。
格斗剧烈。
索南仁波次用各种猛拳,向我身上招呼。
“汉人,放弃吧!不要再打了!”卓玛一湿。
索南仁波次如一头无可宣泄欲火的狂兽,出手都是狠招,招招招呼在我要害。
蓬!我眼骨被击裂,紫血渗流了出来,打从眼眶一直滥过胸部,把我的眼耳鼻唇都要填上一道褐色轮郭。
我用伤臂死死抱着索南仁波次,猛击他双肋。
“哇!”的一声,卓玛终于忍不住哭出来。
索南仁波次扯住我的头发,定住了我的头觑,又一拳就击了出去。
咔嚓。
鼻骨碎裂的声音。
还有卓玛的哭声。
鲜血大量的从我鼻端淌了下来,好像那儿上面有个浓血水龙头忘了关掣似的,不过,也许他没听到自己鼻骨断裂的声音,却清晰听到卓玛的哭声。
“……不……要……哭……”我挣扎、喘息、语不成音,字句和着血块吐了出来。
索南仁波次突然一脚就踹了过来。
踹在我的右腿上。
我闷嘶。
索南仁波次的第二下是膝盖撞向我的脸。
我被撞得仰脸倒下。
索南仁波次又一皮鞋踩着他的头,用力的盲扭着我的脸。
众人甚至可以听到我的头骨和砂石发出摩擦力的异响。
索南仁波次掀起整个头部鲜血淋淋的我哈哈大笑。
我猛然一挣,又箍住索南仁波次双臂一张口,血水喷到索南仁波次脸上,索南仁波次一时闪躲不及,也一脸血污。
索南仁波次揪起奄奄一息的我。
我那张口已成了一个血洞。
但血洞里仍传出了极其模糊难辨的声音:“操你妈的!”
索南仁波次凶残地搁了一把泥土,强塞到我嘴里,然后捏着我软软的脖子,要我连土带泥一齐吞了下去。
我又吐了出来。
索南仁波次一记鹰爪,“咔嚓”声,我的左腿立即耷拉在地上,腿骨已给凶爪生生撕裂!
索南仁波次正要反手一劈,将我的头砸爆,忽然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住手!把这个汉人奸细和女魔格桑梅朵关入大雪寺地宫。。。。。。继续给她酥油;把“凌云夺”封印起来。”
我的凌云夺被取走。
我被几个铁棒喇嘛架起来时,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格桑梅朵。
她是个女魔么?
二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发觉自己被拖进一个地宫里,景物又黑又脏。
地宫似乎有巨大的保护神,摆放着好些弓箭、锁子甲、牡鹿角,剥制的动物、唐嘎、面具、头盖骨以及敬神拜佛的全部用具。
地宫里有一些大件的浮雕金属器皿和石器,如饰有怪兽和头盖骨的屋顶,这些可能在佛教进入西藏前就已经存在了,也许是苯教留下的遗迹。
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件东西的色调是鲜艳的,声音是宏亮的,没有任何东西富有生气,充满活力。
墙壁上几乎都画有大量地狱的图画,细致地描绘各种刑罚。地狱分成很多层,每层设有不同的刑罚,惩罚不同的罪恶。刑罚包括火烧、水煮、油炸、碾压、刀砍及断肢,在烧红的铁上行走或拉出舌头用钉子刺穿,被丑陋庞大的怪兽奸污,还有把骨头从人体内抽出,把人及其内脏像破布一样挂在地狱之树上,或是当成踩在小鬼儿脚下的地毯。
我仔细观察着壁画,开始感到恐惧。
恐惧是人的本性。
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为何变成如此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
大自然在西藏高原上显露出的威力,比在低地平原大得多,而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可能产生足够规模的人类社会,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不难想像,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当一家老小蜷缩在弱小的帐篷里倾听外面 风暴雷霆之声时,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牛羊死于雪灾尸横遍野,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
西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
在《西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
尽管西藏作为佛国慈悲盛行,但形成反差的是,对犯罪的惩罚常常极为残暴,酷刑有时会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藏王墀松德赞在公元九世纪正式奉佛教为国教时,制定的“教法”这样规定:谁用手指指僧侣,手指要被剁掉;谁要恶意地中伤赞普的佛教政策和僧侣,其嘴唇就要被割掉;谁要斜视僧侣,眼睛就要被挖去;谁要对僧侣行窃,那就要按照被窃物价值的八十倍赔偿。
西藏社会等级森严、存在大量繁复的仪式和严苛的规矩,仪式使用的器皿也常常使西藏之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如用人的头盖骨做的杯,用少女腿骨做的号,用女人乳头、月经污染物等制作的法物。还有粉碎人的尸体让禽兽分食的###风俗。许多东西都与死亡、人的器官、肢解等令我恐怖的事物有关联。
左侧有一壁龛,里面黑洞洞的,好像还有一些人在里面敲鼓,我也看不见他们。
这时候,一位喇嘛手握一只海螺,站立在如军队食堂的饭菜窗口模样的一个很深墙洞眼前。
昏暗、闪烁的酥油灯照在喇嘛身上,灯光将那喝酥油的“女魔”格桑梅朵曝露在我的眼前。
格桑梅朵似乎在安眠。
当第二个喇嘛将酥油倒入海螺时,头一个喇嘛将杯子一次又一次严肃地举了起来,口中喃喃念着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