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之书-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能,是事实———它们很快地都将面临相同的命运。不过,只要它们还在我手上一天,我就不可能再任它们其中任何一封,以及任何你所写下的文字遭到摧残。这些信,乃出自一位令人惊叹的诗人之手,读着这些信,我的心绪总一再地回转荡漾,真理因之源源不绝地散放光彩;它们与我是如此地紧密相连,就此意义,它们形同属之于我。然而,再过半个钟头,它们便不复属之于我,因为,我已将它们整理好、准备寄还交予你手,任凭你明智的处理。你是该烧了它们的,就我来看,只不过,倘若阿伯拉尔当初曾毁去伊洛沙留下的永恒的文采,倘若,这位葡萄牙的女尼自此保持缄默,那么,我们大概就不至于显得如此悲哀,也不至于显得如此愚昧吧?就我看来,你应该会把它们都毁了才对。你是那么残忍无情;然而,我也是何其残忍无情,终于了解了这个事实,而且行至此刻才渐渐认清。尽管如此,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倘若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为你做的,无论是现在抑或从此以后,我希望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疑虑,只管向我开口便是。
过去的一点一滴,我是不会忘却的。我本来就不是个善忘的人。(我们之间,原谅与否早已不再是个问题,不是吗?)你大可安心,无论是写过的,抑或是说过的每一个字,以及其他种种,我都会将之密封在我坚韧的记忆里。所有细微的小事,你可都留心过吗?那所有所有的一切。如果这些信真的全被你焚毁,在我有生之年,它们还是会在我的记忆中得到来生的,一如消逝的烟花,会在当时凝神注目的眼膜之中,留下过往美丽的图影。其实我根本不相信你会把信焚毁。但我也无法相信你会手下留情。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至此,我实在也该停止这些胡言乱语了,尽管,我是那么地难以自抑,我也实在不该再期盼那已永远盼不到的你的回信。曾经,你的回信是那般冲击着我、改变着我,而且,一直是我快乐的来源。
我曾经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挚交,我的理性告诉我,你决然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而我,我只能为失去一位挚友感到遗恨。倘若有一天你遇到困难———这话我已说过一次了,你也知道。平静地过日子吧!好好创作。
艾许 敬上
“你们想错了,根本没什么丑闻发生。”乔治爵士对罗兰说道,那口吻透露着复杂的情绪,一来对结果感到满意,再者则借此予以谴责。罗兰虽然知道自己理应沉着冷静,可是听了贝利夫人用着衰弱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读着鲁道夫·亨利·艾许写的信,这些信中的文字就不断地在他脑中嗡嗡作响、反复重组,实在令他痛苦难当;再加上他自己无法对这些藏着爆炸性内幕的书信予以调查,内心的挫败可想而知。于是,一把熊熊怒火在他心底冉冉升起。
“我们也是读了这些信才知道的,我们说过我们知道什么吗?”罗兰反驳道,努力克制的结果,让声音听起来吱吱嘎嘎的很不顺畅。
“但是这很有可能会搞得满城风雨啊!”
“那不尽然!它很重要,只是在文学这方面来讲———”
这时,莫德灵光一现,想到了一则比喻,不过那实在太过煽情,所以她立刻予以淘汰。那就好像是你找着了———简·奥斯丁的情书一样?
“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读那些被收藏起来的信,随便一个作家都一样———如果你再去看看她的生平传记———你一定就会很清楚地发现,有些东西被遗漏掉了,那些都是传记作家没有机会拿到的资料,是最真实的,很关键的,而且也是诗人自己非常非常重视的。一直以来,有很多信都遭到破坏,通常,被破坏的就是信。这些信也许就有那样的意义,对克里斯塔贝尔而言。而且他———艾许———也摆明了认为这些信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么说的啊!”
▲虹▲桥▲书▲吧▲。
第50节:第五章 思尔庄园(14)
“真有意思哪!”琼恩·贝利说道,“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得听听别人的意见才行。”乔治爵士说道,那姿态很是顽强,且满腹猜疑。
“你是该这么做没错!亲爱的!”他的妻子说道,“可是你别忘了,如果不是贝利小姐那么聪明,又哪能把你的宝藏给找出来呢!还有米歇尔先生!”
“如果,看什么时候都可以,先生———如果你愿意考虑一下,给我———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这些信———我们一定会把信里的内容都告诉你———也会跟你说这会对学术界带来什么重大的意义———不论这些信是否可能编辑成册。我已经读了够多的资料了,我非常清楚,你手中的这些信,绝对会大大地改变我对克里斯塔贝尔的研究———如果没法参考到这些信件,我实在也没什么心情再继续研究下去了———米歇尔博士对艾许的研究想必也是这样的,绝对就是这样。”
“啊!没错!”罗兰说道,“那很可能改变我整个思考的脉络。”
乔治爵士看看这个,接着又望望那个。
“话是没错,或许事情真是这样,可是,我真能这么信任你们,由着你们看信吗?”
“这事一旦被公开,”罗兰说道,“大家知道这里有这些信,接下来就会全都跑到这儿来。全部。”
莫德担心这种状况早晚会发生,她狠狠地瞟了他一眼。不过,罗兰心里头盘算的是,只要让乔治爵士想到莉奥诺拉·斯特恩即将前来拜会朝圣,就够让他心烦的了,至于克拉波尔和布列克艾德的造访,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也不会有什么用的———”
“我们可以帮你把信件作个整理,写个简单的说明,再另外抄下来———只要您同意———而且还可以———”
“再说吧!我得听听别人的意见。我话就说到此为止。这么做也比较公平。”
“求您了!”莫德说道,“最起码,请让我们知道,您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会的!我们一定会的!”琼恩·贝利说道,“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她以一双灵巧的手,将这些干巴巴的纸页叠在膝上,一边排序,一边对齐纸页的边角。
罗兰和莫德坐上车,在暗夜中踏上归途。两人简短地你一句我一句,看起来利落而实际;然而,两人脑子里的想法,却忙转转的各有去处。
“我们的看法都一样,这事最好别太张扬。”莫德说道。
“它们绝对值一大笔钱。”
“如果穆尔特默·克拉波尔知道那里有信———”
“明天这些信就会全落到汉默尼市了。”
“乔治爵士的经济状况会好转很多,他可以把房子整修一番。”
“到底会怎么个好转法,这我没概念。钱的事情我一概不懂。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事跟布列克艾德说。这些信也许应该放在大英图书馆里。它们绝对算得上国宝。”
“这些可是情书呢!”
“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也许有人会建议乔治爵士去找布列克艾德,或者克拉波尔。”
“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千万可别是克拉波尔。那还不到时候啊!”
“如果他听了建议,到学校里去找人谈,接见他的很可能是我。”
“如果他听了建议,到苏富比拍卖场去,这些信接着就会消失不见了,流到美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如果运气好点,或许东西会落到布列克艾德的手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很不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独占这些该死的信件。它们根本不属于我啊!”
“那是因为我们是发现信件的人。而且,也因为———因为这些信很私密吧!”
“可是我们总不希望他把信就往碗橱里放吧!”
“当然不行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那里存在着这些信,那怎么可以?”
“你觉不觉得或许我们应该彼此订个———协议什么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又发现了什么事情,谁都不可以再把这事说给第三个人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同时关系着两个诗人,而且这当中又牵涉到那么多的利害关系……”
“莉奥诺拉———”
“如果你跟她说,那就差不多是在通知克拉波尔和布列克艾德了———而且这两个人比她更具行动力,我觉得。”
“有道理,那就希望乔治爵士会到林肯大学找人商量这事,那么,校方就会让他来找我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好奇得昏了头了。”
“那就希望他早日作决定吧!”
等他们再次听到这些信件以及乔治爵士的消息时,那都已经过了好些时候了。
※BOOK。※虫 工 木 桥 虹※桥书※吧※
第51节:第六章 我的青春年少(1)
第六章 我的青春年少
他的品位,亦即他之所癖,引领着他
置身中产阶级平庸厅房,黯淡阴森的秘密后房
处处布满浓烈威严的茶香
就在光亮微笑的犹太人后方,来来往往
尽皆一流高尚,旋于桃花心木之粗犷
家私、箱子柜子、结实的桌子、密密流淌
自喜之情,安满地臣服于安息日般的安宁,于蓝蓝的靛青
于苍苍的茶栗,于深褐色棉织的长条纹理———
他或将见到,精华一一释放
自那俗美的抽柜,历经密锁三道
自那东方丝绸柔软布包
排排陈展、秩序井然
清晰呈现、温柔涌泛
太古的紫水晶之蓝
发自二十只大马士革古老釉砖
光彩一如天堂之殿,其细腻之感
一如孔雀昂首英姿,光辉闪闪
至此,他的灵魂,终于得以餍满
至此,他口尝甜蜜,沉浸于麻木无感的光艳
他的生命苏醒复还,他的人生终获明了,他献上
属之于自己的金碧辉煌,凝神看了又看、反复再看……
———鲁道夫·亨利·艾许:《伟大的收藏家》
这间浴室隔成细窄的长方形,占的空间不大,用的是像糖霜杏仁果那样的颜色。物品净是浓艳的粉红,但其中又带了点黎明时分灰暗的色泽。至于地板上的瓷砖,则是灰漆漆的紫蓝色,其中几块砖面上,还画有小小的暗蒙蒙的一簇簇白百合花———那图案走的是意大利风格。从地板往上直到边墙半高,砌的都是这种瓷砖,紧接在瓷砖之后的,则是一整面佩斯利花纹的塑料布,布面上缀以十分亮眼的紫色和粉红色,热热闹闹的图案,看起来像是真爬满了长着长长吸条吸盘的八脚章鱼,以及海参。陶制物品的颜色也很一致,是带有土灰的粉红色,另外,浴室里还放有一只装卫生纸的盒子、一只装面巾纸的盒子、一只放在碟子上的漱口杯,那碟子看起来就像是非洲人衔在嘴唇里用作装饰的大托盘;再来,还有一只扇贝状的肥皂盒,里头放着一颗颗椭圆形的粉紫色肥皂,看起来都还是没用过的模样。百叶窗的塑料薄板擦拭得十分干净,呈现出破晓时分的粉红色彩,其中还起伏着圆膨膨的玫瑰红积云。底下衬了一层状似皮革的橡皮垫片的烛芯纱织踏脚垫,则是一如薰衣草般的淡紫色;烛芯纱的半月形套子同样也是这般的淡紫色,此刻,那套子正安适地套在马桶弯弯的基座上;同样的淡紫色还出现在一只烛芯纱织的帽套上,那是戴在马桶盖上的。而现在,高高坐在这马桶套上的,正是穆尔特默·克拉波尔教授;他敏锐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急切地凝聚他所有的心神。此刻是凌晨三点钟。他正在打理一叠厚厚的文件、一只黑色的橡胶手电筒,以及一个看起来硬邦邦的竹编黑盒,那大小刚好可放在他的膝上,完全不会碰到旁边的墙壁。
这并不是他习惯的环境。可他多少喜欢那种充满矛盾,而且不为常规所允许的调调。他穿了一件丝绸材质的便袍,长长的、黑色的,衣领翻折的地方则是深暗的枣红色。袍子里头,是一套黑色的丝质睡衣,搭配有深红色的图纹,胸前口袋上还绣了一排花体字,那是他名字的前缀。他的拖鞋是天鹅绒材质,黑的像只鼹鼠似的,上头有个以金线绣成的女人的头,散布在头颅四周的,不知是万丈光芒,还是飞散的发丝。这些都是根据他提出的设计理念,到伦敦特别订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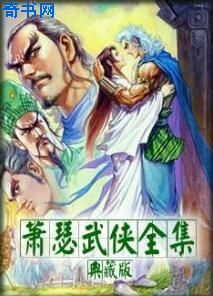

![[网王]书呆子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