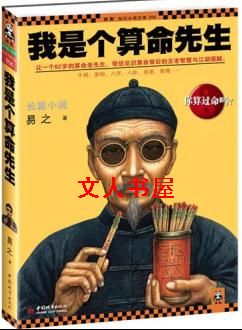不过是个普通人("探花"推理第一部)-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沛沛在厨房嘟哝了一句,为自己找了了根香肠做早点。她回到沙发上,翘腿搭桌,打开的金鸡晓报铺在上面。
追忆往昔,楚闻娟此起彼伏。他现在还好吗?不得而知。会不会已经去世了?有根刺扎在楚闻娟的心里已经许久了。她希望能有一天亲自向包主任道歉。告诉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有多么愚蠢。尽管多年来她都以年少轻狂来安慰自己,可仔细想想总觉得当时的行为实在太……
“小人!”都沛沛狠狠地说。
“你说谁?”
“又没说你,你激动个甚?”
她折起报纸,念上头的内容:
“募捐慈善*义卖收获喜人……西班牙领事夫人纳尔多太太捐出德国纯种猎狗幼犬一只。这也行!奥地利公使勃温先生亲自主持拍卖古董餐柜……不就是个碗橱嘛,真小气!”
“义卖乃是善举,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小人呢?”
“我说的是底下这个。”
楚闻娟接过报纸。文字下面配有一张模糊的照片。她一眼认出了站在和尚左边的石太太何颖。
“过去这么多天还在生气?”楚闻娟嗤之以鼻,把报纸扔还给她。“小心眼!”
“我就……喜欢。”她没说喜欢生气,还是喜欢小心眼,注意力迅速跳向其他版面。
“……塞浦路斯考古学家从古墓中发掘出一张神秘羊皮卷,经土耳其历史学家考证这就是传说中通往黄金城的藏宝地图。据希腊经济学家推测黄金城一旦被找到,国际金价将在一个交易日内下跌百分之七十!”
“有首饰赶快卖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楚闻娟说。
“弗拉明戈皇后不堪记者骚扰已于昨晚出院……弗拉明戈是哪个国家?”
“弗拉明戈不是国家……”乐逸天打着呵欠从楼梯上下来。几个人互致早安。
“你的老同学呢?”楚闻娟凑上去问。
“看见巧克力她就不认识我了。”
“阿天,我想……”
“弗拉明戈是怎么回事?”楚闻娟话没说完,被都沛沛强行打断。
“弗拉明戈是一种舞蹈。源自*语‘逃亡的农民’一词。当年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是谁?”
“哦,吉普赛人是起源于印度的高加索人。这个民族居无定所,遍布世界各地。男人贩卖家畜,女人则用塔罗牌给人……”
“什么是塔罗牌?”
“塔罗牌是算命用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庙里求签时用的竹签。每一张代表不同的意思。一共七十八张,其中有二十二张图画牌,叫大阿尔卡娜和五十六张……”
“什么是大阿尔卡娜?”
“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插不上嘴的楚闻娟终于恼了,大声地呵斥道,“不知道自己很烦人!”
“没关系,我一点儿都不烦。”乐逸天无所谓地说。
“说明你素质高。真不愧是英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懂得真多!”
“这没什么,常识而已。只要和我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读书,想知道不难。”
他在楚闻娟崇拜目光的注视下,进了厨房。
“卖弄!”都沛沛撇着嘴说。
“卖弄说明有本事。你也卖弄一个我看看。”
屋外的引擎声越来越响,在门口熄了火。楚闻娟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
“请问是楚小姐吗?”
“是我,你是……”
“我是石中谨先生家的司机丁宝根。因为上次有急事没能和楚小姐见上一面,我家老爷特意邀请您到府上共进晚餐。”
“石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这是请柬,请您务必赏光。”
“替我谢谢石先生,必将准时赴约。”
“一定传到。”
司机鞠躬后离开。
“为什么只邀请你,”都沛沛抱怨,“怎么没有提到我?”
“有提到你,”楚闻娟打开请柬,“间接提到了,下面有行小字:‘禁止带不受欢迎的人入场’。”
“这算什么?”都沛沛不满地叫道,“摆明了嫌弃我!”
“别这么说,我觉得不是,”楚文娟冷冷地说,“更多的是出于厌恶。” 。。
第七章 晚宴(上)
这是一个六月初的傍晚,整个上海笼罩在蒙蒙雾气中,俨然一座地道的江南小城。天气不像往常这个时间那样炎热,潮气阴魂不散,拖着白茫茫的魅影四处游荡。
后视镜里,丁宝根神情专注地开车,没有发觉楚闻娟一直在盯着他看。
这是个清瘦的年轻人,穿着制服,白净的脸上稀稀拉拉冒出几根胡须,双手握在方向盘十点和两点位置上,神情中透出的认真劲让楚闻娟觉得好笑。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丁宝根。您叫我阿根好了。”
“阿根,上礼拜六你去哪里了?”
“哦……老爷临时有事。”他感觉回答得不够明白,又补充道,”我给老爷开车。我记得我跟您说过。”
楚闻娟点点头,重复地问一个人相同的问题已经从她的工作习惯渐变成生活习惯,好像不这么做就什么事都确定不下来一样。
“来上海多久了?”
“五年。”
“住得惯吗?”
“老爷太太都对我很好。”
“娶亲了吗?”
“还没有。”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
丁宝根话不多,只是忠实地回答问题。两人断断续续地聊着天,前方的道路始终保持在在他的视野里。
石中谨府邸前的马路原先没有这么繁华。如今商贩的吆喝声充斥在街面上,让人不敢相信仅仅几年前,这里还只是上海郊区的一幢西洋别墅。租界急剧扩张的脚步踏平了乡村田园,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大上海的足印,霸道地由不得你做好准备。
汽车只能缓慢行进,最后停在别墅门前。司机阿根跳下车,拉开大门,又跑回来把车开进去。
尽管几天前来过一次,楚闻娟对这里还是没有多少印象。前院西面栽种着一株法国梧桐,从粗大的树干判断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树龄,茂密的枝杈几乎要探进二楼的房间里。两根麻绳吊着秋千,树下的草地已经踩出了黄土。其他地方则是绿草茵茵,从前院一直延伸到府邸后面。
汽车绕过椭圆形的花坛,稳稳地在大房子跟前刹住车,阿根替楚闻娟打开车门。他脸上还是没有丝毫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完成得毕恭毕敬,让人觉得好像稍有不慎就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他身上。
任水从屋里迎出来,男管家容光焕发,看见他那张略显谄媚的表情任何人都不得不跟着心情好起来。
“下午好,楚小姐。老爷在后花园恭候,请随我来。”
楚闻娟跟在他身后,绕过房子,来到后花园摆放遮阳伞的地方。一个男人听见脚步声,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是楚闻娟第二次来到石府,却是初次见到石中谨。他至多不会超过三十岁,一副金丝眼镜架在满是书卷气的脸上,窄窄的肩膀像个女人,带有浅色横向条纹布料做成的上衣多少掩饰了这一点。根据他身材改良的西装有点不伦不类。
依着老丈人的权势,婚后的石中谨可谓平步青云,短短几年就要坐上公共租界警务处副处长的位子了。
他热情地伸出双手,寒暄的方式用在失散多年的亲人身上也毫不过分。
“我应该为上个礼拜的失礼道歉,有突发事件需要处理,请你原谅。”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才对,希望我表妹的粗鲁没有让尊夫人太困扰。”楚闻娟控制着语速,极力表现出一种上流社会的优雅得体。
“阿水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的建议是,忘了它吧。”新任处长转身对下人说,”阿根,叫荣妈把茶送到后花园,再去厨房看看阿华准备得怎么样了。”
“老爷,阿华前天被太太赶走了,现在的厨子叫阿维。”丁宝根说。
“哦……随便吧!”石中谨摆摆手,心不在焉地说。“我太太从小生活在军营里,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还喜欢挖苦人,我已经深受其害好多年了。”石中谨轻松一笑,“孤儿院的小孩也害怕她,只要她一去,没有敢不听话的。”
“石太太对慈善事业的热心我早有耳闻,真令人肃然起敬。”都沛沛读报纸上的新闻此时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过是和富家太太们的社交活动,搞搞募捐,那些记者也乐得给她们上报纸露脸的机会。”
“善举理应被传颂。以我的观点,一件事情带来的好处只要多过坏处,哪怕一点点,它也是值得做的。”
“嗯,好处和坏处衡量的标准可能因人而异,但我认同你的看法。”相对于闲聊天,石中谨的态度过于认真了。”门伯伯说得对,你总喜欢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看法。”
“门伯伯是谁?”
“我讲了超超奇特的五岁半生日宴会,还给他看了你们拍的照片。”石中谨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接着说,“他看完后指着照片上的你说,这样的主意一定是你出的。很神奇吧!其实今天邀请你来也是他的主意,我是从来不敢拒绝的,和我的岳父一样,完全是军人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你瞧,说来他就来了。”
容妈端茶盘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位身体健硕的老人。石中谨看到他赶紧站起身来。
“下午好呀门伯伯,这位就是楚闻娟小姐。——门先生是我岳父的私人医生。”
“是战友!中谨,是战友!”门医生纠正道。
“是你!”楚闻娟惊叫道,”你的脸怎么啦?”
“怎么样,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吧!”
相信所有见过他的人都会首先被他脸上那道长长的伤疤所吸引,老人叫门汝平,亲历了始于1914年那场发生在欧洲继而影响全世界的战争。作为一名军医,他参加了西线大大小小的十余次战役,脸上的伤疤是一枚德国炮弹送给他的“礼物”。
门汝平把两只粗糙的大手放在楚闻娟的肩上,说道:
“有人告诉我,你给巡捕房做事?”
“我是巡捕房的探侦顾问,也提供私人调查服务,你有需要吗?”楚文娟开玩笑道。
“这么说左溪街十九号的侦探事务所真的是你开喽?”
“的确如此。”
“太不可思议了!不知道你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年轻的侦探小姐,究竟是什么样的理由促使你选择这样一种职业呢?”
门汝平说话的方式颇有些西洋味道。
“此事可说来话长了,您恐怕没有把它听完的耐心……”
“那就长话短说。”
“迷信!”
“哦……那可真是太糟糕了!不过回答得很精辟,我喜欢。”门汝平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屁股坐到藤椅上,点燃了一根粗大的雪茄烟,再配上他那撇经过精心修饰的小胡子,看起来倒更些大侦探的气派。
在楚闻娟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门汝平与她的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楚雄才身为中医世家的第五代传人,对西医西药持有一贯的病态排斥心理,自从同在一条街上的门氏西医诊所把门面立起来的那天起,他传统的海派诅咒就没有停歇过。难听的话传到对面的耳朵里自然不会没有回应,一来二去同行间的矛盾逐步升级到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上了,如此水火不容的局面直到门汝平的突然离去才告一段落。
即使存在这样的大背景,楚闻娟还是会偷偷地跑去门氏诊所玩。橱柜中摆放的玻璃器皿和里面五颜六色的液体远比家里丑陋的草根树皮好看得多。小女孩的聪明伶俐让无儿无女的门汝平心生喜欢,两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地下忘年交。没想到今天却在这里重逢。
“你家的老顽固近来可好?”
“托您的福,门氏诊所关门以后他就越来越好。”楚闻娟笑道,”当年你说走就走,原来是去欧洲打仗。”
“战争刚一结束我就回到上海,又重新开起了私人诊所。为了不跟你老子再见面,我换了个地方,离你的侦探事务所不远,也在望平街附近。若不是上校执意要我做他的私人医生,我的诊所可能会一直开下去。那些年里我给数不清的记者看过病。他们这个行业风险很大,一句话说不好就会得罪人,挨揍那是常有的事,所以我的生意一直好得不得了。你要知道,身为一名军医,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外伤。”
“今天您没有用武之地了。”
闻听此话,门汝平眼角挑起一丝笑意。他挪了挪肥硕的身体,藤椅随之发出几声惨淡的呻吟。一时之间,楚闻娟的心里突然涌出不祥之感,那是女人的直觉,身为侦探的女人特有的直觉,通常很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