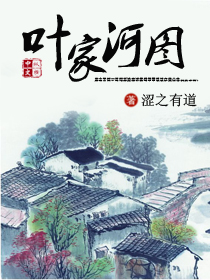及考古学家-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志:昨天的工作未完成就匆匆结束,是因为受到了探险者的内脏器官的报复性打击,我得了急性痢疾,非常严重。我用了半天的时间进行治疗,我试图通过睡觉减轻病痛,然后在洗手间里的“主人之声”牌手提箱式留声机上放了十几个唱针,让这样的下午能够好受一些。在开始继续昨天的工作之前,我去镇上吃点早餐,然后就去了古物管理局和邮局。
9月22日
亲爱的:你好!
谁是你的好女孩呢?我就是,我的王子。我保证当你每天“在作战”时给你写信,而且我会遵守诺言。我今天上午刚把昨晚写给你的一封信寄了出去,尽管我不记得我是拼了命来写这封信的,因为当时茵吉喂我吃了一些烈性药,逼我睡觉。自从你离开以后,我很不安,即使我知道你会说我太荒唐了,但你绝对是我的英雄,而且当一个女孩的英雄离开了这个小镇,似乎一切都变得凄凉了起来,不是吗?现在我又在给你写信了,因为我想告诉你今天上午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昨晚的信已经封好并准备寄走了,所以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刚让茵吉把上一封信送到阿灵顿大街的邮局,等她一回来我就让她再把这封信也送去,因为她有点发福,所以需要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
昨晚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事实上,茵吉昨晚给我吃了止痛药和安眠药,而且我忘了告诉她先让我喝一两口水,然后再喂我吃药。你看,事实上,我对她很生气,而且完全欺骗了她。这些天来,她始终在近距离看护我,我很难走出这个房间,因此感到非常无聊,这是最让人受不了的事情。所以昨晚我偷偷地跑了出去,我去了奥图勒家。可当我回来时,她正在等着我,而且非常生气,就像当初我表现出我是多么比她聪明时她生气一样。所以她就给我喂安眠药和止痛的东西(在喝一两口水之前),当它们混在一起时,就会让我沉睡不醒。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只有我们这一对老夫老妻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看到她拿着解雇书走人。你知道吗?她竟然神经质地告诉我,前几天你爱上我是因为爸爸的钱。我差点儿给她一记耳光,这个瑞典贱货,可她也惩罚了我。
当然,等我辞掉她之后,如果她留下来给爸爸“干活”,你可不要大惊小怪。我知道我熟睡的时候她去哪儿了。毕竟,我不是个大傻瓜。你不想要一个大傻瓜做你的妻子,是吗?现在会吗,我的英国佬?
你的探险还开心吗?我想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可能仍在海上询问船长,给他看你的地图和你那个邪恶法老的诗。很可能你又被一群女孩包围着,就像当初我遇到你的时候。但你知道,他们不是你的,亲爱的拉尔夫。只有深爱着你的未来女王才是你的,而且你是她的惟一。
爸爸问我在你探险和婚礼结束后,我们对于住处是怎么想的,我们要住在波士顿还是搬进特里利普什庄园。他满是伤感地看着我,就像真的一样,他说他想在英国乡村的大庄园里总能看到我,你是怎么想的?你考虑过要回到英格兰吗?或者这仍会让你感到很痛苦?我们有足够的钱重新修复庄园吗?爸爸总是很傻,但在这件事上也许他是对的。我想我会很高兴成为一位英国夫人的。
这让我想起了昨晚的那个梦,在充满药物的迷雾里,像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你和我结婚了。我感觉身体很强壮,也很健康。我们是那么幸福,我从不会因为自己的心情或是任何其它事情给你增添烦恼。你的挖掘发现使我们非常富有,而且你名声显赫,无论我们到哪里,所有的人都会热情地欢迎我们,而且你还带着我到英格兰进见了国王和女王。然后,我们回到家,我将生下咱们的第一个孩子。拉尔夫·切斯特·克劳弗得·特里利普什肯定会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刚生下来就能说话! 而且他说的都是骂人的脏话,他还不停地说你可以想象到的最下流的语言,就连医生和护士们都在摇头和叹气了,而且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喂我越来越烈性的药,我又开始回到昏睡的状态中了,但在我沉睡之前,我看到了,拉尔夫,你,你正在大笑并跟我说:“噢,是的,这是我的女孩,她就是。”
埃及考古学家 九(2)
老实说,写这封信简直让我筋疲力尽。我必须告诉你。这里仍然是酷暑难耐,而我总是昏昏欲睡。茵吉快回来了,这很好,因为我想让她马上就把这封信寄走,我还需要止痛药,今天的状况不是很好。你想象不到的,我痒得甚至想扯掉自己的脑袋。茵吉给我的药让我痒了好久,可等我睡着后,就没那么痒了,如果能够不再这样,我就不会总感觉这么疲惫了(原谅我说得很直接)。我真想出去和朋友们、伙伴们高兴地玩一玩。噢,是的,拉尔夫,你最好快些载誉而归,否则我会让其他人带走的!不要认为我不会,英国佬。一个善良的美国人,结实而又强壮,会很快拥有我。
我很累了。
吻你,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也吻你。它们要舔你几下。自从你走之后,它们的尾巴不像以前摇摆得那么厉害了,这是真的。我的确认为,它们和我一样的思念你。
你的玛格丽特
埃及考古学家 十(1)
(1922年10月17日 星期二,继续)
致玛格丽特:亲爱的,今天我收到了你的第二封信,它紧跟着你的第一封来信。我的心充满了感激,你做的关于阿托姆…哈杜的有趣的梦让我非常高兴,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从未告诉过你去年4月那天我的真实感受,但我在这里与你隔绝的日子会勾起我那段甜蜜的记忆。
我在波士顿历史学会公共演讲大厅里所做的演讲被说成是一次古埃及文化的大讨论,尽管我向组织者保证不会这么做,但其实我就是打算从《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上大声地读些东西。但一位演讲者必须面对现实:那晚的观众无疑是受到了晚会海报的吸引才去的。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我不会愚蠢地断定上百个波士顿妇女是为了听一场关于古埃及的一般性讨论而聚集于此。那么这个演讲者将无疑是那位丑态百出的国王臭名远扬的翻译者,让我们的追随者去否认一首四行诗的任何部分,并回答那些在关于国王的讨论中自然产生的问题(历史的、社会的和解剖学的问题)可能是不公平的。
你知道当晚我就注意到你了,我的女王。当时,我正在解释古埃及逐渐向着一种病态怀旧情绪的倾向发展,更荒唐的是,这是在这个国家的发展早期就出现的特点。这种病态体现在古埃及的政治在历经几个世纪不断复兴的“低俗”的宗教信仰过程中。在他愚蠢的民间记忆中,曾经有过一段繁荣的西部时期,那时有辽阔富饶的绿色草原,强壮的公牛在上面奔跑;在他重现的感觉中,他过着统治末期的腐朽生活。通常这种感觉很荒谬,怀念从未存在过的事情并复兴已处在完好状态的事物,妄想生命即将终结或者权力危险地落入他人之手。可是,在某一特定的重要转折时期,像阿托姆…哈杜的统治末期,这种恐惧感突然得到了证实。“在他生命行将结束之时,阿托姆…哈杜必然相信埃及即将永远消失。”当我讲这句话时,我注意到你坐在前排:你正在打盹儿,我的美人,这可不合适,所以我记住了你的位置;几分钟之后,当我在背诵他的第三十五首四行诗(只出现在片断C中)时,我一直在正视着你:
她将属于我,她将属于我
她将属于我,她将属于我
以及她的母亲、她的山羊和她的九个姐妹
她们将属于我,直至我感到厌烦,这样很好。
这是那次演讲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而且我通常会随意挑选一位年轻的女士感觉阿托姆…哈杜诗文的野蛮激情。于是,亲爱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是如何放纵自己的感情的。
后来当许多追随者来到讲台的角落里问最后一个问题,她们太害羞了,以至于不敢当着全体观众的面问,或者只是和这个英国的探险者握握手,但我那时认出了你,你不在她们之列。我正在回答问题并为她们拿到的《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签名,所以我没有注意你,但你一直在讲台的前面,没有离开,是吗?当我回头看时,你依旧坐在那里。我曾经见过这张脸:这个女人倾听了古代国王的歌唱。
“特里利普什教授?”一个安静而又清脆的声音。“特里利普什教授,我对您的演讲非常感兴趣。”
“哦,准确地说,”我走下讲台来到你的面前,“我还不能完全算是一个教授。就像在任何原始社会一样,我在哈佛时期获得的专业殊荣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回答我时,眯着眼睛,噘着小嘴,“我也不能说对你的演讲完全感兴趣。一些过于专业的内容让我有点走神儿了。”
“哦,小姐,真是的。”在你旁边的一个北欧美人开始责备了。
“堵住你的嘴吧,茵吉,”这是我未来女王的声音,“你为什么不去蒸蒸桑拿浴或是干点儿别的什么?”
你大胆地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禁不住引用了在波士顿到处皆是的广告词,“当你发现费那苒精品服装店的时尚艺术时,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但我必须告诉你,以免你会永远记得茵吉这个挪威人的卑鄙,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家店是你家开的。现在回忆起来:你笑了,但并没有坦白你与它的关系,所以我猜这些名字是一个巧合。阿托姆…哈杜已经在幕后操纵了,亲爱的,金钱从来不是他真正在乎的东西。
观众离开以后,你和我坐在讲台的角落里闲聊了起来,我决定相信你并考验你一下。于是,我教你怎样用象形文字写“阿托姆…哈杜”。此刻,你那个冷若冰霜的保姆正在演讲大厅的门前走来走去和工作人员(庆幸他们引来了这么多的观众,并因警察得到数目可观的保护费后没有破坏这次活动而得以安慰)聊得正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吗?我的费那苒小姐是一个可爱的、有点会撒娇的女人,而且第一次听到阿托姆…哈杜时就被深深地陶醉了。当她说如果我在不久的某天能够陪她去美术博物馆时,她将会非常荣幸,听到这些我并不吃惊,在那里,她也许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会向她解释那些陈列品中的埃及古迹。哦,是的,亲爱的,请别让可疑的茵吉重新改写历史。是你提议让我们再次相会,这是我经历的最大胆的调情方式,从那以后,我就已经属于你了。
。 想看书来
埃及考古学家 十(2)
当然,准确地讲,我并不是愚蠢地认为你的心已被我完全占据了。不是的,我看得出来,另一位20世纪的女性发现了第十三王朝国王的名字是一种无法抵抗的科隆香水。
亲爱的,我在开罗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直在等待着古物管理局发给我挖掘许可证,而且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现在是10月17日晚上11时36分。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宝贝能够让我马上就见到你,一种最高倍的望远镜,我会永远凝视着你,我的爱人。
埃及考古学家 十一
1922年10月18日,星期三
日志:邮局没有我的邮件。四天后,我的“慷慨之主”和支持者将拍电报给我,重新填满我的金库,我动身继续在市场和为我这种情况的人服务的专门商店里购买日常所需。一整天的购物减轻了由于在这里被迫耽搁而产生的烦恼。油漆、刷子、铅笔、凿子、切肉的餐刀、手电筒和行军床。正当我的采购单逐渐被填满的时候,在一个安静的小巷里,我注意到了一家裁缝店。我需要多带上几件外套,以便应付工作和社交场合,并为一个正式的古墓开工仪式做好准备(这种活动通常会有英国、法国和埃及的官员参加,以及可能出席的艾伦比将军等等)。
我掀开串珠门帘,发现这是一个光线充足的小屋,一个高个子的家伙走出来迎接我,这个埃及人因长年在这个低矮的屋顶下工作而过早地变成了驼背。我坐在一个柳条编制的扶手椅上和主人一起呷着豆蔻咖啡,这时两个男童一次次推着装满布料的镀金小车来到我们跟前。我和裁缝用手感觉着这些布料,讨论着这些耐热又惹眼的布料的优点,我看中了其中的10种布料,并决定以它们为材料定做几件外套(费那苒在波士顿可能要花上10倍的价钱),然后,我们站起来开始量尺寸。三面镜使我能够看清自己的左右两侧,在我下方蹲着一个雇员开始量我的裤腿,并把一组数字报给双腿盘坐在椅子上的记录员,此人将衣袖捋得很高,显出光滑的小臂和隐约可见的血管,就像三角洲的立体地图,而从门帘后面,可以听见女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