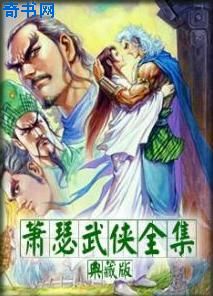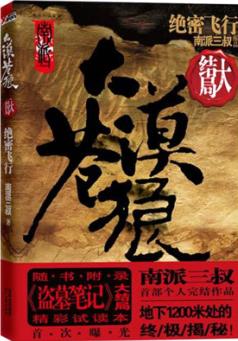大漠苍狼上,下-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打量着帐篷口上的警卫兵,其实溜进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可以通过铁丝通道下头的水游过去。但是,入水的路线需要仔细的谋划。
我回到自己的帐篷,把袁喜乐送我的手表用手帕包好放在枕头下面,然后悄悄摸了回去,一路顺着医疗区域,寻找最合适的进入口。
大坝内侧的建筑都建在地下河道的两边,一边是医疗区、食堂,还有我们住的地方,另一边是工程兵、司令部,还有他们的食堂。因为系统的不同、伙食不同,我们两个系统的人是故意分开的。
医疗区是一块独立的地方,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帐篷,上百个护士都住在里面。
我和袁喜乐的住处中间隔着食堂,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一些铁架子上,有些是日本人原来安上的,有些是我们自己焊接起来的。所以,整个区域全架在水面上,我可以从食堂下涉水过去一路到医疗区。但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上去,铁架子全封死了。
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已经无法再等待,决定先下去再说。
我喝了几口烧酒,活动了一下身体,偷偷从营地的边缘下水,然后摸进了铁丝网下。建立营地的步骤是,先使用电焊加固铁丝板,然后再上面垫上木板,再打上帐篷的防水布,隔音效果很差。所以一路过去,我听到上面的帐篷里全是各式各样的走路声、吵闹声和大笑的声音。
地下河的河水极其寒冷,我冻得瑟瑟发抖,但心中是滚烫的。这个时候也不敢打手电,就靠着木板缝隙中透下来的灯光前进。
游了几十米出了食堂,到医疗区的路上有一段上面没有遮盖,我潜水过去,再探头出来,发现这里忽然静了下来。
我差点打了一个喷嚏,抱着双臂打着寒战从下往上看有没有地方可以上去,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地方透下来的灯光特别亮。
我又闷头游过去,亮光那里的铁丝网上被气割出了一个圆洞,感觉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爬上去之后发现那是一个取水井,旁边放着很多水桶。
冷风吹了过来,我冒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把衣服脱掉拧干,居然还暖和了点。我只穿着一条短裤,往袁喜乐的帐篷摸过去,就看到门口的警卫兵还在,看来那天是陪她去做检查了。
我们的野战帐篷都用泥钉打在土里,本来四角要用重物压住放风,这里没有那么多石头,所以改为直接用木板压住打上细铁钉,我不可能从正门冒险摸进去。
也不知道帐篷里有没有人,我想了想,来到帐篷后面贴着听了一会儿,没听到有人说话,才深吸了一口气,用小刀贴着帐篷的底部划出口子,然后钻了进去。
里面比外面暖和多了,几乎只过了一秒钟,就刺激得我浑身刺痛。帐篷里有一盏很昏暗的灯,我不敢说话,就看到袁喜乐已经坐了起来,看着我的方向。
她的头发变长了,脸显得更加精致,“苏联魔女”那种干练冰冷的气质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种让我无法形容的感觉。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冻得浑身发青地看着她,两个人就这么看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我忽然觉得这样狼狈地出现,是不是会破坏我在她心里的形象?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扑了上来,冲进了我的怀里。
冰冷的身体顿时迎上了一股炽热的暖意,我也抱紧了她。
那几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都不敢说话。袁喜乐怕有人突然进来,关掉了灯,我们依偎在一起,感受着对方的体温。
我的脑海中想起了当时我们在避难所黑暗里的情形,和这事是多么的相似,又是多么的不同。
我不知道那是幸福,还是满足,或者随便其他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离开。
我们在黑暗里,用手指在对方的手上写字交流着,虽然非常模糊,交流得非常有限,但还是非常高兴。我问了她很多问题,她大部分反应都是摇头,好像并不理解。
她中毒的程度要比我们严重的多,我意识到她并没有完全复原,更加的心疼。但我又没法待得太久,因为护士会半夜来查验,袁喜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没有留我,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沿着水路返回。
这条水路看来是一个盲点,我成功回到了自己的区域,虽然冻得几乎想死,但心里还是非常的满足。
到了自己的帐篷里,我和他们说刚才去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去摸枕头下的手表,拿出来偷偷把玩着。那时一只非常小巧的苏联基洛夫表,当然不能和现在的精工表比,但还是比一般的男士腕表要小和薄。当我翻到后面,就发现表达底盘上刻着几个字:“无论我变成什么,你都要怜悯我。”
字刻得并不好,好像是用什么尖刺刻上去的,这应该是她喜欢的名言,也许是某本歌剧里的台词。
苏联的东西以结实夯实出名,这种小表一般都很名贵,是国际间的交流礼物,想买可能都买不到。
我激动起来,想着这表的由来一定很有意义,放在手里吻了吻,心里有什么确立了一样,一下感觉好像她在身边,能闻到她头发的香味。
我知道自己从这一刻起已经万劫不复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也暗恋过一个女生,那是个白净的女孩,平时也不太容易接近,后来知道她是一个团长的女儿,注定要进部队做干部,也就没做出什么行动。我记得那个女孩看我的眼神和我那时心里的感觉,那也是爱情,但,和这一次的程度完全不同。
那时候我还可以思考很多问题,现在,脑子里只有拥她入怀的念头。什么我都没法去想。我知道我已经退不出去。
但是转身又觉得担心,在那个时代,爱上一个女孩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而她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神志。我也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下我能干什么,我也不去奢望,现在想的,只是能多见她几面。
只是王四川带了一帮人过来叫我打牌,我没心没事的,输得满脸都贴了条,后来他们觉得索然无味,就出去抽烟吹牛去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想着之前的事情,心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想到一些场面竟然面红耳赤起来,一边觉得自己没出息,一边又不自主地笑,想着想着睡着了。
第二天王四川踢醒我的时候,我正在做梦,梦里当年那个团长的女儿又回来找我,她的脸一会儿变成袁喜乐,一会儿又变回去。我焦躁起来,想问你他娘学川剧的?刚说话,却看到四周全是人在看我,我一摸脸,发现脸上全是纸条,上面写着“搞对象”三个字。我大惊失色,赶忙去撕,却发现贴得极其牢固,脸上的皮都拉碎还撕不下来,一下吓醒了。
睁开眼睛,我才发现昨天糊里糊涂的,输牌的纸条都没撕就是睡了,王四川正拽着我的脸颊让我起来,看样子很是兴奋。
同时我听到帐篷外面动静也很大,从开着的帐篷门能看到好多人跑进去。
我摇摇头让自己清醒,问怎么了,他说:“快点,有好戏看。”
第二十七章钢缆
正觉得奇怪,王四川撩开了我的被子拖我,我冻得直哆嗦,披上衣服踹了他两脚,然后跟他跑了出去,马上发现那些人都在往大坝跑。
跟随着来到大坝上,围观的人太多了,就有人出来把他们往下赶,我们是技术人员没人敢撵,于是还算方便地来到了大坝边上。走进了看到一群工程兵在摆弄一大圈钢缆,这种钢缆每卷都有一吨多重,运下来一定够呛。
我看到两根钢缆被卷扬机绞成一股,用铁皮加粗在一起,钢缆的一端连着一个大的黑铁坨子。 几个工程兵用杠杆推动铁坨子,一边有一只油桶做的土炮,这是解放军的传统装备了,据说是刘伯承发明的,把油桶的一边切掉,然后再打几个铁箍。
这东西一般用来打高地,然后在剿匪的时候被普遍用来扫雷,只是把火药换成了大量的石子。当时的土匪往往缺心眼把地雷埋得特别密,一炮下去石子漫天开花,地雷炸地雷直接炸掉半座山,连炮弹都省了。
我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这是在架设钢缆,在山区或者落差巨大的地形上,钢缆确实是最快捷的方式。
不过,我没想到会用这么野蛮的方法,而且现在好像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下意识退后了一步,这个动作一做,其他人也立即跟着我后退,有的还捂住了耳朵。
我感到有点好笑,就在这时,从前面人群让开后的空隙里,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他在另一个方向,离我很远的 地方,正坐在大坝的边缘看着那片黑暗,好像并不关心这里的事情。
之所以说他奇怪,倒不是因为他长得怪,而是因为他是个毛子。那是个苏联人。
这里怎么会出现苏联人?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里的保密等级这么高,按理说不会有外国人出现。
这家伙留着很短的络腮胡,看上去身量修长,看得出很健壮,给人一种爆发力很强的感觉,这会儿嘴里叼着根烟,对着深渊发怔。
他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却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要知道在这种强风下,普通人早就腿软了。
我找了边上一个人问,没问出这个人到底是谁,只知道是刚来的,据说是个很厉害的苏联专家。
我还想问个仔细,这时土炮响了,整个地面狠狠地震了一下,我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了过去。只见铁坨子带着钢缆飞入深渊,但是很快力竭掉了下去,垂直落下。
一边的钢缆被抽出,在空中舞动,越动越长,周围的空气发出犀利的破空声,这种时候如果被打到脑袋都会被削去半个。
安全第一,我又退后了几步,钢缆下坠的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钢缆不再抽出,舞动重新平息下来,我才敢再次靠近。那条四五十度角的缆绳已经刺入了大坝下的黑暗里。*br*“结不结实?”王四川问。
几个工程兵抓住静止下来的钢缆,用力往下压,道:“这是打桩机用的钢丝绳,你说结不结实?”
王四川学着他的口音:“好,我相信你,我摔下去你赔我脑袋。”
“赔你赔你,你是头大象我都敢这么说!”那工程兵道,看得出他确实很有信心。
我们以后会顺着这根钢缆下去,看到这种信心还是很高兴的。
王四川笑着去递烟,我上去吊了一下,果然钢缆纹丝不动,顿时安心了不少。
钢缆的另一边开始在大坝一端进行加固,用卷扬机把钢缆弄直,尽量避免风压的影响而晃动。在钢缆附近,我清楚地听到狂风略过的震动声。
王四川很快就和几个工程兵熟了,开始打听,我看着钢绳连着的深远的 黑暗,总觉得,自己能从中看出什么来。
等我想起了那个苏联人,把注意力再次提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走过去,也坐在大坝的边缘,却被烈风吹得差点刮下去,不由得心生恐惧终于放弃。
这一次照面以后,过了很久我都没有再见到他,对他的疑惑倒没什么困扰我,毕竟我最大的问题远比这严重多。
不过我在茶余饭后的一些言论中,大概知道了他的来历。这个人名叫伊万,来了没多久,经常在司令部出没,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大领导对他都很客气。*br*王四川想到,该不是又来了个要搞左倾的。我说,早不是苏联人能左右的时代了,只不过这种人出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一周后,所有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我们开了个小小的动员的大会后背起装备,准备出发。
打头的是两个工程兵,这条钢缆的承重能力足够吊起一百个我们,但是为了保险,我们还是两人一组,用滑轮滑下去,约定安全到达以后以信号弹为信号。*br*轮滑的速度极快,两个工程兵戴上了防毒面具,连目送的时间都没有,就消失在了黑暗里,只有钢缆的振动表示他们挂在上面。
我已经谈不上紧张了,趁着现在多抽了根烟,一直耐心等待着,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也没有等到信号弹。两个工程兵好像被黑暗吞没了一样。*br*他们消失了。
我和王四川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现场指挥,现场指挥的面色已经铁青了。
行动立即取消,老田被叫去开会,上头还给我一个任务,安定人员鼓舞士气,不要被牺牲和困难吓倒。
两个人下落不明,老田去开会,我和王四川不需要教育,只剩下一个工程兵,我也不知道这打气会该怎么开,不过这小子确实吓得够呛,坐在我们面前,腿都直哆嗦。*br*这些工程兵在林子里出生入死,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