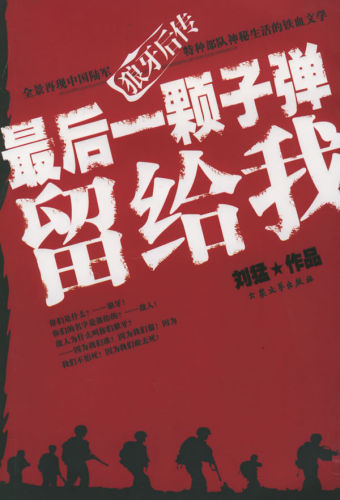一颗铜纽扣 反间谍小说-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蓦地抓住了她的胳臂,把它们拧到了她的背后。做得完全象小孩子打架时那样。
扬柯夫斯卡亚喊了起来:“您疯了吗?”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情势迫使我只得这样做。
“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勉强地喊了一声,但是我一点儿没客气,伸出手去就捂住了她的嘴。
我用系门帘的带子把她的两只胳臂缠到了她的身上,就把她按到椅子上了。
看样子她是以为我喝醉了酒,所以她就不准备反抗了。
“不要这样,”她声音喑哑地嘟哝说,“不要……”
我毫不客气地把她检查了一番;她总是把她的手枪放在她的手提囊里或者是大衣口袋里,对她多加点小心是应该的。
我用台布捆住了她的两条腿,我就在她对面坐下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要明白,”我说,“您这回落到了我的手里,您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您要是不讲话我就总这样捆着您。如果到头来还是不讲,那我就打死您,尽管可能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我也要冒险回到我们自己人那里去……”
扬柯夫斯卡亚刚才还茫然无措,神情沮丧,准备听我的摆布,这时却突然有了精神,她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眼珠儿象猫的一样,变得娇绿了。
“啊哈,您要问话吗?”她讥诮地问道,“那好,请吧!”
‘您到底是谁?”我问道,“说吧。”
“您也是这样,”她说,“预审员开头儿也都是这样问。我叫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杨柯夫斯卡亚。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您本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我说,“您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若是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里干工作那又怎样呢?”她问道,“如果说是他们要我搭救您呢?”
“先开枪,而后再救吗?”
“唔,好啦,别扯这个了。”她同意了,“我自然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个游击队员……”她动了动胳臂。“我很不得劲,”她说,“您可以放开我吗?”
“不成。”我断然地回答她说,“我不把全部问题弄清楚绝不放开您。”
“随您的便吧。”扬柯夫斯卡亚很服贴地说,“如果您—定坚要问,那我就回答您。”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我问道,“不要再捉迷藏了!”
“我?”扬柯夫斯卡亚眯起了眼睛,“我是个间谍。”她把这话说得非常自然,就仿佛说是个裁缝或是食堂管理人似的。
“您是为哪一个间谍机关工作的?”我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就算是为英国间谍机关工作的吧。”
“不是给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吗?”我问道。
“如果我是在为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您现在就不会果在这里,而是落到拘禁政委、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去了。”
“就算这样吧,”我同意了,“那么,您的领导人是谁?这里吗?”
“是的,他也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意味深长地说。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是您。”杨柯夫斯卡亚说。
“别开玩笑吧。”我说,“正经地回答。”
“这是正经的,”扬柯夫斯卡亚说,“我的直接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您。”
她确实把话说得很正经。
“您把话说清楚,”我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噢!”她很宽厚地减道,“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您自己就会猜到这一切的……”
她严峻地望着我,她那双灰眼睛在这一瞬间仿佛现出嘲笑又象是愤怒的眼神,但她马上又抑制住了由于自尊心受到委屈所引起的愤怒,她的脸上又现出了冷漠和疲倦的神情。
“我本想准备使您逐渐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低声安详地说,“但是既然您等不得,那就依着您吧……”
于是她终于说出了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其实,我并非是出于无谓的好奇,因为也有我参加在内的这场把戏是关系到人命的。虽然她很不愿意讲,但到底还是讲出来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要点,首先应当对我有所了解。”她挑衅般地、很自负地说,声音却很安详,“但是因为您不能也不愿意了解我,所以我尽量少谈我自己……”
她冷笑了笑,就把她认为应该告诉我的讲给我听了。
“戴维斯·布莱克是五、六年以前来到里加的,我来得比较晚。他是用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人世间是否真有这一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画家,在巴黎受过专门的教育。布莱克在里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看来也可能真有道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其人,也确是一个画家,并且确实曾在巴黎受过教育。这一切都是很可能的。但是,从巴黎回到拉脱维亚的却是另外一个贝尔金了。我不晓得真正的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藏在哪里。他也许还呆在巴黎,也许到了南美,或者也许是叫汽车撞死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父母当时已经去世,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揭破戴维斯·布莱克的假相了。假如有一些老相识觉得阿弗古斯特有些不象了,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过了好些年,好多人都会变样的,又何况这好些年还是在巴黎那样的城市里度过的呢!您一定会懂得这种伪装的意义了吧?戴维斯·布莱克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他被指派为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他选择里加作了他的安身之处。这个城市不愧称为间谍中心。里加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局面使它变成了各色冒险家的乐园,好多间谍机关正是以里加为中心向各处进行活动的。布莱克做了一番工作,他的联系扩大了。于是,我就被派来协助布莱克……”
“于是您嫉妒他的成就,”我插嘴说,“就决定把它除掉,要占据他这个位置?”
扬柯夫斯卡亚瞧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一方面含着痛苦,另一方面也含着轻视的神情:在她看来,在判断谍报机关工作这方面,我一定是显得特别幼稚。
“您可大错特错了。”她宽厚地反驳说,“干掉和您一同为一个……目标而工作的人,那是不明智的。”她又显得有些活跃起来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她又继续讲了下去,“但是,情况越复杂,间谍机关的工作就越困难。德国人攫取了波兰,又进占了法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生活变得飞快,象万花筒一样,因而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侦探人员,一个秘密组织的几乎手无寸铁的间谍人员有时就担负着加速或延缓历史前进的使命……”
“您把间谍这种职业说得怪不错的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
“完全正确,实际的生活要粗暴和可怕很多。”扬柯夫斯卡亚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您初次见到我的那一天晚上,布莱克被人打死了……”
“谁打死的?”我打断了扬柯夫斯卡亚的话。
“这还没有弄清楚!”她没有正面问答我,“打死布莱克以后就……”
“向我开了枪。”我替她说完了这句话:“打死布菜克的原因是可以猜到的,但是为什么要打死我呢?……”
“啊,无论什么都会事出有因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因为您看到了一些不应被人看到的事……”
“这多亏了您。”我说,“我并没有强要给您作伴……”
“这无关紧要,……”她仿佛想逃避我的责难,“可是,您却比戴维斯走运……”
“是由于您不会打枪吧?”我问道。
“不,我会打枪,”她反驳说,“但是,当我瞄准您的那一瞬间,我却突然想把您留下来,用您来顶替布莱克……”
“是德国侦察机关把他打死的吗?”我问道,“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打死了布莱克。”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还没有弄清楚。”扬柯夫斯卡亚又重复了一遍,“苏联的侦察机关也是能够那样巧妙地把他打死的。”
我不想同她争论。
“可是您我找来干什么呢?”我问道。
“噢,这一点可相当重要。”扬柯夫斯卡亚高兴地解释说,“重要的是应该叫英国人和德国人以为布莱克还活着。假如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布莱克死了,那就会另外派来一个头子,谁知道我能不能同他工作得合手。此外,德国人对布莱克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不使他们失望,对您也是有好处的。我认为他们一定会设法诱致您,所以您就得装做既为英国人工作,也为德国人工作。”
“我若是不装做为任何一方面工作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又会怎样呢?”
“那您就会随着可怜的戴维斯一路去了。”扬柯夫斯卡亚很干脆地说,“在这场把戏里淮也不会让淮的。”
“假如我还是不同意呢?”我又重复了一遍,“您怎能保证我不会找机会跑回自己人那里去呢?”
“人都依恋生活,”扬柯伏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您是正常的人,并且愿意活下去,到苏俄去那你只有一死。”
“一死?”我很奇怪,“为什么呢?”
“对一个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扬柯夫斯卡亚说,“让俄国人认为您已经被外国网罗去,又被送回去从事间谍活动,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您和我搞在一起就已经声誉扫地了……”
我确实打算活下去。但我认为死比毁损名誉更好些。不管他们怎样败坏我的名誉,我总还是要跑回自己人那里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聪明些,所以暂时还可以搅到扬柯夫斯卡亚搞的这个把戏里去。
“您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问道。
“您先把我放开吧,我的胳臂和腿都麻木了。”她说,“至于您,您就装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时期已经满好了。”
我把她放开了。她把我打死对她并没有好处,我也不准备打死她。何况不事先做好准备,要想从里加逃走也根本办不到。
“可是您还没有对我解释接吻那桩事呢。”我说,“那天夜里,坐在汽车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后来您为什么又到了楼梯上?”
“啊,这都是细则!”她满不在意地说,“您总会弄清楚,这并不是要点。”
“要点究竟在哪里呢?”
“在明天。应当行动起来,而不是向后看。”
“我到底应当怎样做呢?”
“我已经说过,您要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阶段就满可以了。”
“可是您没有想到您要我装作戴维斯·布莱克有可能被别人看破吗?”我反驳说。
“噢,不会的,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解释说:“贝尔金有他自已的一些熟人,其中有些右倾分子,他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天里就从里加逃跑了,至于其中的一些左倾分子,他们已经同苏维埃机关一同撤退了。最后,假如您的女厨师和您的情人对您的身分都不怀疑,还有谁敢怀疑您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
“谁是我的女厨师以及她在想些什么,这我已经知道了。至于情人,那可不妙,我可不知道我的情人是谁。”
“难道您没有猜到吗?”扬柯夫斯卡亚一面伸动着她那麻木了的胳膊一面讥俏般地问我,“不然的话,我就未必那么清楚布莱克的一切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这样吧,阿弗古斯特,”她很正经地说,“我去洗个澡,收拾一下,您换一身衣服,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您是否确实象我以为很象的那个贝尔金。”
我听了她的话,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下了楼,我坐过的那辆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谁的汽车?”我问道,“是您的还是我的?”
“是您的。”她回答说:“但是我不想现在就交给您。”
这是很明显的。
她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车开得很好。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道,“这不是秘密吧?”
“不是。”她回答说,“我们到格列涅尔教授家里去,您能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
“就是我在病院里曾经见过的那个高个子吗?”我猜到了,“我用什么名字同他见面呢?”
“他知道您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但他怀疑您是戴维斯·布莱克。”


![[综漫]穿成一颗球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887.jpg)


![[综]一颗龙珠引发的血案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6/7609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