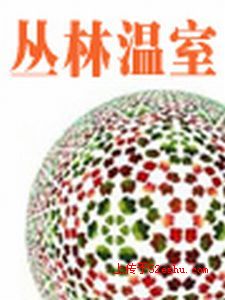毒气室-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样教你的,我只知道应当由我作决定。”
萨姆走到一张空着的椅子旁,又拿起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说道:“这封信是给州长的,要求他取消周一的赦免听证会。如果你拒绝取消的话,那我就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新闻界,我要让你、加纳·古德曼和州长都下不来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明白不过了。”
萨姆将信放回椅子上,又点燃了一支烟。
亚当在他的备忘录上又画了个圈。“卡门周一要来这里,我不敢保证莉能来得了。”
萨姆缓缓走到一把椅子前坐下,眼睛并不着亚当。“她还在康复中心吗?”
“是的,不清楚她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你想要她来吗?”
“容我再想想。”
“要快些,好不好。”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弟弟唐尼刚刚来看过我,他是最小的弟弟,他想见见你。”
“他也是三K党徒吗?”
“这算什么问题?”
“是个只需要回答是与否的问题。”
“是的,他是三K党。”
“那我不想见他。”
“他不是坏人。”
“我相信你的话。”
“他是我兄弟,亚当,我要你见的是我兄弟。”
“我不想再见到凯霍尔家的其他成员,萨姆,特别是那些穿长袍戴尖顶帽的人。”
“噢,真的吗?三个星期前你恨不能把这个家底翻过来,生怕知道得不够多。”
“我认输,好不好?我听到的够多了。”
“噢,事儿还多着哪。”
“够了,我够了,你饶了我吧。”
萨姆咕哝了一句什么,有些自得地笑起来。亚当看了一眼拍纸簿说:“有件事你听了也许会高兴的,监狱外面除了三K党外又来了一些纳粹分子、雅利安人和光头党,还有其他崇尚仇恨的组织。他们都沿着高速公路站成一排,向过往的汽车挥动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的当然是要求释放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萨姆·凯霍尔,真像个热闹的马戏场。”
“我在电视上看过了。”
“他们在杰克逊的州议会大厦周围也举行了抗议示威。”
“那是我的错吗?”
“不是,但都是因为你的死刑。你如今成了偶像,就要成为殉教士了。”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做。就等着执行死刑好了,那样就称他们的心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对不起,萨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诚恳地建议你甩掉那些压力,像我一样。”
“不行,我已经把那些蠢货掌握在手里,萨姆,我还没跟他们动真格的。”
“是吗,你提交了三轮诉状,各级法院已经有七次把你驳回,你的得分是零比七,我不想看到你动真格时会是什么样子,”萨姆说这些话时脸上挂着一种顽皮的笑容,字字句句都透着调侃。亚当也笑了笑,两人之间的气氛缓和了一些。“我想过了,你走了以后我要起诉他们,”他显得很激动地说道。
“我走了以后?”
“没错,起诉他们滥用死刑,被告就是麦卡利斯特、纽金特、罗克斯伯勒以及密西西比州。我们要起诉所有那些人。”
“还没有谁那样做过,”萨姆捋着胡须说,好像是在认真考虑。
“是的,我知道。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也许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但只要想想我在今后五年中会怎样折腾那些杂种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同意你那样做,起诉他们!”
笑容渐渐隐去,幽默也不复存在。亚当在备忘录上又看到另外一些事项。“还有几件事要说一下。卢卡斯·曼让我问问你见证人的事,你只能有两个见证人在见证室里,我是说真要到了那一刻。”
“唐尼不想干,我也不想让你在那里。不知道还有谁会愿意当那个见证人。”
“好吧,我就这样答复。我至少收到了三十个采访要求,几乎各大报纸和新闻杂志都提出了要求。”
“不见。”
“好吧。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作家温德尔·舍曼吗?那个想要给你录音的人,还有——”
“对了,还有五万美元。”
“如今加码到十万了,由他的出版商为他筹集资金。他要把一切都录下来,还要去执行死刑的现场,然后进行深入研究,再写一个大部头出来。”
“不干。”
“好的。”
“在今后三天里我不想再谈论我的生活经历,我不想让某些不相干的人到福特县去乱打听,而旦我活到这当儿最不需要的就是那十万美元。”
“我都清楚了。你曾经说起过穿衣服的事——”
“唐尼答应办这件事。”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如果得不到缓期的话,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可以有两个人陪伴你。按规定,狱方有一张表格需要你签字并指定这两个人。”
“一般应该是律师和牧师,对不对?”
“没错。”
“那就是你和拉尔夫·格里芬啦。”
亚当把名字填入表格。“谁是拉尔夫·格里芬?”
“是监狱里新来的牧师,他反对死刑,你能相信吗?而他的前任则恨不能把我们都给熏死,当然是以基督的名义。”
亚当把表格递给萨姆。“在这儿签字吧。”
萨姆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把表格还给亚当。
“你有享受最后一次配偶探访的权力。”
萨姆大笑起来。“拉倒吧,孩子,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是清单上的,明白吗?卢卡斯·曼私下跟我讲说我应该告诉你。”
“好了,你已经告诉我了。”
“我这里还有一张有关你的私人物品的表格,要写明继承人是谁。”
“你是说我的遗产吗?”
“差不多。”
“这实在病态,亚当,我们干嘛现在就做这件事?”
“我是律师,萨姆,我们有责任落实一切有关细节,这些都不过是些书面上的文章。”
“你要我的东西吗?”
亚当听到他的问题后想了片刻。他不想伤萨姆的感情,但同时他也实在想不出怎样去处理他那几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旧书以及一台小电视机和那双橡胶拖鞋。“我要,”他说道。
“那它们就属于你了,把它们拿去一把火烧了。”
“在这儿签字吧,”亚当说完将表格推到他的面前。萨姆签完了字,又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我真想让你见见唐尼。”
“没问题,只要是你的要求我都会照办,”亚当说着把拍纸簿和表格收拾好装进公文包里。所有的细节都已落到了实处,亚当觉得公文包更显得沉甸甸的。
“我明天一早再来,”他对萨姆说。
“给我带点好消息来,好吧?”
纽金特上校趾高气扬地沿着高速公路的外侧向前走着,后面跟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卫。他怒视着那二十六个三K党徒,又向那十来个穿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分子皱着眉头,还停下脚步虎视眈眈地望着离纳粹分子不远的一群光头党。他摇晃着身子,围着那片狭长的示威专用草地外侧转了一圈。两个信奉天主教的嬷嬷坐在尽可能远离其他示威者的地方,他停下来同她们聊了几句。这时的气温足有华氏一百度,嬷嬷们坐在荫凉地里还在冒汗,她们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把标语牌靠在膝盖上望着高速公路的方向。
两位嬷嬷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他说自己是监狱的代理典狱长,来这里只是为了确保示威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于是,她们让他离远点。
……
四十三
也许因为是星期天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正在下雨,亚当在喝早晨的咖啡时显得出奇的从容。外面仍然很黑,温乎乎的夏日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阳台上,把人带入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境界。他站在敞开的门边,听着那雨滴的溅落声。时间还太早,下面沿河公路上还听不到车声,也听不到河里有拖船的声音,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详和。
今天是死刑执行前的第三天,他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一会儿要先去办公室,还有一份最后时刻诉状要起草一下,那份诉状的争点是如此的荒谬,亚当几乎不好意思把它交出去。然后他要去帕契曼和萨姆一起坐一会。
看起来各法院在星期天都不会有什么动作。当然,大限已经临近,负责死刑的书记宫和他们的助手们很有可能会加班。不过,周五和周六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他估计今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而明天就完全不同了,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看法,不太成熟,也没有经过检验。
明天自然免不了会非常繁忙,而周二无疑会像恶梦一般的紧张,那是法律规定萨姆在世的最后一天。
但这个周日却格外平静。他睡了差不多有七个小时,堪称是最近一段时期的又一项纪录。他的头脑清醒,脉搏正常,呼吸轻松,他的心绪平静而从容。
他翻动着周日的报纸,心不在焉地把标题浏览了一遍。里面起码有两篇是有关凯霍尔死刑的报道,其中的一篇配发了更多的监狱外面越演越烈的示威场面的照片。太阳出来时雨停了下来,他坐在一把湿漉漉的摇椅上看了一会儿莉的建筑杂志。经过几个小时的平和安宁以后,亚当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准备动身。
在莉的卧室里还有一件未了的事,一件亚当一直想忘却但又难以忘却的事。十天来,他的心里一直在为她抽屉里的那本书而激烈斗争着。她是在酒后告诉他私刑照片的事的,但那并非一个瘾君子的痴人说梦。亚当知道那本书就在那里,那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里面有一张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被用绳子吊起来的黑人青年,他的脚下是一群骄傲的白人,那些人正在对着照相机做鬼脸,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起诉。亚当在内心里反复拼贴着那张照片,给它添上新的面孔,勾画树的轮廓,画上绳子,并在它的下面加上标题。但有些事他还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那个死者的面孔能够看得清楚吗?他的脚上是穿着鞋子还是赤着脚呢?那个小萨姆容易辨认吗?照片里有多少白人的脸孔?他们有多大年纪?有妇女吗?人们带着枪吗?有没有血迹?莉说他曾经被牛皮鞭子抽打过的,在照片里能看见鞭子吗?他几天来一直在想着那张照片,是到了看看那本书的时候了,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也许莉就要康复归来,那时她会重新把它藏起来。他计划在今后的两三天里仍住在这里,但没准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一切全部打乱。他也许不得不被迫赶去杰克逊或是在帕契曼睡在自己的车子里。当你的当事人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日子时,像午餐、晚餐和睡觉一类的寻常小事便都会变得莫测起来。
现在是天赐良机,他终于下了决心去面对那群施私刑的暴徒。他走到前门向停车场的方向望了望,只是想确认一下她还没有回来的迹象。他甚至还锁上了她的卧室房门,然后才拉开了那个抽屉。抽屉里放着的都是她的内衣,他对自己的唐突行为感到有些难为情。
他在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那本书,就放在一件褪了色的汗衫上面。书很厚,封面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南部黑人和大萧条时期。匹兹堡托夫勒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亚当把书拿出来坐到了床沿上,书页非常新,像是从来没有翻看过的样子。生活在最南部的人有谁会看这样的书呢?虽说这本书在凯霍尔家已经放了有几十年之久,但亚当确信根本不会有人看它。他看了看书的封皮,猜测着这本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归到了萨姆·凯霍尔家的名下。
这本书共有三部分照片。第一部分都是些简陋的房舍和破败的棚屋,是种植园里黑人被迫居住的地方。有带着十几个孩子的父母在门前拍摄的全家照,也有农工们被迫在田里弯着腰摘棉花的情景。
第二部分插在书的中部,大约有二十多页。有关私刑的照片只有两张,前一张是两名身穿白袍头戴尖顶帽的三K党徒正在用步枪向照相机瞄准的可怖场景,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男人吊在他们的身后,眼睛半开半闭,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照片说明写道:三K党施行私刑,密西西比州中部地区,一九三九年。似乎这种种族歧视的暴行可以用地点和时间限定似的。
亚当凝视了片刻那张令人发指的照片,然后又翻到第二张有关私刑的情景,这张比起头一张来显得不是那么很恐怖。绳子上吊着的死者只能看到胸部以下。衬衣似乎被撕碎了,可能是皮鞭抽打的结果,如果的确使用过皮鞭的话。那名黑人身体很瘦,肥大的裤子紧紧地箍在腰间,双脚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