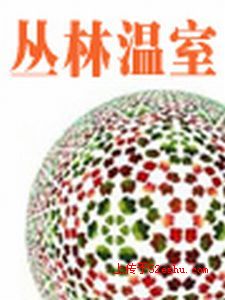毒气室-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辄用轮奸威胁那些犯有极小过失的犯人。这些新科犯人很少有再回到帕契曼的。
“纽金特是疯子,奈菲。他早晚会伤害什么人的。”
“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准备让他去伤害萨姆,该怎么就怎么呗。按书上指示做。天知道纽金特有多么热爱遵从书本。他是最好的人选,卢卡斯。这会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死刑。”
对于卢卡斯来说这无关宏旨。他耸耸肩说:“你是老板。”
“谢谢,”来菲说,“看住纽金特,行吗?我这头的事由我盯着他,法律上的事你来把关。我们会办好这件事的。”
“这将是迄今最轰动的一次处决,”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我老了。”
卢卡斯收拾起桌上的材料向门口走去。“等那个孩子走了后我会给你打电话。他应该在走之前来见我。”
“我很愿意见他,”奈菲说。
“他是个好孩子。”
“有的家庭,哼。”
这个好孩子和他的判了罪的祖父静静地沉默了十五分钟,房间中唯一的声音是负担过重的空调器困难的喘息。亚当走到通风口挥了挥手,那儿多少有一股凉气。他抱着双臂靠在台子边上眼睛盯着门,尽量离萨姆远些。这时门开了,帕克警官把头探进门。他说只不过看看是不是有事,先看了亚当一眼,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透过隔板目光落在萨姆身上,萨姆正坐在那儿用手捂着脸。
“我们很好,”亚当说,并没有看萨姆。
“好,好,”帕克连忙关上门,锁好。亚当慢慢回到他的椅子上。他把椅子向前挪了挪,身子用肘支撑着更靠近隔板。萨姆有两分钟没有留意他,然后坐起来用袖口擦擦眼睛。他们互相望着。
“我们需要谈谈,”亚当静静地说。
萨姆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用另一只袖口又擦了擦眼睛。他把烟放在两唇之间,打火时他的手在发抖。他极快地吐出一口烟雾。
“那么你真的是艾伦,”他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知道。”
“你生于一九六四年。”
“非常正确。”
“我的长孙。”
亚当点点头看着别处。
“你是一九六七年消失的。”
“差不多吧。你知道我不记得这些。我最早的记忆是从加州开始的。”
“我听说埃迪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有了另一个孩子。有人后来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卡门。我这些年里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知道你们全都在南加州的什么地方,但他确实很成功地消失了。”
“我小时候我们到处搬家,我觉得他很难保住一份工作。”
“你原来不知道我?”
“不知道,家里从来不提起。我是在他的葬礼后才发现的。”
“谁告诉你的?”
“莉。”
萨姆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又喷出一口烟。“她好吗?”
“我想,不错。”
“你为什么要去给库贝事务所干事?”
“那是一个挺好的事务所。”
“你知道他们代理我吗?”
“知道。”
“看来这些都是你计划的?”
“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可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你总是有原因的。”
“原因很明显。你是我的祖父,行了吧。喜欢不喜欢都一样,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现在我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应该离开。”
“我不离开,萨姆。我已经准备了好长的时间。”
“为的什么?”
“你需要合法的代理人,你需要帮助,所以我来了。”
“帮助我也没用了。他们决心毒死我,知道吧,原因很多。你不必卷到这里面。”
“为什么不?”
“嗯。第一,这事没有希望。你搅进去了肯定会受到伤害而且不会成功。第二,你的真实身份就会暴露。那将是挺尴尬的事情。如果你仍然是亚当·霍尔,生活对于你会好得多。”
“我是亚当·霍尔,我不准备改变它。同样,我是你的孙子,我们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对吧?所以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会让你的家庭非常尴尬。埃迪把你们保护得很好。别糟蹋了他的努力。”
“我的保护层已经被糟蹋了。我的事务所已经知道这件事。我告诉了卢卡斯,而且——”
“那个混蛋会告诉所有的人。一分钟也别相信他。”
“是这样,萨姆,你不理解。我不在乎他是否告诉别人。我也不在乎全世界是否知道我是你的孙子。对于这些肮脏的家族小秘密我早就受够了。我是个大人了,能够独立思考。此外我是律师,我的脸皮会越来越厚。我会处理得好。”
萨姆在他的椅子里放松了一些,似乎有点高兴地望着地板傻笑了一下。这是那种大人看到孩子整个一副小大人的表现而露出的笑容。他嘟囔着什么然后慢慢地点点头。“你其实不懂,孩子,”他仍然坚持着,但语调却是耐心而有分寸的。
“那就解释给我听,”亚当说。
“那话可就长了。”
“我们有四个星期。四个星期中你可以讲不少东西。”
“确切地说,你真想听的是什么?”
亚当把支撑他的双肘向前挪了挪,把笔和纸放好。他的眼睛离隔板上的窗口只有几英寸。“首先,我想谈谈案子——申诉、策略、审判、爆炸、那天晚上你和谁在一起——”
“那个晚上没人和我在一起。”
“这咱们可以以后再谈。”
“咱们现在就谈。就我一个人,你听清了吗?”
“好的。第二,我想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要隐瞒起来?我想知道你的父亲和祖父,还有你的兄弟和表亲。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可能不喜欢他们,但我有权力知道他们。我长这么大一直被剥夺了了解的权力,现在我要知道。”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噢,是吗。这么说,萨姆,你给关在这个死监里就挺值得一说。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社会。事实上你是白人,中产阶级,快七十岁了,这就使事情更加值得一说了。我要知道你是为什么和如何来这儿的。是什么使你干了那些事?我们家有多少三K党徒?为什么?有多少人像这样被他们所杀?”
“那么你觉得我会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会改变主意的。我是你的孙子,萨姆,是还关心你的唯一在世的、还喘气的亲属。你会讲的,萨姆,你会跟我讲的。”
“行了,既然我会这么多嘴,还有别的什么可讨论的吗?”
“埃迪。”
萨姆深深地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你想知道的不多,是吗?”他温和地说。亚当在他的纸上瞎划着什么。
现在是点燃另一支香烟的时候了,萨姆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一程序。又一股蓝色的烟雾腾起,使得萦绕在他头顶上的烟雾更浓。他的手又稳住了。“等我们谈完了埃迪,你还想谈谁?”
“我不知道。那已经够咱们忙四个星期的了。”
“我们什么时候谈谈你?”
“什么时候都行。”亚当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卷宗。他把一张纸和一只笔从窗口递过去。“这是律师代理协议。在最下边签上字。”
萨姆没有去碰它,而是远远地读着。“这么说我又和库贝事务所签约了。”
“差不多。”
“什么意思,差不多?这么说我同意让那帮犹太佬再一次代理我。我费了那么大劲才甩掉他们,而且,妈的,我甚至没有付给他们钱。”
“这个协议是和我签,萨姆,行了吧。除非你愿意,你永远也不会见那些家伙了。”
“我不愿意。”
“好。只是我碰巧为这家事务所工作,所以协议必须和事务所签。这容易。”
“噢,乐观的年轻人。什么事都容易。我坐在这儿离毒气室不到一百英尺,时钟在那面墙上嘀嘀嗒嗒地走,越来越响,还说所有的事都容易。”
“签了那个见鬼的文件,萨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工作。从法律上讲,没有那个协议,我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
“开始的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
“把克雷默爆炸案过一遍,非常仔细,一步一步地来。”
“那已经做过上千次了。”
“我们再做一次。我有厚厚的一本问题。”
“那些问题都问过了。”
“是啊,萨姆,可是那些问题没有被回答过,对吗?”
萨姆把烟蒂叼在嘴上。
“何况我还没有问过,对不?”
“你以为我说谎?”
“你说呢?”
“没有。”
“但你没有讲出整个的故事,对不?”
“这又有什么不同,法律顾问?你总该看过贝特曼案吧。”
“是的,我记得贝特曼。其中有不少疑点。”
“标准的律师。”
“如果有新的证据,就会有办法呈送法庭。我们现在要做的,萨姆,就是设法混淆情况,以使某些法官在某些地方再而三地重新考虑。然后他就会批准一项延缓令,以便了解更多情况。”
“我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孩子。”
“亚当,行吗,叫我亚当。”
“好的,那你就叫我爷爷。我估计你要上诉到州长。”
“是的。”
萨姆向前挪了挪椅子接近隔板,用他右手的食指点着亚当的鼻子。他的脸忽然严厉起来,眼睛眯着。“你听我说,亚当,”他咆哮着,手指戳来戳去,“如果我签了这张纸,你永远不能和那个浑蛋谈话,永远。你明白吗?”
亚当看着他的手指什么也没说。
萨姆接着说:“他是个婊子养的冒牌货。他的卑鄙、下流、彻底腐化全都被一副有漂亮笑容和梳理整洁的头发的面具所掩盖。全是因为他我如今才坐在这个死监里。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你和他联系,你就再别做我的律师了。”
“那就是说我已是你的律师了。”
萨姆把手指放下,放松了一点。“我也许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拿我练习练习。你知道,亚当,法律界实在是乱七八糟。如果我是个一心谋生、安分守己、按时纳税、遵纪守法的自由人,那不会有律师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除非我有钱。可我现在在这里,是个定了罪的杀人犯,被判了死刑,在我名下没有一分钱,而全国的律师却都来求我,想要代理我。大律师,有钱的律师,有长长的名字,前面有缩写,后面有数字,大名鼎鼎的律师,他们拥有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和电视节目。对此,你能解释吗?”
“当然不能。这些我也不关心。”
“你进入的是一个病态的行业。”
“大多数的律师是正直勤奋的。”
“不错。死监里我的大多数同伴如果不是被错误地判罪,他们也可能是牧师或传教士。”
“州长或许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那他们还是现在就把我送进毒气室吧。那个目空一切的浑蛋或许正想看我被处死,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把行刑的每个细节公之于众。他是条没骨头的虫子,都是因为我才爬到这么高。要是他能从我身上挤出奶来他也会干的。你离他远点。”
“我们以后讨论这件事。”
“我们现在就讨论,在我签这张纸之前你得向我保证。”
“还有条件?”
“是的。我希望在这儿加上一条,讲明如果我决定解雇你,你和你的事务所不得反对。那样会容易些。”
“让我看看。”
协议又从窗口递出,亚当在纸的最下边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一段。他把纸还给了萨姆,萨姆把纸放在台子上,仔细地读了一遍。
“你还没签名,”亚当说。
“我还在考虑。”
“在你考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问几个问题?”
“你问吧。”
“你在什么地方学会的爆破?”
“到处都学。”
“在克雷默之前起码有五起爆炸,全是同一类型,都是很初级的——炸药、雷管、导火线。当然克雷默案有所不同,因为用了定时器。谁教给你制造炸弹的?”
“你放过鞭炮吗?”
“当然。”
“同样的原理。用火柴点着导火线,拼命地跑,就炸了。”
“定时器可有点复杂了。谁教你如何接线的?”
“我母亲。你计划什么时候再来这儿?”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