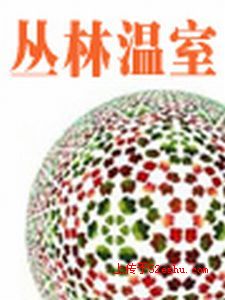毒气室-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想见到她,但埃迪却说她不是好人而不让见。他们的母亲小声告诉他们,莉实在是个好人,有一天她会带他们去孟菲斯见她。
反而是莉去了加州,和他们一起埋葬了埃迪。葬礼后她住了两个星期,与侄子侄女混得很熟。他们爱她,因为她漂亮又潇洒,穿着牛仔裤与T恤,赤脚在沙滩漫步。她带他们逛商店,看电影,在海岸边作长长的散步。她用许多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早来。她说她想来,也答应过,只是埃迪不许她来。他们从前打过架,他不愿意见她。
最后,还是和亚当坐在码头上一起观看夕阳沉入太平洋的莉姑姑谈到了她的父亲,萨姆·凯霍尔。海浪在他们脚下轻柔地拍打着,莉给亚当讲述了当他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曾在密西西比那个小镇呆过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她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盖,揭开了他们家族悲惨的历史。她赤裸裸地列出萨姆参加三K党活动的细节,克雷默的爆炸案,以及那些终于把他送进密西西比死牢的审判。她的口述中虽说有不少的漏洞,但她很有策略地包含了所有要点。
对于一个刚刚丧父、尚不成熟的十六岁少年,亚当接受整个事情的表现却非常得当。他问了几个问题,海上的冷风吹来,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个可怕的故事给他一种奇特的安慰。在他的世界之外竟有一个家族在那里!或许他根本不是与常人不同。或许他也有不少可以分享人生经历的叔伯姑姨表兄弟姊妹。或许也有几栋由真正的祖先建造的老房子,还有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农场。他终归还是有来历的。
但是莉是聪明人,她及时觉察到他的兴趣所在。她解释说凯霍尔家族是个奇特而秘密的家族,他们自我封闭,回避与外人接触。他们不是那种到了圣诞节就团圆,逢七月四日国庆必聚会的友好热情之人。她住在离克兰顿只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却从未见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日暮时分去海堤成了一种仪式。他们会先在市场上买些红葡萄当零食,把籽吐进大海,直到天全黑下来。莉给他讲了在密西西比与她的弟弟埃迪度过的孩提时代。他们住在离克兰顿仅十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农场里,那里有可以钓鱼的池塘和可以骑的小马。萨姆是个和蔼的父亲,不是专制的却也实在不能说是亲切的。她的母亲多病而且不喜欢萨姆,但她溺爱她的孩子。她失去过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那时莉六岁,埃迪差不多四岁。她几乎一年都没走出她的卧房。萨姆雇了个黑女人照顾埃迪和莉。一九七七年她母亲死于癌症,那也是凯霍尔全家最后一次相聚。埃迪曾偷偷跑回家乡去参加葬礼,不过他设法避开了所有的人。三年后萨姆最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刑。
关于她自己的生活莉没有讲多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典礼结束后一个星期她就匆匆离家直奔纳什维尔,打算录制唱片一举成名。不知怎么回事她遇上了费尔普斯·布思,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生,家里开着银行。他们最后在孟菲斯结婚安了家,开始了一种看来并不快乐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沃尔特,他显然相当反叛,现住阿姆斯特丹。关于莉的情况细节只有这些。
亚当拿不准莉是否改过姓。他怀疑她改过,可谁又能责怪她呢?
像来时一样,莉悄悄地离开了。没有拥抱也没有告别,天亮之前她溜出他们家走了。两天后她打来了电话,鼓励亚当和卡门写信来,他们也热切地照办了,可是再也没有了她的信和电话,重新建立联系的保证渐渐地烟消云散。他们的妈妈有一个解释。她说莉是个好人,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凯霍尔家的人,天生就有些忧郁古怪。亚当的梦碎了。
在他从佩琅代因毕业的那个夏天,亚当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半个国家去基韦斯特。他们在孟菲斯与莉姑姑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她独自住在公寓式管理的一套宽敞、现代化的私人套房里,房子坐落在可以俯瞰河上风光的陡峭河岸上。他们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他们三个,吃家里烤的比萨饼,喝啤酒,看过往的驳船,几乎无所不谈,只是从不提及家庭。亚当对于将要上的法学院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莉也有一大堆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她活泼、幽默、健谈,是个称职的女主人和姑姑。当他们拥抱告别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并且央告他再来。
亚当和他的朋友避开了密西西比,取道向东,穿过田纳西州和云雾山。据亚当估算,他们曾一度离帕契曼的死囚牢和萨姆·凯霍尔不到一百英里。那是四年前,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那时他已经收集了整整一大箱有关他祖父的材料,录像带也差不多完成了。
昨晚在电话中的谈话不长。亚当说他会在孟菲斯住几个月,会很高兴去看她。莉邀请他去她的老地方,那个有四间卧房和一个半工女佣的峭岸上的家。她坚持让他住在她那儿。然后他说他将在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工作,实际上他将致力于萨姆的案子。电话的另一头半天没有了声音,接着是个不那么坚定的邀请,无论如何要去她家,他们一起谈谈这件事。
时间已过九点,亚当一面瞟着他的黑色敞篷绅宝一面按下她的门铃。这一排建筑共有二十套,紧密地连在一起,一色红瓦的房顶。一面宽阔的砖墙,墙头上是粗重的铁栏杆,保护着社区不受从孟菲斯市区来的威胁。一名武装警卫守着唯一的大门。要不是房子另一面有河上的景色,这些房子实际上不值多少钱。
莉打开门,他们相互吻了一下面颊。“欢迎,”她说,看了看停车场,锁上了他身后的门,“累了吧?”
“还可以,应该十个钟头的路我走了十二个钟头。我不是很急。”
“你饿不饿?”
“不,我几个小时前吃过。”他跟着她进了书房,两人面面相对,琢磨着说什么合适。她差不多五十岁了,四年来她老了很多。头发已是灰褐各半,并且长了很多。她把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了个马尾。她淡蓝色的眼睛有点发红并且神色焦虑,眼角多了许多皱纹。她穿着宽松的活领棉布衬衫和褪色牛仔裤。莉仍然很潇洒。
“真高兴见到你,”她说,带着亲切的微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咱们坐到阳台上去。”她拉着他的手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木结构阳台上,吊在木梁上的篮子里种着蕨类植物和九重葛。河就从他们下面流过。他们坐在白色的柳条摇椅里。“卡门好吗?”她边问边从一个陶水罐里给亚当倒了一杯冰茶。
“挺好,还在伯克利的研究生院。我们每星期通一次话。她很认真地在和一个小伙子交朋友。”
“她学什么呢?我忘了。”
“心理学。想拿个博士,然后也许教书。”茶的柠檬味太重却不够甜。亚当慢慢地咂着。空气闷热。“马上就十点了,”他说,“为什么这么热?”
“欢迎来到孟菲斯,亲爱的,整个九月都会很烤人。”
“我受不了。”
“你多少会习惯的。我们大量喝茶并呆在屋里。你母亲怎么样?”
“还在波特兰,现在嫁给了一个做木材生意发了财的男人。我见过他一次。他大概六十五岁,说七十岁也像。她四十七岁,看上去像四十。一对漂亮的夫妻。他们飞来飞去,圣巴斯、南部法国、米兰,所有富人都得去看看的地方。她非常幸福。她的孩子长大了,埃迪死了,她的过去已经被彻底埋葬。她有的是钱而且生活得非常正常。”
“你对她太刻薄。”
“我对她太宽容了。她确实不愿意有我在她身边,因为我让她痛苦地联想起我的父亲和他倒霉的家庭。”
“你母亲爱你,亚当。”
“天哪,那可是好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就是知道。”
“我没想到你和我母亲这么亲密。”
“我们并不是亲密。别激动,亚当,轻松点。”
“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仅此而已,我需要强烈点的饮料。”
“放松些。趁你在这儿咱们开开心。”
“我不是来开心的,莉姑姑。”
“就叫我莉,行吗?”
“行。我明天要去看萨姆。”
她小心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离开阳台。她回来时带了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了许多。她一口气喝下了她那杯,望着远处的河面。“为什么?”她终于问。
“为什么不?因为他是我的祖父。因为他要死了。因为我是律师而他需要帮助。”
“他甚至不认识你。”
“明天他会的。”
“所以你会告诉他?”
“是的,我当然要告诉他。信不信?我真打算把凯霍尔家的一个深藏不露的肮脏秘密公开。对此你怎么看?”
莉用双手捧着杯子慢慢地摇摇头。“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着,并不看亚当。
“还没有,但很高兴知道你也关心他。”
“我是关心。”
“真的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别提这些,亚当,你不理解。”
“好的,很公平。给我解释一下,我在听,我希望理解。”
“我们不能谈点别的吗,亲爱的?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心理准备。”
“不。”
“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保证。我只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以为我们只是聊天说笑。”
“对不起,莉。我烦透了聊天和秘密。我没有过去,因为我的父亲轻易地把它抹去了。我想知道它,莉。我想知道到底有多糟。”
“糟透了,”她的声音像耳语,几乎是对她自己讲。
“好的,我是个大人了,我能承受这些。我的父亲在他必须面对这些之前就在我面前溜掉了,所以恐怕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实情了。”
“给我一些时间。”
“没有时间了。明天我就要和他面对面了。”亚当一口气喝了一大口,然后用袖子擦擦嘴。“二十三年前,《新闻周刊》说萨姆的父亲也是个三K党徒,是吗?”
“是的,我的祖父。”
“还有几个叔叔和堂兄弟也是。”
“他妈的一大帮。”
“《新闻周刊》还说在福特县人人都知道萨姆在五十年代初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而且从未因此而被捕,从未在监狱里呆一天。是真的吗?”
“这和现在有关系吗,亚当?那是你出生之前好多年的事。”
“所以真有那么回事?”
“是的,有那么回事。”
“你知道情况?”
“我看见的。”
“你看见的!”亚当似乎无法相信地闭上了眼。他喘着粗气,把身子缩进了摇椅。一艘拖船的汽笛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目光随着它走向下游,直到它从一座桥下穿过。波旁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
“咱们说点别的吧,”莉温和地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仍然望着河流,“我就爱上了历史。我对多少年前人们生活的方式着迷——拓荒者、马车队、淘金潮、牛仔和印第安人、西部移民。曾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说他祖父的祖父抢劫过火车并把钱埋在了墨西哥。他要拉起一帮人跑去找钱。我们知道他是瞎编,但是非常好玩、我经常想象我的祖先,记得我曾因为似乎没有祖先而困惑过。”
“埃迪怎么说的?”
“他告诉我他们全死光了,说人们在家族史上浪费的时间比其他的事都多。每次我问有关家族的问题,我母亲就会把我推到一边叫我把嘴闭上,因为再问有可能惹恼他,也许他会因此情绪低落,在他的卧房里呆上一个月。我的整个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父亲身边都是如履薄冰般提心吊胆。长大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非常怪僻的人,非常不幸,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自杀。”
她晃动着杯子里的冰块喝下最后一口。“事儿还多着呢,亚当。”
“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莉轻轻拿起水罐注满了他们的杯子。亚当兑进波旁威士忌。几分钟过去后,他们边喝边望着河边路上的车流。
“你去过死囚牢吗?”他问,仍然盯着河上的灯光。
“没有,”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在那儿呆了差不多十年,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是最后那次审判之后不久。六个月后他给我回信让我别去,说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死囚牢里。我又写了两封,他一封也没回。”
“我很难过。”
“别难过。我心里非常内疚,亚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