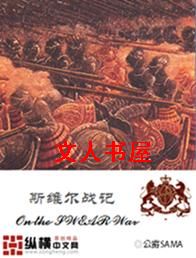3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物会不意地闯进去时所必然会有的那种耐心和兴趣熬了过来。钟敲了一下,又敲了两下,在绝望之中,我们几乎都想再度放弃不干了,就在这时,突然我俩在椅子里猛地坐直起来,已经疲倦的全部感官又重新变得警醒而敏锐了。我们听到了过道里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我们听着那脚步声偷偷摸摸地走了过去,直到在远处消失为止。然后准男爵轻轻地推开了门,我们就开始了跟踪。那人已转入了回廊,走廊里是一片漆黑。我们轻轻地走到了另一侧的厢房,刚好能看到他那蓄着黑须的、高高的身影。他弯腰伛背,用脚尖轻轻地走过了过道,后来就走进了上次进去过的那个门口,门口的轮廓在黑暗中被烛光照得显露出来,一道黄光穿过了阴暗的走廊。我们小心地迈着小步走了过去,在以全身重量踩上每条地板以前,都要先试探一下。为了小心起见,我们没有穿鞋,虽然如此,陈旧的地板还是要在脚底下咯吱作响。有时似乎他不可能听不到我们走近的声音,所幸的是那人相当地聋,而且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干着自己的事。
最后,我们走到了门口偷偷一望,看到他正弯腰站在窗前,手里拿着蜡烛,他那苍白而聚精会神的面孔紧紧地压在窗玻璃上,和我在前天夜里所看到的完全一样。
我们预先并未安排好行动计划,可是准男爵这个人总是认为最直率的办法永远是最自然的办法。他走进屋去,白瑞摩随即一跳就离开了窗口,猛地吸了一口气就在我们面前站住了,面色灰白,浑身发抖。他看看亨利爵士又看看我,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的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白瑞摩?”
“没干什么,爵爷。”强烈的惊恐不安使他简直说不出话来了,由于他手中的蜡烛不断地抖动,使得人影也不停地跳动着。“爵爷,我是夜间四处走一走,看看窗户是否都上了插销。”
“二楼上的吗?”
“是的,爵爷。所有的窗户。”
“告诉你,白瑞摩,”亨利爵士严厉地说道,“我们已决心要让你说出实话来,所以,你与其晚说还不如早说,免得我麻烦。现在,说吧!可不要谎话!你在那窗前干什么来着?”
那家伙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们,就象是个陷于极端疑惧、痛苦的人似的,两手扭在一起。
“我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害处啊,爵爷,我不过是把蜡烛拿近了窗户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蜡烛拿近窗口呢?”
“不要问我吧,亨利爵士——不要问我了!我跟您说吧,爵爷,这不是我个人的秘密,我也不能说出来,如果它与别人无关而且是我个人的事的话,我就不会对您隐瞒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便从管家抖动着的手里把蜡烛拿了过来。
“他一定是拿它作信号用的,”我说道,“咱们试试看是否有什么回答信号。”我也象他一样地拿着蜡烛,注视着漆黑的外面。我只能模糊地辨别出重叠的黑色的树影和颜色稍淡的广大的沼地,因为月亮被云遮住了。后来,我高声欢呼起来,在正对着暗黑的方形窗框中央的远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极小的黄色光点刺穿了漆黑的夜幕。*
“在那儿呢!”我喊道。
“不,不,爵爷,那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管家插嘴道,“我向您保证,爵爷……”
“把您的灯光移开窗口,华生!”准男爵喊了起来,“看哪,那个灯光也移开了!啊,你这老流氓,难道你还要说那不是信号吗?来吧,说出来吧!你的那个同伙是谁,正在进行着的是个什么阴谋?”
那人的面孔竟公然摆出大胆无礼的样子来。
“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是您的事,我一定不说。”
“那么你马上就不要在这里干事了。”
“好极了,爵爷。如果我必须走的话我就一定走。”
“你是很不体面地离开的。天哪!你真该知些羞耻啊!你家的人和我家的人在这所房子里同居共处有一百年之久了,而现在我竟会发现你在处心积虑地搞什么阴谋来害我。”
“不,不,爵爷,不是害您呀!”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白瑞摩太太正站在门口,脸色比她丈夫更加苍白,样子也更加惶恐。如果不是她脸上惊恐的表情的话,她那穿着裙子、披着披肩的庞大身躯也许会显得可笑了呢。
“咱们一定得走。伊莉萨。事情算是到了头了。去把咱们的东西收拾一下吧。”管家说道。
“喔,约翰哪!约翰!是我把你连累到这种地步的,这都是我干的,亨利爵士——全是我的事。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且是因为我请求了他,他才那样做的。”
“那么,就说出来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那不幸的弟弟正在沼地里挨饿呢,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的门口饿死。这灯光就是告诉他食物已准备好了的信号,而他那边的灯光则是表明送饭地点的。”
“那么说,您的弟弟就是……”
“就是那个逃犯,爵爷——那个罪犯塞尔丹。”
“这是实情,爵爷。”白瑞摩说道,“我说过,那不是我个人的秘密,而且我也不能告诉您。可是,现在您已经听到了,您会明白的,即使有个阴谋,也不是害您的。”
这就是对于深夜潜行和窗前灯光的解释。亨利爵士和我都惊异地盯着那个女人。难道这是可能的吗?这位顽强而可敬的女人竟会和那全国最最声名狼藉的罪犯同出一母?
“是的,爵爷,我就姓塞尔丹,他就是我的弟弟。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把他纵容过度了,不管什么事情都是随着他的意思,弄得他认为世界就是为了使他快乐才存在的,因此他就应该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欲为。他长大以后,又碰上了坏朋友,于是他就变坏了,一直搞到使我母亲为之心碎,并且玷污了我们家的名声。由于一再地犯罪,他就愈陷愈深,终于弄到了若不是上帝仁慈的话,他就会被送上断头台的地步。可是对我说来,爵爷,他永远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曾经抚育过和共同嬉戏过的那个一头卷发的孩子。他之所以敢于逃出监狱来,爵爷,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住,而且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以帮助。有一天夜晚,他拖着疲倦而饥饿的身体到了这里,狱卒在后面穷追不舍,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就把他领了进来,给他饭吃,照顾着他。后来,爵爷,您就来了,我弟弟认为在风声过去以前,他到沼地里去比在哪里都更安全些,因此他就到那里去藏起来了。在每隔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在窗前放一个灯火,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里,如果有回答信号的话,我丈夫就给他送去一些面包和肉。我们每天都希望着他快走,可是只要是他还在那里,我们就不能置而不顾。这就是全部的实情,我是个诚实的基督徒,您能看得出来,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罪过的话,都不能怨我丈夫,而应该怪我,因为他是为我才干那些事的。”
那女人的话听着十分诚恳,话的本身就能证明这都是实情。
“这都是真的吗?白瑞摩?”
“是的,亨利爵士。完全是真实的。”
“好吧,我不能怪你帮了你太太的忙。把我刚才说过的话都忘掉吧。你们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关于这件事,咱们明早再谈吧。”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又向窗外望去。
亨利爵士把窗户打开,夜间的寒风吹着我们的脸。在漆黑的远处,那黄色的小小光点依旧在亮着。
“我真奇怪他怎么敢这么干呢?”亨利爵士说道。
“也许他放出光亮的地方只能由这里看到。”
“很可能,您认为距这里有多远?”
“我看是在裂口山那边。”
“不过一二英里远。”
“恐怕还没有那么远呢。”
“嗯,白瑞摩送饭去的地方不可能很远,而那个坏蛋正在蜡烛旁边等着呢。天哪,华生,我真想去抓那个人去。”
在我的脑子里也产生过同样的想法,看样子白瑞摩夫妇不见得信任我们,他们的秘密是被迫暴露出来的。那个人对社会说来是个危险,是个十足的恶棍,对他既不应该可怜,也不应该原谅。如果我们借这机会把他送回使他不能再为害于人的地方去的话,那我们也只不过是尽了我们应尽的责任罢了。就他这样残暴、凶狠的天性来说,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的话,别人可能就要付出代价呢。譬如说吧,随便哪天夜晚,我们的邻居斯台普吞都可能受到他的袭击,也许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才使得亨利爵士要去冒这样的险呢。
“我也去。”我说道。
“那么您就把左轮手枪带着,穿上高筒皮鞋。我们愈早出发愈好,那家伙可能会吹灭蜡烛跑掉的。”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出了门,开始远征了,我们在秋风低吟和落叶沙沙声中匆忙地穿过了黑暗的灌木丛。夜晚的空气里带着浓厚的潮湿和腐朽的气味。月亮不时地由云隙里探头下望,云朵在空中奔驰而过。我们刚刚走到沼地上的时候,就开始下起细雨来了。那烛光却仍旧在前面稳定地照耀着。
“您带了武器吗?”我问道。
“我有一条猎鞭。”
“咱们必须很快地向他冲过去,因为据说他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咱们得出其不意地抓住他,在他能够进行抵抗之前就得让他就范。”
“我说,华生,”准男爵说道,“这样干法福尔摩斯会有什么意见呢?在这样的黑夜、罪恶嚣张的时候。”
就象回答他的话似的,广大而阴惨的沼地里忽然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吼声,就是我在大格林盆泥潭边缘上曾经听见过的那样。声音乘风穿过了黑暗的夜空,先是一声长而深沉的低鸣,然后是一阵高声的怒吼,再又是一声凄惨的呻吟,然后就消失了。声音一阵阵地发了出来,刺耳、狂野而又吓人,整个空间都为之悸动起来。准男爵抓住了我的袖子,他的脸在黑暗中变得惨白。
“我的上帝啊,那是什么呀,华生?”
“我不知道。那是来自沼地的声音,我曾经听见过一次。”
声音已经没有了,死一样的沉寂紧紧地包围了我们。我们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了。
“华生,”准男爵说道,“这是猎狗的叫声。”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因为他的话里时有停顿,说明他已突然地产生了恐惧。
“他们把这声音叫什么呢?”他问道。
“谁呀?”
“乡下人啊!”
“啊,他们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您何必管他们把那声音叫什么呢!”
“告诉我,华生,他们怎么说的?”我犹豫了一下,可是没法逃避这问题。
“他们说那就是巴斯克维尔猎狗的叫声。”
他咕哝了一阵以后,又沉默了一会儿。
“是一只猎狗,”他终于又说话了,”可是那声音好象是从几里地以外传来的,我想大概是那边。”
“很难说是从哪边传来的。”
“声音随着风势而变得忽高忽低。那边不就是大格林盆那个方向吗?”
“嗯,正是。”
“啊,是在那边。喂,华生,您不认为那是猎狗的叫声吗?
我又不是小孩,您不用怕,尽管说实话好了。”
“我上次听到的时候,正和斯台普吞在一起。他说那可能是一种怪鸟的叫声。”
“不对,不对,那是猎狗。我的上帝呀,难道这些故事会有几分真实吗?您不会相信这些吧,您会吗,华生?”
“不,我决不相信。”
“这件事在伦敦可以当作笑料,但是在这里,站在漆黑的沼地里,听着象这样的叫声,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伯父死后,在他躺着的地方,旁边有猎狗的足迹,这些都凑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华生,可是那种声音简直把我浑身的血都要凝住了。您摸摸我的手!”
他的手冰凉得象一块石头。
“您明天就会好的。”
“我想我已无法不使那种叫声深印在我的脑中了。您认为咱们现在应当怎么办呢?”
“咱们回去好吗?”
“不,决不,咱们是出来捉人的,一定得干下去。咱们是搜寻罪犯,可是说不定正有一只魔鬼似的猎狗在追踪着咱们呢。来吧!就是把所有洞穴里的妖魔都放到沼地里来,咱们也要坚持到底。”*
我们在暗中跌跌撞撞地缓缓前进着,黑暗而参差不齐的山影环绕着我们,那黄色的光点依然在前面稳定地亮着。在漆黑的夜晚,再没有比一盏灯光的距离更能骗人了,有时那亮光好象是远在地平线上,而有时又似乎是离我们只有几码远。可是我们终于看出它是放在什么地方了,这时我们才知道确已距离很近了。一支流着蜡油的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