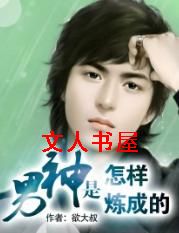剪刀男-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在这次的功劳上,就准你抽烟吧。”村木笑笑:“又出现了目击者吗,不错不错。”
村木再次出神地望着照片。
矶部心想,他在看什么照片呢?若是日高的照片,不可能需要拿着好几张比对。
或许是注意到了矶部的视线,村木朝他转过脸:“你在意这个?”
“是啊,那是什么?”
“很有趣的照片,我从鉴识课那里要来的,你也来看看。”
村木向矶部招招手,矶部拖过村木旁边的椅子坐下。
“喏,你看。”村木递过来一张染有血迹的剪刀照片,那是鉴识人员拍摄的凶器照片。
“还有一张,这张。”村木给他看的仍是一张剪刀照片,这把剪刀上沾着灰土,是矶部找到的另一把剪刀的照片。
“你觉得怎样?”村木问。
“是两张剪刀照片。”矶部不明所以地回答。
“没错。”村木从矶部手中拿回照片,两手各持一张:“这张是凶器剪刀的照片,这张是你在树林里发现的剪刀的照片。”
矶部弄不懂村木的意图。
“问题来了。”村木再次把两张照片递给矶部:“这两把剪刀究竟有什么不同?”
矶部仔细对比着两张照片。照片中的两把剪刀由同一厂商制造,品种相同,从外观上看完全是同样的剪刀。
“答案是?”
“凶器剪刀上染有血迹。”
“那还用说。”村木似乎有些失望。“你讲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文)“制造编号不同吗?”
(人)“大批量生产的文具怎么可能刻有制造编号。”村木笑了:“我天天跑文具店,说的肯定没错,你就信我的好了。”
(书)“那我就想不出别的区别了,这是两把同样的剪刀。”
(屋)“是啊,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仔细查看这张照片时,我发现了足以推翻这一看法的事实。”
村木拉过椅子,朝矶部探出身来,指着手上照片的剪刀尖端:“你看,剪刀的尖端磨尖了吧?”
“因为剪刀男刺第一个被害者时大费周折,之后便用锉刀之类将剪刀磨尖。”矶部记起了堀之内的话。“可是,两把剪刀都磨尖了啊。”
“的确两把剪刀都磨尖了,但是有微妙的区别。你瞧,颜色略有不同吧?”
矶部凝目注视村木指示的剪刀尖端。感觉上颜色确实有少许差异,那差异十分微妙,令人以为可能是眼睛的错觉。
“会不会只是鉴识人员拍照时光线的影响造成的?”矶部抬起头说。
“有可能。所以我让鉴识课给我送来剪刀尖端的特写。”
村木从桌上拿起另外两张照片。
“这一来就能清楚发现区别了。首先是这张。”村木递给矶部一张照片:“你看看,真厉害啊,磨得跟锥尖似的,精光发亮。喏……”
诚如村木所言,放大的剪刀尖端不仅锋利尖锐,而且表面十分光滑,毫无毛糙之处。
“不锈钢剪刀要磨到这么锋利光滑,得耗上多少时间啊?”村木喃喃低语。
想像着日高握着锉刀一点一点把剪刀尖端磨尖的情景,矶部有点毛骨悚然。
“另一方面,这把剪刀又是怎样?”村木递给矶部另一张照片。
“乍一看是同样磨尖了,干得相当不错,但并不完美。你看,”村木指着照片:“不光滑吧?”
没错,这把剪刀的尖端不够平整,留有锉刀的痕迹,好似刀削的铅笔尖一样。尖端的尖锐程度也不均一,稍有些弯曲。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村木问。 棒槌学堂·出品
矶部默然摇头。其实他对村木想说的事明白了一半,但那种事太岂有此理了,他开不出口回答。
“我还从鉴识课那里要来了在江户川发现的第二名牺牲者脖子上插的剪刀照片。”
村木伸手拿起桌上剩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张。就像你看到的,剪刀的尖端和这张照片里的剪刀一样,磨得很光滑,简直偏执狂才干得出来。”
村木顿住话头,盯着矶部:“你懂了吧?”
“两把剪刀是不同的人磨尖的。”矶部终于说出了回答。“可是,怎么会……”
“答得好。”村木无视矶部的困惑,两手举起两张剪刀尖端的放大照片,继续往下说。
“这张是剪刀男磨尖的剪刀。但这张不是,是某个模仿剪刀男的人磨尖的。那家伙竭尽全力想模仿剪刀男,但他的耐性不够。也难怪他,就算是我,要是别人叫我把不锈钢剪刀磨尖到这个程度,我恐怕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地提高嗓门。”
“请等一下。这么说来,日高不是真正的剪刀男吗?”
矶部一边极力反复思索,一边喘着气说道。
“日高企图模仿剪刀男,带着自己磨尖的剪刀走在路上时,偶然发现了真正的剪刀男杀害的死者,因此他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怀疑,把携带的剪刀抛到了树林里。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不可能发生这么偶然的……”
“我的设想是更加意想不到的偶然。”村木眼里闪着光芒。“你把两把剪刀弄反了。听着,插在被害者喉咙上的是这把,某个模仿剪刀男的人磨尖的剪刀。而你在树林里发现的,是真正的剪刀男的剪刀。”
“你说什么?”矶部禁不住大叫:“怎么可能!”
第二十一节
周六下午打工回来后,我决定用窗帘轨道上吊自杀。
令我疲倦的并非工作,冰室川出版社还没有进入忧郁期,我只是照佐佐塚的吩咐做些杂事而已。
我的疲劳感更多的来自精神上。自从昨天和敏惠谈过话,我自己的心情似乎也陷入了忧郁状态。
我打开阳台的窗户,爬上铝制窗框,背靠着窗框,一边保持平衡,一边用运动毛巾把脖子系在窗帘轨道上,然后两手抓着窗框,慢慢把自己往地板上放。
我的双脚挨着了地面。
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脖子缠着毛巾站在地板上,这个样子岂非很怪?连上吊自杀也不能如愿吗?
有白色的东西从灰色的天空飞舞而下。
为什么我还能看到天空?
醒过来时,我仰面倒在阳台上,呼吸急促,心跳快得叫人害怕,后背和屁股都很痛。
为什么我会倒在阳台上?
我勉力抬起头,望向依然敞开的窗户。窗帘轨道已经从当中折断,无力地卷曲着,白色的运动毛巾自一边耷拉下来。
看来,尽管我两脚挨着了地面,但因为颈动脉被勒住,还是丧失了意识。要不是窗帘轨道承受不住我的体重,我大概就能顺利死掉了。
然而窗帘轨道在重压下折断,我从窗户往后倒在阳台上,后背和屁股想必都已青紫。仰面摔在混凝土地面上,头盖骨却没撞伤,简直不可思议。
胖子连上吊自杀都做不到吗,我不禁悲从中来。
从空中飘落的白色东西,原来是东京的初雪。我闭上双眼,任由雪落在我的脸上。
“据说上吊自杀的人,耳边会听到美妙得无可比拟的天国音乐。”医师从桌前回过头,笑嘻嘻地说。
“会听到什么呢?譬如,山下达郎的《平安夜》?”
“哪有,我什么也没听到。” 棒槌学堂·出品
“还是海滩男孩的《Little Saint Nick》?保罗·麦卡特尼的《Wonderful Chrisstmas Eve》?”
“干嘛老扯些圣诞歌?”我不耐烦地说。
“因为快到圣诞了。是我的话,会向天国的电台点播three wise man【注1】的《Thanks For Christmas》。那首歌似乎能令人安详升天。天使清楚地看到地狱,弹着竖琴,精神百倍。说不定天使们也随着曲子在唱片针上翩翩起舞。”
Thanks for Christmas
Thank you for the love and happiness
It's snowing down
All around
Thanks for Christmas
Thank you for the winter's friendliness
It's snowing down
All around the world
“没错,正如气象预报员所言,整个东京都在下雪。”
医师摆出做作的姿势,宛如朗读一般开始长篇大论。
“雪飘落在剪刀男躺卧的阳台上,飘落在奔走调查的可怜刑警身上,飘落在还未能摆脱悲伤的被害者家人居住的沙漠碑文谷屋顶上,飘落在私立叶樱学园高中白杨树阴下的红砖道上,飘落在学艺大学车站前的咖啡馆奥弗兰多的窗户上,也飘落在无人的鹰番西公园,今天依然在肃穆举行某人葬礼的春藤斋场,还有不知位于何方的樽宫由纪子长眠的墓地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模仿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们》。”
我都因为上吊昏过去了,还得洗耳恭听医师那无聊的引用么?我不禁叹气。
“那是因为你吊在窗帘轨道那种容易折断的东西上。”医师扬声笑起来。“下次你要上吊,最好选择更结实的东西,像叶樱高中的林荫道就合适得很。也就是说,像奇妙的果实从白杨树干上吊垂下来。”
我连问他在说什么的力气都没了。
“或者路灯也可以。你知道吗?据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民众就是利用小巷的路灯将贵族处以绞刑。Sizou omu,a ra ranterune!”
“什么意思?”
“法语的‘把剪刀男吊到路灯上!’。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可是民众的头号敌人,给吊到鹰番西公园的路灯上也是难免的事。不过法国大革命时的路灯似乎是从墙上探出的煤气灯,现代日本那种类似豆芽形状的水银灯,没有合适地方挂私刑用的绳索。”
医师用圆珠笔尖搔着太阳穴:“我眼前浮现出你被逮捕时的情景。相机的闪光,电视台用的强烈灯光,记者的叫喊声。你被表情凝重的刑警带上警车,戴着手铐,脸上打了马赛克。你是在后座上垂头丧气,还是昂然挺胸,大无畏地望着前方?”
医师似乎沉浸在那无聊的空想中。我本来就很郁闷,还得听这种扯谈的话,真受不了。
“记者朝这个房间、冰室川出版社和你父母家涌来。为了证明你是何等异常的人物,何等危险的怪物,广泛搜集一切证言和情报。楼下的居民大概会说,这么说来,这人丢不可燃垃圾的方式确实很反常。冈岛部长大概会皱着眉头说,我觉得一个人不想成为正式社员很可疑。佐佐塚会说什么话呢?父亲大概是表情沉痛地默默不语吧。”
“我没有父亲。”
“哦呀,是吗。那自称的父亲也行。学生时代的朋友大概是脸上打着马赛克,口若悬河地回忆你的种种奇异事迹。你要说没有朋友,那我就改成自称的朋友吧。什么你是个与别人相处不融洽的孩子啦,中学时代说过很奇怪的话啦,高中的毕业文集里写过怪异的话啦,形形色色的证言满天飞。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你小时候的照片能卖多少钱一张?大概能给同学赚包烟钱吧。”
医师张开双手,仰首望天。
“心理学者和犯罪学者,前刑警和前检察官,纪实文学作家和推理小说作家,全都以评论员的身份聚在一起对你进行解剖。也就是说,由于如此这般的童年经历和心灵创伤,你精神构造里的螺丝弯曲了、歪斜了,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障碍,召来了危险之极的怪物。剪刀男就是这样产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幼儿时期养育方法存在问题。社会上的母亲们只怕会因为太过恐怖,陷入育儿神经过敏。”
医师比平时更加饶舌。为什么呢,我暗自诧异。
“为什么变得这么喋喋不休?当然是因为恐惧了,对遭到逮捕的恐惧。”医师回答。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恐惧?你不可能感到恐惧吧。”
“你这样想吗?”医师静静地回答,不知为何,口气很认真。
“是啊,你多半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你无法理解恐怖为何物。”
医师摘下圆圆的黑眼镜,用白衣的下摆擦拭镜片。
“你是理解不了的吧,恐怖也好,悔恨也好,罪恶感也好。”
黑色眼镜下现出的双瞳带着平静的光芒注视着我。
“樽宫健三郎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能杀人。你想到了一个实在很绝的比喻:没割包皮的小学生。的确如此。你又回答说,‘想杀人的话就去杀好了’。这也正如你所言。理论上就是这样。可是,实践中却办不到。”
医师微微侧着头,闭上了眼睛。
“人之所以禁忌杀人,只是因为些微小事。亲眼看到死亡时的不快感,闻到鲜血味道时的恶心感,碰触到尸体时的毛骨悚然,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与冠冕堂皇的伦理道德毫无关系。那种某种行为乃属禁止的观念,反而导致了人们在轻易违反时倒错的喜悦。正因为违反了禁忌才乐在其中,正因为超出了常轨才倍感欢欣,由于疯狂而深信自己是比别人特别的存在,像这种脑筋不好的家伙多不胜数。”
医师的声音微带怒意。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在于更微妙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杀人?因为看到人死去会不愉快。跟伦理道德没有关系,跟善良、友爱、同情、共鸣也统统没关系,单纯的不快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