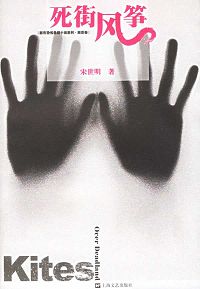日落断魂街-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不是一天之内跪了两次?
☆、套娃和骨灰
降体温的方法有很多。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可将病人泡进冰水里,可将病人绑在电风扇前吹一个小时,也可以用十床大被子把病人压得不得翻身;从化学的角度讲,可以吃药。周轨被贾成舟诚心诚意花样百出地折腾了一番,病情加重,重得几乎能看见载他西去的仙鹤。
心寒周身凉。周轨的病最后还是好了,虽然方法并不得当。贾成舟从吧台上拿了四瓶刚刚添置的上等白兰地,一溜烟窜到周轨床前,打开洗手间大门,正好让马桶对着周轨。他拔开瓶塞,把酒咚咚地倒进马桶里,倒完后回眸一瞧。周轨原本烧得通红的脸这下子煞白,他一只手捂着胸口,在一山的被子中打了几十个颤抖,眼一翻,栽进了被子里。第二天清晨,不但高烧消退,连手脚都是冰凉的。
贾成舟在周轨的卧室里闲逛着,病老板正趴在床头一口口吃着糖煮蛋。周轨嗜甜,嗜烟,和法医无异。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就是不肯下床。人都是有惰性的,变态也是人。
周轨的卧室很宽敞,阴冷。屋里的暖气开到了五档,还是没用。贾成舟咧着嘴微拱着肩,周轨坐在一堆白花花的被子里,像云端上刚减了肥的佛祖。
床对面是个巨大的胡桃木书架,书不多,倒是排放了好几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靛蓝色,描绘得颇精致,脑袋上有一圈用来开合的拼痕。贾成舟拿起一个掂了掂,里面装满了东西,有些沉。扭开一看,原来通共只有一层,里头装了许多黑色粉末。他觉得怪异,嗅了嗅,也没什么味道,于是问道:“这是什么?”
周轨光顾着喝糖水,只抬眼一掠,口齿不清地说:“这个呀,是我爸的骨灰。”
贾成舟手都抖了。“你再说一遍?”
周轨放下碗,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书架上其他几个看见没?从左往右是我爷爷,爷爷的爸爸,然后。。。。。哎,爷爷的爷爷去年被我弄丢了。总而言之,你手上是我爸。”
贾成舟几乎把套娃投回了书架,眼珠瞪得比眼眶大。“你死了以后?”
周轨有点惆怅:“颜色还没挑好呢。”
“你们家都不入土么?”
周扒皮五世耸了耸肩:“死了还要和乱七八糟的邻居打交道争地盘,做鬼也不安生。”
贾成舟哼了声:“怪不得你房间阴冷阴冷的。”
周轨唉声叹气:“对呀,你说我一个男人阳气好像也不够。这房间再多个男人就好了。”
贾成舟手往桌面上撑了把,手掌上沙沙的,抬起手一看,原来是洒出来的骨灰。他好像忘记哪个瓶子是周轨老爹,于是随手拿了一瓶,扭开套娃脑袋,一攒攒往里装。“你可以贴个广告找个伴?”
周轨撇了撇嘴巴:“出租卧室?你当我有毛病啊。对了,你把我爹放我爷爷身上干什么?”
贾成舟窘迫地翻着套娃里的黑色粉末。“那该怎么办?不过你爸的颜色比你爷爷深一点。要不我把他挑出来?这个好难办。。。。”
“算了,反正他们关系不错。”周轨摆了摆手。“其实出租房间也不难,你不就是个大活人么?”
“我不是有个房间了?再说这里才一张床。”
周轨有点着急:“你不是写过黄书卖过碟片吗?”
贾成舟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对呀,有什么关联吗?”
“对呀,通常情况下,一人对另一个人这么说,然后——”周轨摊开手做了个“你应该明白”的手势,看贾成舟依然没有反应,只好叹了口气。“我有点冷啊,你再去拿床被子。”
贾成舟抓了抓头发,悻悻地出了房门,一路走到一间总统大床房内。所谓的总统大床房和普通大床房没什么区别,除了多两包茶包和咖啡。他一边嘀咕着酒店真小气,一边把被子折叠在一起。搬动到一半才看见被单上有东西。他把那一角翻起来一看,上面是用黄线刺绣出来的两个字。“总统”。
贾成舟抱着一大捧被子回到卧室,在床上翻了半天才找到他的老板,周轨几乎被床上用品吞没了。贾成舟犹豫片刻,又盖上一层被子,把他完全埋了进去。
酒店处于休业状态,老板不喜欢点灯,因此店里是幽暗的。贾成舟靠在吧台边上点了支烟。烟卷受了潮,丧失了劲头。他吞吐了两口就将它碾死。店门响了两下,他看了过去。店门上挂着招贴画,只能现出来人的两条腿。那人穿着牛仔裤和帆布鞋,是个男人。
门又被敲了两下。贾成舟从吧台后面走出去,拔下插销,开了门。
是杭潮生。
十二月份的拉城冷得让人找不着北,杭潮生只在T恤外面罩了件薄呢大衣。他的胡子在脸上扩张着,青皮灰须在寒冬总比白底一片要好。
两人隔了扇门,一个在风口外,一个在风口中,因此贾成舟的头发服帖地趴在脑袋上,杭潮生的脑袋则像一朵迎风的蒲公英。他跺了跺脚说:“你不让我进去?”贾成舟才恍然大悟地往屋里退了两步。
杭潮生进了酒店,上上下下打量着屋里的装修。“你的朋友呢?”
贾成舟看了眼萧瑟的街道,关上了门。“病了。”
“所以这里就你一个人喽?”
贾成舟又抓起吧台上的烟盒,抖了抖,里面的烟全是软的。“你身上有烟吗?” 杭潮生停止了踱步,从口袋里拿出包红万,一盒火柴。两人嘴里各衔一支,擦了火柴点上。
“应该我来找你的。”杭潮生的人死了不少,贾成舟脸上下不来。
杭潮生往天花板上吐了口烟。“你有这个胆么。”
“警察是你叫的?”
“唔。”
“你认识局长?”
“打过几次交道,人不错,特别喜欢他的糊涂。”
贾成舟伏在桌子上,表情复杂。“你手下的人死了不少,你还帮我?”
杭潮生嗤地笑了:“我帮人只帮一次,但总归要帮到底。我手头的人么,老的不死新的不来。”
贾成舟嘴巴里苦了下,忽然害怕起来。杭潮生又开始来回踱步。“来你店里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同你说,我就只能帮你一次。下次找别人去吧。”他抬起头看着贾成舟,眼神里终究是透着怜悯和轻视。
贾成舟脸皮薄而不破,吐了口烟说:“多谢。只是我这点出息也没办法回报什么。”
☆、肃杀
李约暂时还没来找他们的麻烦,这个暂时大约有一周多。周轨的毛病好了,酒店重新开始营业。贾成舟终日里闷闷的,债务和人命就像学生时代的成绩,黑沉沉压在头顶上,让你总是忍不住抬头去看。
时间过得飞快,日历上又多了几行红圈,再过一个月贾成舟就可以滚蛋了。马克笔的墨水快干了,周轨画了好几回才在新的一天上勾出一个圈。他闻着笔尖油腻的味道,看见贾成舟辗转于餐桌之间收拾着一天的残局。这人就是脑袋瓜转的太慢,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话他是听不懂的。
周老板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思考,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说,他的员工怎么那么笨,比如说,怎么把爱偷吃甜食的警长给赶跑。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考虑半夜的狩猎场所。他没有资本在光天化日下喋血,只能躲在阴暗的地方,瞄准猎物,将其拖进一个不见光的角落撕个粉碎,连骨带血一扫而光。他的狩猎技术不比他老爹,只能挑最笨的猎物。
冰窖里空落了许久,张飞的气息也没有了。周轨又在准备迷药和刀具了。贾成舟问他,你就非得用人肉吗?周轨吭哧吭哧磨着把军刀,懒得理他。他最近见了贾成舟就厌烦。厌烦的情绪有时候来得莫名其妙,周轨从来选择乖乖接受。
贾成舟没有放弃,问他,你就不能用猪肉,牛肉或者鸡肉吗?什么肉就好,为什么非得杀人呢?周轨冷笑两声:“我要是不用人肉,张飞是怎么死的?别得了便宜还充好人。”贾成舟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厨房。
周轨知道他一直有些怕他。他的心绪很乱。贾成舟是不会喜欢上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的,确切点说,自己这样阴晴不定的家伙从来都不讨喜,可他又没办法做出改变,你有见过一个善良爽朗的侩子手吗?
凌晨十二点一刻,他从酒店后门走了出去。
狭窄的街道上漆黑一片,偶尔有两盏伶仃的路灯,半张脸埋在蜘蛛网里,苟延残喘地闪着光。周轨的前面走着一个男人,瘦的有些畸形,比他更瘦的影子耷拉在地上,被周轨的脚尖踩踏。男人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他只是有些飞高了,欣慰飘然地走着,像一个孤独梦游的鬼魂。
男人刚从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翻墙出来,靠在墙壁烤着锡箔纸上的白色粉末,享受完毕后便成了准受害者。
周轨冲他打了个招呼,男人打着晃转了个身。周轨吃吃笑着:“给我也来一点?”
男人转过身的时候打着摆,嘴上还不忘骂脏。狗杂种,滚一边去。
周轨加快了步伐赶了上去。男人抡起虚弱的拳头,还没冲到周轨的脸上,口鼻就被蒙住,两秒钟后软了下去。周轨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麻绳,套住他的脖子,一脚蹬在男人的背上,把绳子的两端往后猛扯。粗糙的绳索吃进男人的脖颈,男人开始挣扎,两手无助地划着空气,半条舌头探出了嘴唇。侩子手下手狠绝,受害者连倒气的声响都发不出来。
半分钟后,男人死了。周轨拖着一具嶙峋的死尸走在小路上,这里离旮旯酒店有些远,周轨身体并不健壮,还没从大病中完全恢复,半夜的风猫爪似的蹭在脸上,他出着虚汗。
他原路返回,又经过了那个停车场。停车场被封起来了,政府要重建成办公楼。周轨手臂发酸,速度减慢,半天才勉强把死去的男人从停车场一边拖到另一边。黑幕中有风声,他的轻微喘息,还有死者僵硬的下肢擦滑地面的声音。又有声音混了进来,声音来自于停车场外的墙头。周轨把尸体拖进一个角落,伸着脑袋看过去。墙头上蹿下两个男人,口袋里鼓鼓囊囊。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东西,像死去的男人,饥渴无比地点燃,嗅着。
第二天早上贾成舟起晚了,他赶到餐厅,里面空无一人。周轨躺在吧台上,对着天花板吞云吐雾,他的脑袋边上放了一攒包装纸,里面还沾着布朗尼的碎末子。
贾成舟问他:“今天不开门?”
周轨头往后仰,贾成舟倒立在他的视野中。他把一只手挂下桌台。“你打算怎么还债?”
“不知道。”
周轨翻身起来,跳下吧台。“办法还是有的,关键是你还要不要这条胳膊。”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周轨挑拣着词汇。“贩毒的经验?”
小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的父亲去买报纸了,座椅的另一边是空的。有人做了下来,吸了两下鼻子,把头转向了小东西。“你的大人呢?”
那人很高,小葱扬起脑袋看了上去。男人的胡须和头发有些泛白了,可精神面容上却并不显老。小葱拿手指了指椅背后。男人回头看了下,给他一个大大的笑。“这么冷的天,你爸给你穿那么点?”
小葱拉了把他的袖子:“你比我穿得少!”
男人笑了笑:“因为我比你大。”
对面的长椅刚刚上了漆,一个胖子蹒跚着走到那里坐了下去。小葱抖着肩膀,咯咯地笑了出来。尖尖的孩童音。男人嘘了声:“别笑那么大声!”
胖子早就听到了,满脸狐疑地站了起来。他的白色羽绒服上绿幽幽地染了一大片,屁股上也全是。胖子蹒跚着走到他们跟前,像只愤怒的火鸡,呱呱地对男人叫着:“混蛋!管好你的小鬼,没教养的小杂种。”
男人挠了两下小葱的脑袋瓜。“你说的是。”胖子转过身骂骂咧咧地往回走,不时转过头瞪他们。小葱用两根食指把脸皮向下拉,冲他扮着鬼脸。他指着胖子的屁股,笑成一团:“快看!他屁股上那块像不像胖大象?”
胖子又走了回来,几乎大吼大叫起来:“死小鬼,你他妈的在说什么?”
男人冲他打着哈哈:“跟孩子计较什么呀,再不回去洗就结住了,屁股上沾着个大象到处走可不大好。”
胖子抡起了圆滚滚的拳头挥向了男人,被男人抓了个正着。小葱咯咯地笑着,跳下了椅子。他忽然停止了笑,对一个方向叫;“爸爸!他要揍我!”
胖子和男人停止争持,胖子面泛窘色,骂了两句离开了。唐晋北拍了两下小葱的头顶,呵斥了句:“又不听话。”眼神却对上了杭潮生。
小葱抢先说:“这个爷爷可好玩了。”
唐晋北有点不好意思。“叫叔叔,怎么能叫爷爷呢!”
“他的头发是白的,白头发的不是得叫爷爷吗?”
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