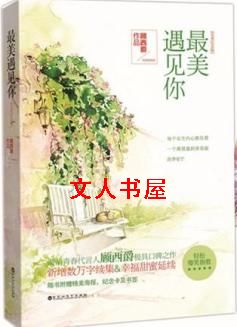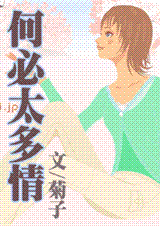醉死当涂(完整精修版)-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对我一本正经的回答,黎翘居然笑了,笑得艳光四射,白牙尽露,令人眼晕不已。
笑足了之后,他说,第十七届青舞赛的冠军名叫杨滟,我跟她认识了很多年。
“脚踏实地活着的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可悲,反倒是你这样的人——”意味深长的一个停顿之后,黎翘取出墨镜重新戴上,抬手拍了拍我的雪佛兰,“好好开你的车吧,袁骆冰。”
这个男人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可我分明看见了他墨镜后的眼神,轻蔑夹杂厌恶,如同俯首鞋底一撮泥。
离开前黎翘彬彬有礼地与我爸打招呼,叫了他一声“叔”,还嘱咐他当心身体。
五、押沙龙,押沙龙(下)
我住的地方紧挨火葬场,换房子的时候一点没考虑吉不吉利,只贪图便宜,又信了中介的鬼话,说这儿其实“闹中取静”。
初来乍到的我每逢出殡便要难受,闹丧的锣鼓砉然响然,哭丧的人比锣鼓还能闹。
时间长了才明白,“闹与静”无关“孝与逆”,闹的未必伤心,静的未必不孝,多少子欲养而亲不待,最后都变成了几家坟上子孙来。
于是我跟老袁说,你活着的时候我待你好点,你死的时候我就不哭了。
夜里扪了们心口,觉得尚对得住它,自此日子照过,心如止水。
小区没车位,我不得不花了点钱打点了附近小区的物业,好处是不必担心乱停车被贴条,坏处就是停车以后还得步行二十分钟。
连天的雨总算消停了,在天黑透之前,我扶着老袁穿过一条极窄的巷,往家的方向走。
老袁大约也知道今儿这出闹得太离谱,偏着头,佝着背,与我一路无话。
上了年岁的老公房,设施不佳,遇上大雨排水沟就容易堵,小区门口这会儿已经积了水,像一片静水流深的湖。我目测水深漫过了小腿肚子,于是便卷起裤腿,脱了鞋,让老袁把鞋拿手里。我跟他说,牛皮的,可贵了,你得给我拿好了。
然后我就弓下腰,把这柴瘦柴瘦的老头儿背在了身上。
“人家都说子女是父母的讨债鬼,屁咧!上辈子一定是我欠了你了……”水比我想象得还深一点,煞浑煞冷,看不见的地方,还有酒瓶盖之类的东西隔着袜子直硌脚。
刚蹚过去,老袁就在我背上不安分地动了动,问我就这么走了,后来人呢?
这老东西的脑子时好时赖,这会儿就是好的时候。我跟他有点默契,点头说,那你坐边上等一会儿。
我来来回回好几次,找了砖头与木板,在出入小区的必经之路上,找准较浅的地方,给后人垫了一条不用脱鞋蹚水的小道。
既然背了就背回家吧,我又把我爸驮上后背。老东西看着嶙峋,实则若泰山压顶,沉得不得了。我庆幸自己练舞出身,腰细且柔韧,否则定要被他压折了。
沉默一会儿,老袁开口:“今天在超市里那人……挺好的。”
想也不想便晓得他说的是黎翘,点了点头:“是挺好的,车费给了两千呢。”
老袁以重音强调:“长得好。”
这是实话,我又点头:“嗯,活人里头是没比的了,神仙恐怕还能争一争。”
老袁突然打我,就拿我的皮鞋,还不是做样式,结结实实以鞋底板兜了我一个嘴巴子。
我无辜被打,立马如火蹿房梁般跳起来:“袁国超,你他妈再打我,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撂水里!”
转折太突然,哪想到老东西这会儿比我还生气:“你为什么不喜欢姑娘,尽注意跟你一样的爷们儿?你要不让我抱孙子,我就活阉了你!”
我知道老袁一直想掰正我的性取向,于是不客气地回嘴:“喜欢男人是我愿意的吗?隔代遗传懂不懂,你孙子要跟你一德行,人家上有老下有小是父慈子孝天伦之乐,我呢,手里提溜个小畜生,背上还驮着只老王八!”
老袁啪地又拿鞋兜我一个嘴巴子,火了:“我什么德行?!我德行再差也是你爸!”
“什么德行?在超市里尿一裤子的人可不是我——”险些气急败坏兜不住嘴,努力冷静下来,我问他,“哎,袁国超,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存心摸那女人?”
老袁病了之后一改往日的嚣张作风,在哪儿都低头自认孙子,独爱对我摆老子的谱。可他嘴皮子没我灵活,被我骂了以后久搭不上腔,半晌才来一句:不记得了。
我噗嗤笑了:“行啊,你个老流氓,不枉我今天跪到腿软——”
老袁又不说话,只悄悄搂我紧些。
“摸就摸了呗,你要真想女人了,改明儿我去街边给你找一个,找一个腿长奶大的,让你来一个老汉推车……”老东西骂我我常勇于回嘴,可他一认怂我鼻子就止不住地发酸,我故意开玩笑,跟老子安抚儿子似的说,“总有一天,你儿子会有大出息,以后你在外头膀胱胀了,就告诉别人你是袁骆冰他老子,所有人都得对你肃然起敬,脱裤子也不会被人扇耳光,想抖鸡巴抖鸡巴,想尿多远尿多远……”
小区里有不咋亮的路灯,我披着一脉微光,驮着我的老子,脚踏实地,一步步向前。
夜凉如水,濯洗城市尘霾,今晚的月亮特别皎洁。
回到家里,又擦又洗地把老袁安顿在厅里的沙发床上,我洗毕碗,刷完锅,把他尿湿的裤子泡进盆里,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娱乐新闻。
把桌椅推了推,在狭小空间里挪出一块地方。坐在电视机前,轻轻松松拉开一字马,就如同我刷牙的时候总会把腿掰过头顶。我虽然不怎么相信自己还能回到舞台上,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来年的汗与泪和血吞,总不舍得轻易荒疏。
其实平时我不太爱看这类新闻,今天不知怎么就格外留心了一下,果不其然,电视画面还没出现就听见了黎翘的名字。
单独一个专题,标题也是触目惊心——细数黎天王的七宗罪。
据说今天电视台本有一个为帮助脑瘫患儿的公益类节目,一众明星应邀出席,隆重亮相,唯独黎翘一身由头黑到脚的简装,还迟到了近一个小时。到场以后也不理记者提问,不与主持寒暄,从头到尾没给一声解释,只摆着一张“女人只要看着我就能高潮”的臭脸。
恰巧就是前两天,他刚刚惹上麻烦,把一个前来接机的女粉丝推了一个跟头。
向粉丝动手,那粉丝还是高中生。这事儿可太大了,媒体人口诛笔伐,可黎翘照旧我行我素,拒不道歉。
我想了想,黎翘今天迟到好像是因为我,虽然这人视我如鞋底泥,但一码归一码,我不信他推了那个女高中生,也不信他真如媒体所言那么混蛋。
看完娱乐新闻外出倒垃圾,正好遇上邻居丫头范小离练舞回来,她喊我一声:冰哥!
小丫头过年之后刚满十八,丹凤眼配瓜子脸,更手长腿长身板精瘦。老天赏了一口舞者的饭,范小离也在老娘皮那儿学舞多年,我猜老娘皮一定颇为中意这丫头的灵慧气质,而我看过她跳舞,确实也挺有灵性的。
范小离这阵子正在全力备战四个月后的第二十一届青舞赛,天天比打鸣的鸡起得早,比归巢的乌鸦回得晚,但她从不抱怨,她深信自己会在青舞赛上一舞成名,然后顺利转入娱乐圈;她深信自己不是鸡也不是乌鸦,就是一只等着青云直上的凤凰。
“比赛的时候跳哪一支舞决定了吗?”我不忍以我当年的境遇泼她冷水,她说什么是什么。
“雪璟老师希望我跳《醉死当涂》,可那舞实在太难了,我大概会在《践行柏柏尔》和《子夫诉》里选一支吧。”范小离把脸向我凑近,压低了声音说,“冰哥,透个秘密给你听,我在路上碰上星探啦,她邀我去做个节目,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可别在老娘皮面前说这个,她这人是舞痴,也寄望别人都是。她要知道你比赛前分心去录别的节目,铁定要撕你的脸。”
范小离吐了吐舌头,知道我不是吓她。
我突然叹气:“如果你能跳《醉死当涂》就好了,老娘皮的毕生心愿,就是这支舞蹈后继有人。”
范小离也叹气:“我是真的跳不好。我练过几百次了,可老跟东施效颦似的,仿不出那个神韵来。”
停了停,她说:“说到这个,雪璟老师今天又提起你了,她总跟我们说你是她教过的所有学生里,论舞蹈功底你当排第二(第一应当是另一个姓袁的),但论悟性、天赋,谁都差你一大截。她每次提到你眼眶都会发红,我看得出来她挺想你的。你为什么从来不回去看看她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再跳舞以后,我确实再没回去探望过老娘皮。我知道她对我有怨,她认为我不该作践自己的舞蹈天赋,她认为我应该极尽绚烂之后死在舞台上,而不是每天碌碌奔忙,活得像狗一样。
就在我放弃舞蹈的第三年,老娘皮曾经主动来找过我,她给我带来了西班牙皇家吉萨尔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闻名世界的艺术殿堂,孕育了多少令世人惊啧的舞蹈家,老娘皮托了不少关系才让那边愿意破格收我进去,甚至她还打算卖房子为我支付高昂的学费。
令人不可置信的好消息,可我不满意她不是先来找我,而是先去找了老袁。
老袁好面子,他不要嗟来之食,也不愿拖我后腿。他所能想出的唯一两全其美的解决法子就是去找老厂的厂长,据说他带了铺盖坐蹲守在厂长的家门口,堵着对方不让出门,他一边哭一边说他这一身的毛病是为领导挡酒挡出的工伤,厂里得负责他的养老送终问题,或者简而化之,给他一笔钱。
这个据说,是据民警说。
厂长被老袁哭烦了,放狗赶了几回也没赶跑,最终忍无可忍报了警。民警没责怪老袁,把他送回家时却责怪了我,说老人有病就好生照顾着,这是人之所以生而为人最基本的义务。
“我都两年没跳舞了,腿都劈不开了。你要真想帮我,别整这些弯弯绕的,直接给我钱吧。”我心里怨老娘皮施加无形压力于老袁,脸上还笑得特别轻松,“我正好想给我爸换进口药,顺便再给他添件皮大衣,老邻居请喝喜酒,得给老东西挣点面子。”
老娘皮当即骂我,为示我目光短浅,愚不可及,她甚至还举了个例子,说有报道政府为救灾饥荒送去了粮食的种籽,结果却被当地的农民煮熟吃光了。
“我这人就是稀泥巴糊不上墙,您老别为我瞎操心了,扯开裤裆放大屁的,多余。”我把心一横,拉开门就把老娘皮轰了出去。
此后几乎再没见过。最近一次见她还是半年前,当时我在一所中学门口摆摊卖烧腊饭。
“几多钱话你知啦,嗱,畀你。”
为显示自己的烧腊味道正宗,我时不时要冒出几句粤语来冒充背井离乡的广州仔——这招不赖,除了与城管打游击实在头疼,我的烧腊生意一直不错。正当我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跟一个买烧腊饭的女孩说话,突然感到不远处一束目光直直盯着我。
我抬起眼,看见站在街对面的老娘皮。
也归咎于天热,脸颊一阵烧,额头的汗突地滑了下来。手上满是油腥,我以肘弯擦了擦脸,可手还未放下,汗又下来了。
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老娘皮牵着一个学舞蹈的孩子,静静望着我,我看见夕阳在她脸上退逝,她的神情就像泣玉的卞和一般悲痛欲绝。
“哎,小广东,你的脸突然好红啊。”
“热到飚烟啦。”我把视线从老娘皮脸上挪开,埋低一张脸。
我被城管撵过无数回,冷嘲热讽没少挨;我跟别的小贩争占有利地形,斗完嘴皮挥拳头,从来不落下风。
可我唯独受不了老娘皮这样的眼神。
她毕生奉献于舞蹈,我曾是她与舞蹈的唯一血脉。
世人不识我为和氏璧,便是我自己也忘了,我好像生来就是一个横系腰包的小贩,每天回家数一数那些油腻腻的票子就很满足。
“我跟那人说了别剪短,结果他一刀下去剪了那么多,你看,这头多傻呀。”刚才叫我“小广东”的女孩是个熟客,她这会儿又苦着脸跟同伴说话,像是对新剪的发型不满意。
生意总是要做的,麻利地将黄瓜切段、烧肉切片,将米饭装盒,外套一只塑料袋。我重整旗鼓灿烂一笑,一个马屁拍得倍儿响亮:“你嘅头发剪得好靓,我都想同你去街啦!”
女孩被我夸得神清气爽,从我手里接过打包好的叉烧饭,笑说明天还来照顾我的生意。
待我忙过一阵再抬起头,老娘皮已经不见了。她站过的地方空无一人,只剩下黄昏过后死气沉沉的夜色。
六、做人好攰呀
范小离最终还是决定去参加那档选秀节目,固定的明星导师搭配每期各异的男神嘉宾,大腕云集,噱头十足,未播先火是必然的。
范小离能得到这次机会也不容易,初试、复试连着几轮,直至面见导演最后拍板,一路过关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