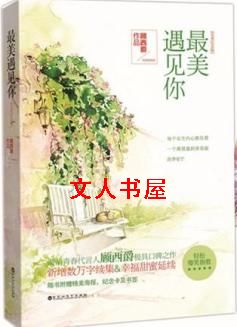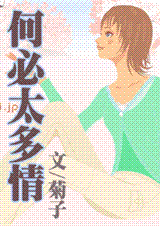醉死当涂(完整精修版)-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耽】《醉死当涂》作者: 薇诺拉
文案:
“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
但是,这篇文和李太白没有一毛钱关系。
如果一定要概括,应该就是一个“屌丝青年无下限调戏高岭之花并最终成功逆袭”的故事。
另外,这篇文和你期望看到的娱乐圈应该也没有一毛钱关系。
【暴力高冷明星攻】X【满嘴粗话小市民受】,现代背景,轻松白亮,八万字左右,HE。
……黎翘看着我,如同俯首鞋底一撮泥。
……而我同样看着他,却是看待心坎上的一颗痣。
内容标签:都市情缘 励志人生
搜索关键字:主角:袁骆冰,黎翘 ┃ 配角:顾遥,范小离,袁国超,王雪璟 ┃ 其它:HE,第一人称
………………………………………………………………………………………………
我们像车轱辘一样承载着不断向前的使命,挺着一管阳具,躁动着一颗心。
一、兵以诈立,你在扯屁
“人和畜牲差在哪儿?其实哪儿也不差,都是饥食渴饮,你死我亡——诶?你要不要来根烟?”
三月初,雾霾天,柏油地。
气温骤低于前些日子,这天儿多飘了一蓑牛毛雨,多吹了一口打头风,整座城市显得灰头土脸,眉目不清。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是个坐不住的客,四十岁不到的样子,市井细民的打扮,唧唧歪歪自来熟,上车之后时不时要把头凑过来跟我瞎聊。这会儿他递上一包玉溪,我从打开的烟盒里抽了一根,说了声,谢谢。
“学美术的在设计公司被操到死,学表演的最后都去坐了台,几十年改革开放没出几个真正的艺术家,为什么?因为这社会发展得太摧枯拉朽,人却还是那个熬不住饿的人,一餐不食就难受,三天不食立马英雄气短……”
“气短没关系,那话儿不能短。”我把烟叼嘴里,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
平时载客我不夹生,不拿劲,尤爱口无遮拦开黄腔,但今天没太大心思发挥。路线比我预计的要长,我心想就不该横穿整座城市送他去机场,车钱才给一百五,如果拉不到回程的客人,去了这趟远途的油钱,根本没挣头。
车是在车市上淘的二手,白色的雪佛兰景程,跑了7万多公里,但保养得还凑合。为它我磨蜕了几层嘴皮子,最后以三万不到的价格拿下,险些把原车主的嘴给气歪。
我驾照拿得早,几包中华就搞定了驾校师傅,但决定买车还是三个月前,一来是图出行方便,二来是想载客营运。
其实就是开黑车,我跑得不算勤,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入囊四五千。
目的地是市东国际机场,雪佛兰停在红灯前,再过两条街口,就该到了。
“就比如说你吧,你明知道开黑车犯法,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我吐出一口烟雾,漫不经心回答他:“不就是你刚才说的吗,我要吃饭啊。”
“一看你就没读过书,年轻人还是要多读读书,多一张证书多一块敲门砖,多一张文凭多一条谋生路……”
“我也想啊,从小就吃了没文化的苦——我日你妈!”
一辆红色的奇瑞突然从后头蹿上来,猛地打了个拐,要不是我反应快,他的车屁股一准擦烂我的车头。
又打一把方向盘回到道上,我把车窗摇下来,把头伸进雨里,冲那车连珠炮似的大骂:“你丫瞎撞什么?!撞死了没人管你儿子少教所管,没人养你老娘她得给你上坟,撞个半瘫不死你一勃起就得往外崩屎,你老婆湿着裤裆还得来敲我家房门!”
奇瑞上的人估摸不肯吃亏,当即摇下车窗骂回来:“你妈个傻逼!”
“哎对了,‘傻逼’就是说你妈。”逆风香百里,骂人更得迎头痛击,对方这一回嘴彻底把我点着了,“你妈蚌老肉松,好赖不分,不管出也不管进,只管咬着隔壁老王的牙签棍儿,却没在生你这畜生的时候一个使劲夹死你——哎呀,你妈个‘傻逼’!大傻逼!”
奇瑞车不吱声了,我把手里的烟头扔出去,重新把住方向盘。
“你这人瞧着人模狗样……这嘴也太脏了。”身旁的男人露出吃惊的表情,似乎被我吓着了。
“嘴脏,心干净。再说,这不是良药苦口么。主要是教育他,生死时速,人命关天呢。”笑笑,我这人没别的优点,也就天生嘴贱,还挺过瘾的。
“哟!这不是顾遥吗?你偶像?”他从座位上腾起屁股,伸手拽了一把挡风玻璃前的挂饰。
别人都在车前挂什么辟邪木、平安符,唯独我挂了一只颇显精巧的相框。相框里有张合影,我和大明星顾遥的合影。
两个男人看来十分亲密,脸贴着脸,笑得唇红齿白天造地设。
“不是偶像,是熟人。”似怕那人夺了我的相片,我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把乱晃的相框稳住,半真不假地说,“他还请我拍过戏呢,就那部《大明长歌》,就那个最后刺死太子的小脔宠常月,可我嫌剧本没劲,没接。”
《大明长歌》是两年前上映的片子,饰演常月的是个毕业于舞蹈学校的新人,就靠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一炮而红,从此星运亨通,票子赚到手软。
男人“嗤”得笑了一声,摆明不信。
“不信?我手机里还存着他经济人的号码呢,是顾遥亲手给我输进去的。”
“哟喂,还亲手,你他妈也太能扯了!”他又凑近了去看那相片,呼出一口馊哄哄的气,笑出一嘴被烟熏黄了的牙,“我最多就从这照片上看出一件事儿——你挺上镜的,不输大明星。”
我被这人的反应搞得很泄气,闭了嘴,专心开车。
雨声喧街,雨势不减,放眼望去人稀车少。唯有一些女孩子,年轻鲜嫩得像初春新透芽的枝桠儿,齐刷刷地穿着一款自印的粉色T恤,捧着花,拉着横幅,嘻嘻哈哈小跑一路,噼噼啪啪踩出一串水花。
她们胸前印着一个男人的照片,我没看清,只看见她们背后印着一句表达爱意的英文,而倾诉爱意的那个名字是Lee。
看样子都是粉丝,来给哪个大明星接机呢。
又堵一个红灯,机场总算到了。
男人没给钱就下了车,我只得跟他一起下去。他掏了掏胸前口袋,掏出一本证件似的东西,伸长胳膊,让那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窥一斑而见全豹,证件显示他是市交通局的人。
“把驾驶证拿出来!”这人瞪亮了一双铜铃眼,完全变了脸。
胆儿再肥的人也得被唬住,我大气儿不敢喘,乖乖掏出驾驶证交了上去。最近正严打,黑车司机大多不敢轻易接生客,就怕被来这么一下“微服私访”,治安拘留跑不了,还得交几万罚款。
“你叫……袁骆冰?”
打开驾驶本儿,这人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见我点头,便又拿着本子重重拍了拍我的脸,跟老子教育儿子似的教育我,“趁年轻就多读点书,干什么不好,非干违法的事儿。”
“哥,哥哎!您饶我一回……”我反应奇快,说话同时还屈膝下跪,发出噗通一声脆响。
“家里太困难,要不困难我也不能违法呀!我妈死得早,我爸又病重,两天就得用一针药,那药一针就得好几百块钱……”使劲挤了挤眼睛,成功挤出几滴泪,我越哭越入戏,一把抱住他的腿,“哥哎,哥,我真不能进去……我爸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离了我一天都活不了……”
“得得得,别动手动脚的!穷山恶水出刁民,遇见你们这样的人最没法子。”男人看似绕过了我,往我面前的地上扔了一张五十块,然后说,以后得长点眼力见,我坐你们这种车就没给过五十以上的。
我突然有点怀疑,这人跟我扯了一路淡,根本存心涮我,此刻凶相毕露半真半假,只为少付一百块车钱。
日他八辈儿祖宗,一百块都不给我。
低头去捡那张揉皱了的人民币,一滩泥水里映出一张长眉细眼的年轻脸孔——我看他一晌,觉出这眉目里深藏多年的愤、怨与苦,一经酝酿就汹涌欲出。然而这种陌生的情绪爆发未遂,他自己咂摸过来,拂一把面上疲惫,又把惯常的嬉皮笑脸找了回来。
我才抬起头,对着那人大声地喊:“谢谢亲哥!”
男人总算露出一脸“算你识相”的笑容,走之前还不忘跟我说,大明星顾遥还找你拍戏?你扯的屁我一个字都不信!
雨毫无征兆地大了,打在地上劈啪作响,好比锣齐鸣,鸦乱飞。我从地上爬起来,攥紧手里的五十块钱,浑身湿透地回到车里。
透过垂在眼前的湿发,一眼不眨地望着那张合影。
我这辈子扯过无数个屁,可今天还真没有。
我认识顾遥,还不止一面之缘。
二、那个神经病在跳舞
我认识大明星顾遥,这事情得从王雪璟那个老娘皮开始说起。
我自幼学习舞蹈,开始只为修型健体陶冶情操,哪知道我竟有点天赋,很快就触各类舞种而旁通。十三岁时我欲更上一层楼,于是拜师于一位曾经享誉海外的舞蹈家,别人都恭敬称呼她为“雪璟老师”,只有我明里喊她“贤姐”,背地里管她叫“老娘皮”。
老娘皮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王祖贤,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即使现在应已年逾四十,看上去依然如绿缎子上刺的红牡丹,美得隆重又惹眼。她一直对外头瞒着自己的真实年龄,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每当我向别人介绍起她,开篇总是“生卒不详”四字。
老娘皮性子刚烈,自恃貌美与才高,既不懂向领导献媚,也不屑与同行相偎,因此开罪不少人,日子也越过越不如意。四十岁后她被更年轻的女人挤出了舞蹈团,只得自己开办民营艺术团(其实规模极小),靠教学生跳舞赚一点脂粉钱。
当时跟我一起在老娘皮这儿学习舞蹈的孩子不少,第一次见面,老娘皮就面目凝重地问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跳舞?
为名,为利,为陶冶情操,为光耀门楣……有人答得特别梦幻,有人答得特别现实,有人答得特别崇高,有人答得特别猥琐。
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跳舞?
我说,跳舞的人柔韧性好,能干别人不能干的。
你想干什么别人不能干的?
我想给自己口。
……
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初练舞的日子,我始终认为觉得,老娘皮对我“另眼相待”就是因为这个毫无粉饰的答案遂了她心意,但也有知情的师哥师姐一早透露给我听,说我各方面都很像老娘皮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
好巧不巧,那人也姓袁。
艺术团里除我之外没第二个姓袁的,我问师哥师姐,那人后来呢?
被部队文工团挑走了。大袁觉得是个成名的机会,可雪璟老师不同意,说他性子太犟,锋芒太露,不适合在那种地方生存,又说部队里同一个岗位上人才分配往往过剩,而表演“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大袁认定是雪璟老师有意阻碍他的前程,一气之下不顾老师苦苦挽留,一意孤行地偏就走了。
再后来呢?
部队其实远比我们想的黑,大袁在里头混得不如意,也不知是不是得罪了领导,尽被人往偏远山区打发,上头规定每年必须完成的百余场演出也压得他喘不过气。估计是不忿于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无出头之日,大袁终于在农历春节前一天晚上给雪璟老师打了电话,然后卧轨死了。
我没机会见一面那个人人眼中的跳舞奇才大袁,但我愿意相信老娘皮待我严苛不为怀旧,只是惜才。那些日子她天天把我往死里操练,恨不能一天就倾其所有,而我也拼了命生吞死咽,恨不能一天就把她的浑身本事全吃进去。
老娘皮生平最得意的两支舞,一支是与德国现代舞大师合作完成的《践行柏柏尔》,还有一支是她自己编舞的成名作《醉死当涂》。
前一支舞我跳得青出于蓝,常能把观众跳哭,但后一支却百学不会。跳舞的人讲究“舞我合一”的境界,我却做不到。
我告诉老娘皮,我特别厌恶酒鬼,纵使太白有“沽酒与何人”的才情,在我眼里也只是语文课本上那个毫无雄性气质的死胖子。
那时候选秀节目不比现在多似牛毛,如果不进部队文工团,民间学舞蹈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参加两年一届的全国青年舞者电视大奖赛。我参加的那一届“青舞赛”是第十七届,决赛地点安排在广州,我头一回坐飞机,带着漱具、拖鞋、换洗的内衣裤、我爸悄悄揣我兜里的两只茶鸡蛋与一颗十八岁的灼灼雄心。
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场选拔赛,不在电视上直播,只会以花絮的形式做个剪辑回顾。
我有点人来疯的毛病,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舞台,那么多的观众,选拔赛时我跳了《践行柏柏尔》的其中一段,那支舞蹈不到七分钟,那七分钟里,我忘记了自己是贴地爬生的离离草,我乘风向上,苦尽甘来,我的血肉凝铸于舞台上,灵魂飘在万里之外。
舞罢已浑身是汗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