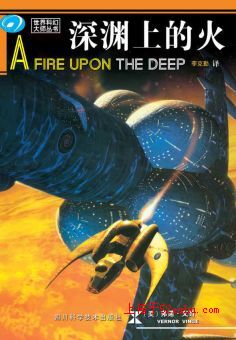尖白深渊4·暗棋作者:dnax-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各种五官图样的电脑里拼凑出来,然後再和全世界的罪犯作对比,这样就能很快抓住他了。”
彼得捏住自己的鼻子,以一种正要打喷嚏的姿势偷偷发笑。奥斯卡向他瞪了一眼,托比自信地说:“我可以描述其中一个凶手的模样,我看得很清楚。”
“好吧。”奥斯卡说,“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可以拼凑五官的电脑,你可以把你能想起来的特征告诉彼得,他比电脑好用多了。”
“是吗?”托比将信将疑地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年轻人。
“相信我,作为凶杀组的探员,我们通过彼得的画像抓住过很多人,这个月就有六起谋杀案。两个地下帮派的小混混,一个药店老板,一个货车司机,一个退役棒球队员还有一个午夜嫖客。”
托比仍然抱著怀疑态度:“可我怎麽从来没见过你们发的通缉令?”
奥斯卡仍在对付自己乱糟糟的头发,托比泄气地开始向彼得描述凶犯的模样。奥斯卡松了口气,放下手臂,从桌上的一堆文件里找出几张失踪女孩的照片。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奥斯卡看到彼得站起来和托比握了一下手,然後托比就离开了。离开之前这位先生执著地在彼得的画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目击证人:托比.肯特。
“他是不是一个罪案电视迷,或者是一个侦探小说爱好者?”
彼得没有回应奥斯卡的调侃,他出奇的沈默,看著自己的画板发呆。过了一会儿说:“你要不要调查这个案子?”
“别开玩笑了,我去看过现场,敢肯定双方都是职业杀手。如果你不信,不妨等两天,看看死者的身份会是什麽?一片空白,没有记录,没有名字,甚至有的人连指纹都没有,就像一张白纸,於是我们在这种案子的档案里随手记上一笔,杀手A,死於头部中枪。有时间调查狗咬狗的案子,不如把那些可怜的姑娘们找回来。”
“你想让我把这张通缉令贴出去吗?”
“随你的便。”
“奥斯卡,你看。”
彼得把画板转过来对著他,奥斯卡抬头看了一眼。他愣住了,疲倦一扫而空,脑袋也空了。
他在画纸上看到了最熟悉不过的人。
“你看到了什麽?”彼得明知故问。
奥斯卡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抢过那一页画纸。
“你们在搞什麽鬼?”
“我也想知道。”
“彼得,你画了什麽!”奥斯卡对他咆哮,“这是麦克,你以为我不认识他吗?”
“我当然知道,我也很惊讶,我好不容易才强作镇定地送走托比.肯特,这当然是麦克。”彼得说,“但麦克是罪犯吗?是杀手吗?他还活著吗?”
奥斯卡走回办公桌,看起来很想找个人打一架,但最後只是把那张画像扔进抽屉,上锁。
“这件事对谁也不准说,这个案子我来负责。”
“通缉令呢?”
“你疯了,他是麦克!”
奥斯卡对彼得说:“不管他犯了什麽事,都不准你发他的通缉令。”
06。游客守则
飞机降落在一条破旧肮脏的跑道上,附近的杂草中有时还能看见一两只行动迅速的小动物,驾驶者对这些隐患视若无睹习以为常,因为危险和意外正是这里的特色。
飞机在跑道上颠簸了一阵,终於停稳时,机上的乘客发出一片零零落落的掌声。麦克在座位上等他们先走。先是一对年轻夫妇,丈夫瘦弱斯文,带著点神经质的警惕,妻子有著美丽的古铜色皮肤和漆黑如丝的卷发。接著是个抱著相机的男人,头发凌乱,鼻梁上架著眼镜,穿一件蓝白色条纹衬衫,袖子卷起一半,右手上有一只皮带轻微磨损的手表。队伍最後跟著几个当地商人,两个黑人神父,一个阿拉伯人。
机舱外一片灼热的荒漠,热气对流使景色不规律地抖动。麦克脱掉外套,背上背包,跟著人群走向一辆没有窗玻璃的旧巴士。巴士上已经有一些人,但是互相并不交谈,看到有新乘客加入,他们中的几个人会抬起头,毫无表情地看上一两眼,只是因为这为数不多的一点动作才显示出他们是活人。麦克走到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年轻夫妇坐在前面,那个抱著相机的男人匆匆上车来,他的头发始终湿漉漉的,脸色发红,额头冒汗,在车门口扫视一下车厢,发现了麦克身旁的空位。
“我可以吗?”他走过来小声问。
“请便。”麦克友好地回答。
对话又引起几个人的注意,这个男人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坐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座椅上,开始摆弄相机。麦克从他的相机屏幕上看到一些战火纷飞的照片,妇女们在清理房屋的照片,一张小女孩蹲在墙角拨弄野花的照片,背後是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
“你是记者吗?”麦克看著照片问。
“不完全是。”这个人说,“我曾经是个周刊记者,後来不干了,现在我自己办了一份小报。”他抬起头看了麦克一眼,额前的头发挡住了视线,他不耐烦地用手向後梳理一下。
“我叫安迪?斯特林。”安迪从上衣口袋翻出一张名片,上面写著《9号周刊》,麦克几乎没见过这份报纸。
“我叫亚当?弗格斯,很高兴认识你。”
“你是来干嘛的?”
“我是游客。”
“唔,游客。”安迪耸了耸肩膀说,“打算先去哪?”
“你去过萨伦基尔吗?”
“当然。”安迪从相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央有一个被爆炸气浪掀到半空的人,可以预见,等他落地後将永远失去四肢中的一部分。
“这就是在萨伦基尔拍到的,这样的照片可遇不可求。我的报纸卖得不怎麽好,几乎没什麽订阅,但网站阅读量很不错。”
“这是什麽时候拍到的?”
“上个月,萨伦基尔现在不太平,如果你要去,千万别做任何出格的事,也不要让当地人认为你有可疑之处。他们对外国人都有敌意,包括孩子和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自由战士。”
尽管安迪已经尽量小声,但仍然有人向他看过来,幸好司机在这时发动了汽车,一阵巨大的噪音盖过了他的说话声,旧巴士车像一只睡醒的猛兽,剧烈地抖动著,咆哮著,慢慢往前开动。
开车後,安迪不再交谈,把相机抱在怀里靠著座椅睡觉,动荡的车厢外除了荒漠还是荒漠。热风把一些沙子吹进车窗,安迪的脑袋向後仰著,嘴巴微微张开,显得又疲惫又满足。麦克望著窗外,灼热的空气和粗糙的沙粒让他产生了一点焦虑。计划中他现在应该在威尼斯,在贡多拉船上和心爱的人一起享受浪漫和悠闲,可在萨伦基尔,“游客”的含义却绝不是友好和享受。
他从背包中取出地图和旅游指南。一张旧地图,上面有各种颜色的笔划过的痕迹,在某些空白处,可以看到前一位使用者留下的记录,例如:导游,阿扎维。接著是一串号码。或者:卡普利餐厅,预订座位。各种涂鸦。麦克仔细搜索每个角落,在市中心的某处,一支红笔以极不自信的笔调画了个箱子,标注著:萨伊德利。
麦克翻开旅游指南,那是一本极为粗糙的小册子,介绍了整个岌岌可危的戈尔维亚共和国,但越危险的地方越充满魅力,麦克甚至从最後几页中找到一家中餐馆,简介上说一对夫妇混进战火纷飞的军营为士兵们供应中餐和酒。
翻到最後一页,他感到廉价塑料薄膜下有一点突起,用指甲划开,从里面倒出一枚小硬币。这枚硬币经过了太长时间的使用,每一条刻痕都结著污垢,看起来就像一枚黑灰色的纽扣,正面有个模糊不清的数字,反面是一轮弯弯的新月。麦克把它放在手心里,阳光照得它更是肮脏不堪。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车上昏昏欲睡的人们全都惊醒了,安迪在他身边惊跳起来,眼镜从鼻梁上滑落。麦克合起手掌,把硬币塞进口袋和其他零钱混在一起,他往车窗外看,远处有一道滚滚的黑烟冒了出来,紧接著一阵枪声和几下零星的爆炸。
“又开战了,每天不打几枪,他们就浑身发痒。”安迪腾出一只手把眼镜推回去,双眼警觉地望著浓烟,隐约能够看见一些城市的轮廓,在热气升腾的荒漠上,这座城市更像海市蜃楼。
“爆炸的是什麽地方?”
“谁知道,可能是个工厂,或者集会所,或者某个政府官员的家。”安迪激动得脸颊泛红,不知道是阳光让他发烫还是远处的爆炸,他握著相机的手指开始发白,一滴汗水从手臂上滑了下去。
“希望我们到的时候枪战还没有结束。”
“你不害怕吗?”麦克问。
安迪无所谓地笑了笑。车厢恢复了平静,商人们习以为常,牧师在胸前画著十字,年轻妻子将围著丝巾的头靠在丈夫肩膀上。安迪和麦克换了个位置,抢先在窗口拍了两张照片。
一个小时後,巴士抵达了荒漠中的城市。
麦克跳下车就闻到了硝烟味,但是四周似乎很安静。孩子们围拢在熄火的巴士旁,街道在骄阳下一直往前延伸,两边是各种店铺,但没有殷勤的招呼。所有人都在遮阳棚的阴影下等待,以怀疑和警惕的目光注视他们。
安迪背上自己的行李,胸前挂著他视若珍宝的相机,他问麦克:“你想去哪?”
“随便,到处走走。”
“好吧,小心一点,我得去工作了。”他向麦克伸出手,握住,热情地上下摇摆,“回头见,这个城市很小。”
麦克和他告别,开始考虑是先去追踪器消失的地方碰碰运气,还是去杂货店取武器,最後他决定了前者。露比为他下载准确的GPS地图,虽然他们都对追踪器失去作用的地方并不抱什麽太大指望,但这至少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临走前他记住了萨伦基尔城市的主要路线,可是眼前的道路却比记忆中更复杂,一些临时搭建的简易建筑总是会突然出现拦住去路。半个多小时後,当他经过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时,忽然察觉有人在身後跟踪。他故意在一个水果铺前逗留了一会儿,仔细挑剔地选了一个苹果。遮阳棚下的女人对待他的态度完全是漠视,以眼角的余光指示他将硬币放在桌上。
身後没有可疑人,但是在泰勒之家的那次袭击使他时刻处於警惕状态,似乎露比安排的安全线路也并不那麽安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他感到露比在这件事上有些犹豫和动摇,不像以前那麽自信万无一失了。
走出市场後,道路变得更加难以分辨。这个城市的一半已经被战火烧毁,越往前走越多废墟。麦克看著那些只剩下一面墙的房子,绿色的墙壁上油漆剥落,地上全是灰尘和粉末,接著他又会发现在残垣断壁之间孤独而顽强地矗立著几间小屋。这样的情况连绵不绝,形成一大片苟延残喘的平民区。由於有人居住的房屋之间搭著遮阳棚,这条街显得十分阴暗,麦克走到一间小屋前,几只苍蝇正围著门外的野狗打转。
是这里吗?他打量这间屋子,如果艾伦最後在这里出现过,他一定会留下些什麽。
麦克推开小屋的门,苍蝇没头没脑地撞在他身上。屋子里有一股热烘烘的灰尘味,除了几张废弃的桌椅,整个房间简陋而空旷,屋顶因为几次爆炸的碎片砸出无数个破洞,阳光从千疮百孔中直射进来,在地板上形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光斑。
露比为他精确到了一间屋子,但是里面空空如也。
破旧的桌椅上覆盖著一层薄薄的灰尘,至少十多天没人使用过。墙上有几幅出自孩子之手的涂鸦,一只死老鼠在墙角散发恶臭。麦克摸著墙面上的一小块凹陷,地上堆积著掉落的墙粉。他伸手轻轻拨弄,指尖在粉末中被尖锐物刺了一下,发现了一块碎玻璃。
他再次回到小屋中间,把翻倒的椅子扶正,注意到地板上有几道白色划痕,似乎是椅子在上面反复摩擦的痕迹。这些划痕凌乱而集中,就像有个人坐在椅子上不安分地挪动。麦克仔细检查椅子,随处可见的木头椅子有些沈重,背後的横档上因为某些原因的摩擦而留下刮痕,椅背外侧还有几块褐色斑点。
麦克坐到椅子上,想象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一些人站在周围,把一个人绑在椅子上,捆绑使用的粗绳在横档上留下刮擦的痕迹,褐色斑点是手腕磨擦绑绳流下的血迹。他们从他身上搜出一些物品,把其中一件扔向对面的墙壁,也许是手机,或者别的什麽他们认为可能会引来麻烦的东西。他挣扎过,椅子的移动表示他曾在这里受到刑讯和逼供。
阳光洒在麦克身上。椅子上的人是谁,那些人又是谁?
光斑在慢慢移动,虚掩的门外传来一声轻响。他睁开眼睛,冲过去,打开门往外面的街道望了一眼。
一个人影飞快地转过街角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