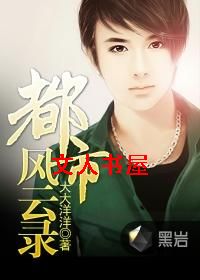附庸风雅录-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诚实唏哩呼噜地吃着,含含糊糊道:“小方你挺大方啊,以前怎么只觉拒人千里之外?是不是经此一役吸取教训,终于决定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
“哪里……师兄真的觉得我拒人千里之外?”
“怎么?不服气啊?除了打招呼,几乎不跟人主动攀谈;不论专业课还是同门聚会,有什么说什么,没一句多余寒暄;集体娱乐鲜少露面,社交活动如非必要,从不参加。去年国学院跟商学院搞联欢,一帮女生想拉你,谁不知道,叫你也白叫?——你这样的,还不是拒人千里之外?自命清高目无余子,所以关键时刻才会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方思慎苦笑:“是么?有这么惨?我倒没觉得……”
高诚实又捞起一筷子面条:“我现在才明白,你大概不是假清高,你是真迟钝,哈哈!”
高诚实本硕博连读,在这个校园待了近十年,属于京师大学的家生子。又擅交际,耳闻目睹的掌故逸事极其丰富,与方思慎的孤陋寡闻恰成对比。两人吃吃说说,不觉聊得痛快。到后来,基本是高诚实在说,方思慎在听。
听他讲“夜叉王之叱”的来历,说那“夜叉王”本是共和之后京师大学首届高材生,己巳风波前夕做到国学院院长,却因风波中受到打击发了疯。又讲与“夜叉王之叱”齐名的其余几大传说。比方“修罗王之魅”,某位院长为谋进取,如何以身饲虎牺牲色相不论性别无往不利;比方“海龙王之泣”,某位老教授凡遇各种福利机会,如何辗转校内凄切哀哭直至得偿所愿;比方“梵天王之斩”,某位知名教授为学为人极端苛刻,门下除貌美女弟子皆有考场覆灭之危……
方思慎起初听得骇笑,后来却胸中闷闷:“师兄,何至于此。”
高诚实看他不愿相信,便道:“坊间传言,未必空穴来风。过耳即逝,倒也不必当真。像你这样什么都不管,还真是福气。”
话题渐渐深入具体,终于谈及现实处境。高诚实问:“你申请换导师批下来了吗?”
“还没。”
“老寇接手你原先做的课题,听说准备跟他自己的合一块儿,拿去申报博士后。”
博三面临毕业去向抉择,文科生不好找工作,能获得博士后资格继续做研究,尤其是在京师大学这样名望实力一流的高等学府做研究,前途自是可观。
方思慎用事不关己的淡漠口吻道:“嗯,我跟他分的都是秦汉段,只不过他做官方简帛,我做民间简帛,合一块儿确实方便。”
高诚实用心捞着火腿,捞了半天,最后叹气:“我说小方,你也忒嫩了。”
方思慎起身拿了两个勺,分一个给他:“师兄教训的是。寇师兄凡有论文发表,一定把张教授名字署在前头,我从前还腹诽教授偏袒私传,故而发奋自励,现在才想明白,是自己不懂尊师重道。”
高诚实拍他肩膀:“此言有牢骚气。”
自从事件发生以来,方思慎始终没个知情人可以倾诉,忍不住便想多说几句:“上周我去教研室,发现常用的电脑被改了密码。因为教研室电脑连着扫描仪、打印机,我偷懒,总是在那儿弄,不少东西都没来得及复制。实在气不过,跑到教授家去理论,结果吵了一架。”
所谓吵架,也就是争辩几句而已。但那过程中对他人及自身的失望,令方思慎深觉沮丧。
高诚实继续拍他肩膀:“所以说偷懒迟早要吃教训的。”
方思慎哼一下:“张教授也是这句话。”
“教授从前可总说你最勤奋。”
“我现在明白了,那是嫌我笨。”方思慎悻悻道。
高诚实又大笑。
“哎,如今老寇可成了香饽饽了。据说今年国学院一共才两个博士后名额,张教授早就攥了一个在手里,我本来还存了不良企图想要染指,现在是没指望啰!”说罢,滋溜滋溜喝起汤来。
“师兄此言亦有牢骚气。”
“嘿!”
方思慎小心撇开面上厚厚一层红油,舀了几勺在碗里:“那师兄有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说不得,也只好抛下这张老脸,烧香拜佛,钻头觅缝,寻条门路则个。”忽然正色道,“愚兄近日耳闻一事,正要向贤弟求证。”
“师兄请讲。”
高诚实咽下一口汤,微微停顿,正经发问:“方笃之方院长,到底是不是你爸爸?”
方思慎喝汤喝得鼻尖上全是汗,擦了一把,才道:“师兄何以有此一问?”心想大概上次方大教授在宿舍楼前拦截自己,不小心被人认了出来。
“这么说,那就是不假啰?”高诚实狠狠敲一下饭盆边儿,“怪不得你这么沉得住气!我要有这么一爸爸——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啊!”
方思慎一时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师兄你误会了。”
高诚实却道:“你先听我说完。若非有些真凭实据,我也不会信口开河。你知道前些时候金帛工程开中期报告会,就在咱们京师国际会堂,接连开了两个周末,因为方大教授只有周末才得空。那天教授们往潇潇楼午餐,我有幸受命帮忙拿东西,正好偷听到一段对话。”
高诚实挤眉弄眼地模仿:“方教授对张教授说‘犬子顽劣愚钝,我这当父亲的实在有失训导,惭愧惭愧’。当时黄院长也在座,方大教授又冲他说什么‘犬子年幼无知,给诸位添麻烦了’,我看院长大人一脸尴尬,哼哼哈哈不知如何作答,倒是张教授不动声色,回复他‘年轻人积极上进,难免容易浮躁,出发点总是好的,吸取教训也就是了’……”
高诚实一面说,一面观察方思慎表情。竹简造假新闻炒得最热的时候,就有人拿方氏父子关系大做文章,因了当事人毫无反应,普通观众也就没当真。等所有人都忘得差不多,却被一方当事人自己挑了起来。
正如没想到方笃之会亲自到学校来找自己,方思慎更没想到他会在金帛工程的教授聚会上公开提及父子关系。同行本就是冤家,何况秉承文人相轻千古传统的学术圈。自从方笃之荣任院长,率领国立高等人文学院拼搏杀伐,大有压倒原泰山北斗京师大学国学院之势。迟钝单纯如小方童鞋,也知道双方表面和衷共济,底下暗箭冷枪不断。
上次与方笃之匆匆会面,之后再没有音讯,心里也就放下了。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突然有此举动,故意授人以柄。却莫名想到:这似乎是父子相聚近十年来,作为圈内名人的方笃之,第一次公开提起儿子。当然,此前长期低调,也是当儿子的方思慎,出于种种年少敏感好强又狭隘的心理,强烈要求,刻意为之,而当父亲的人一味迁就造成的结果。
高诚实等了半天,但听方思慎慢慢道:“我的事,一向自己做主,不用他管。”停了停,补充,“所以……没想到这次……”
望着高诚实苦笑:“师兄,真要是你,有这么一个父亲,你会像我这么傻么?”
高诚实语塞:“呃……毕竟是父子,他摆明了给你撑腰。”
“你要这么讲,我也没法反驳。总之你刚才所说的事,我此前一点不知道。其实,自从进了京师大学,我已经……三年多没回家了。”
“啊?那……”
“实话跟你说罢,我出生在芒干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共和33年,也就是‘第三次大改造’结束前一年,那年夏天,我父亲回了京城,而我是十二月生的,跟遗腹子没什么两样。”
高诚实听得呆了。
“芒干道”,那是大夏共和以来新史上一个如雷贯耳却又敏感微妙的地方。共和26年,最高元首亲自发起第三次大改造运动,即继开国初期敌对阶级改造、共和10年落后阶级改造之后,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的劳动思想改造。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中,上千万年轻人响应号召,轰轰烈烈奔赴边远地区,屯垦戍边,造林卫疆,持续十年之久。而位于东北边疆青丘白水最深处的莫尼乌拉群山,也里古涅河畔,被杳无边际原始森林覆盖的芒干道,则是一批重点改造对象落户的地方。
方思慎低声慢慢继续:“十五岁那年,养父临终前,忽然告诉我他不是我的父亲,要我到京城找一个叫做方笃之的人……”抬起头,“师兄,一个人的父母,真就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子女跟父母的关系,有时候,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依高诚实的八卦脾气,不知有多少问题想问,却终究被“芒干道”三个字所代表的一切压下去了。只喃喃道:“原来如此……对不起,我明白了。”
端着饭盆告辞的时候,高诚实万分诚恳神秘兮兮地对方思慎道:“小方,有件事,我猜你一定不知道:学籍处的‘何等师太’,据传乃咱们张春华教授多年‘红颜知己’。方笃之教授是你父亲,只怕三年前你报到头一天,他就晓得了……”
第〇〇六章
周六,方思慎照例早起,往国一高上课。
他发现自己渐渐适应了学生与老师之间有规律的角色转换,并且似乎慢慢开始渴望这种转换。站在讲台上与坐在讲台下,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相应的连带整个人气势气场也完全不一样。要知道,当你脚踏讲台背靠黑板,面向学生说话时,便不得不竭尽全力把自己武装起来。这种武装,涉及外貌形象语言动作知识学问道德品质从里到外多层次全方位,如履薄冰。也正因为如此,这份临时教职令方思慎于颓靡中振作精神,全神贯注。
他跟高诚实一锅泡面吃出感情,说了不少真心实话,还一时冲动吐露出个人隐私,第二天睡醒就后悔了。然而说出去的话覆水难收,徒留遗恨,又忍不住去想父亲在“金帛”工程教授餐会上的言行,心中混乱且郁闷。郁闷到星期三,突然想起还没备课,一头扎进图书馆,又忙着上网搜索资料做演示图,那些胡思乱想自然烟消云散。到了周六早上,收拾停当,抖擞精神,背上帆布包,架起平光镜,授课去也。
名单上“洪鑫垚”三个臃肿大字扑面而来,不由得先往教室后排看了看,果然没来。正准备从头开始点名,两个女生表情郑重地站到讲台前,小声开口:“方老师。”
“什么事?”
其中一个略加犹豫,道:“方老师,我们是来跟您说再见的。我俩瞒着爸妈选了文科,他们知道了,非要我们改理科……”
方思慎愣住了,下意识应道:“是么……”
“我们都很喜欢这门课,可是,我妈特地来学校找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俩改上实验物理。以后……再也不能听您讲《太史公书》了。”
方思慎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道:“不能和父母再商量商量吗?”
女孩们摇摇头,红着眼眶跟他道别。
方老师怅然若失,目送两个女生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只听前排的学生议论:“要不是我数学实在太烂,我爸也不许我学文。”“我也是哎。我爸就是文科生,我妈说他做了一辈子万金油,一生气就骂我没出息,走我爸的老路,唉。”小男生故作老成,摊开双手深深叹了口气。
下课铃刚响过,教务处刘老师就来了,进门先扫视一圈:“洪鑫垚又没来?”
看他转身要出去找人,方思慎忙问:“有两个学生说转理科了,跟您核实一下。”
刘老师看一眼名单:“没错,是她俩。”方思慎还想说什么,对方挥挥手:“每年到了高三最后一学期都还有临时变主意非要换文理的,没什么。”匆匆走了。
结果,直到上午的课全部结束,洪鑫垚也没露面。
方思慎作为外聘任课教师,只管考勤,并不管“抓考勤”,倒不用担责任。不过由该生这般表现,兼之上次的短暂露面印象,庶几可以想见是何等人物,接下来的分组研修和个人论文,只怕届时想手下留情亦无从留起。方思慎轻叹一口气,麻烦。
学生们正收拾东西往外走,抬头问了声:“哪位同学和洪鑫垚同学比较熟?”
梁若谷正走到讲台前,停下:“方老师,那个二世祖,花他爸钱来买毕业证的,您就别管了,浪费时间。”
几个学生撇着嘴帮腔:“就是,老师,您不知道吧?他转来才仨星期,迟到、旷课、不交作业、不做值日、还动手打人,表现特差!动不动就跟人显摆他的‘兰蒂’最新款,整个一暴发户。”
梁若谷待同学们说完,照例很有礼貌地点点头:“老师再见。”
方思慎呆在讲台上。半晌,摇摇头:后生可畏。
下午坐在宿舍翻看学生交上来的自愿分组名单和选题方向,小孩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胡扯瞎掰,颇多胡闹,亦不乏奇趣。唯独那个立志研究宫刑的叫做史同的男孩,为他吆喝呐喊的一大群,动真格的时候一个愿意搭档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