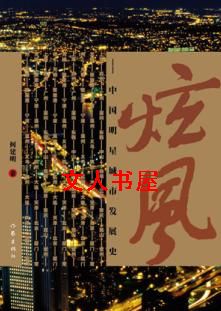飞车梦 中国磁浮列车教父 朱维衡-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什么大事。
原来,这些数字确实是一些代号。蔡明芝首先暴露了他内心羡慕的一个女孩是4483。她究竟是谁,原来是他高中时的女同学叫葛一飞。4483就是从《四角号码字典》中可查到的“葛一飞”姓氏号码。可是蔡明芝从来没有与她有任何接触,也从不敢向她表露,只是自己默默地在单相思。以此类推,同学邓伟才在“BH”中表示出对1026的好感,是说他在10月26日这天觉得化学系一位女同学外表看着很舒服,也只不过单方面发表议论,让大家讨论讨论,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同学马家驯大概是说了一句觉得同班一个叫陆昌涵的女同学不错,大家就吵着说他喜欢上她了,戏称她为“六仓汗”。这样似乎是开玩笑的活动,慢慢地也蔓延到了朱维衡的头上。可谁也不知道朱维衡还真的在爱幕一个女孩子,但只能是暗暗地思念,不能公开,也不能在“BH”上谈论,因为她正是最早表达单相思的蔡明芝的妹妹N小姐。这不能讲出来,她此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呢。
那还是在杭州读初中的时候。一天,风和日丽,放学后,蔡明芝邀几个同学一起去他家做作业。做完作业后,蔡明芝把几个同学带到了他妹妹的房间,当时朱维衡根本不知道是谁的房间。他坐在了一张书桌旁,大家正说着话,突然蔡明芝的妹妹N小姐冲了进来,到书桌上拿起一件东西就往外面跑,嘴里说了声:“讨厌!”。
朱维衡脸上一热,问蔡明芝怎么回事,蔡明芝说她拿的是她的日记本。不过一秒钟的镜头,一阵风似的旋进来又旋了出去,却好长时间没有旋出朱维衡的脑袋。那时朱维衡只有十五六岁,而N小姐才不过十二三岁。
转到了上海读书后,朱维衡也常去蔡明芝家,谈论中常提起N小姐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朱维衡没有单独与N小姐说过话,只是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多了一些牵挂。
大学一年以后,同学邓伟才考取了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再从一年级读起;同学吴退学了,蔡明芝全家迁往昆明,蔡明芝进了西南联大电机系,也是再从一年级读起。N小姐考入了西南联大经济系,留下的只有高爽秋、马家驯和朱维衡。自然也就不再有“BH”的事了。`
由于蔡明芝的关系,蔡明芝的父亲,这个精通西洋经济学的原清华大学教授蔡伯父平日里也很关注朱维衡。蔡家临行前,蔡伯父嘱托朱维衡照顾一下蔡伯父的姐姐,就是蔡明芝的大姑妈,朱维衡欣然答应。
蔡伯父和他的姐夫姚先生原来都是清华大学教授。姚家只有一个儿子叫姚威廉,清华大学学生,去了延安。姚先生去世后,大姑妈只有一个老保姆陪她住在上海女青年会。
朱维衡非常感激蔡伯父对自己的信任,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保持与远在昆明的蔡家的联系,特别是……
临行这天,朱维衡精心挑选了一件衬衫,系了一条鲜艳一点的领带,到十六铺码头为蔡明芝一家送行。
一番离别祝福之后,朱维衡拿出带来的一架蔡司相机,为自己的好朋友蔡明芝一家拍了一张全家福。
之后的日子,每隔一段时间,朱维衡就去女青年会看望一下大姑妈,帮忙办些小事情,然后再写信告诉在昆明的蔡伯父。 。。
(12)飞车梦
(12)飞车梦
大学一年级,凡是学习工程专业的同学,都要买一套计算尺和绘图仪器,市面上卖的几乎全是外国进口的,价格很高。朱维衡一天突发奇想要自己动手做计算尺卖钱。朱维衡怀着忐忑的心情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不仅没反对,反倒极力支持,给钱买了一台刨床,装在亭子间里开始试做计算尺。
同学们也很赞成朱维衡的创意,一位同学推荐了他的朋友东吴大学物理专业的樊爔培来与朱维衡合作。
樊爔培了解了朱维衡的设想方案,非常欣赏。他找来了一支高倍放大镜,装在刨床上,提高加工的精度。经过一阵试验,樊爔培还请来实验室的一位老工人,专门负责加工制作。朱维衡甚至把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叫“中国矩形公司”,还有商标设计成:长方形里边的A字上部有个C字,下部有个H字,就是CHINA(中国),突出是中国生产的。
邓伟才在大同大学时,从来不过问政治。没想到他到了上海交大,成了话剧团团长,比在大同大学时忙了许多。排演的许多剧目多是表现爱国义士的。有几次还邀同学马家驯到朱维衡家里,刻写蜡纸,油印打倒汉奸陈公博、林柏生、褚民谊的传单,然后拿到街上去散发。
可是,朱维衡的脑子里,还是总离不开那些试验,对邓伟才他们的一些说辞不太感兴趣。
这时,朱维衡的“飞车”研究正在不断扩大和完善。进一步的设想:一是继续加大功率,推动载人车辆;二是地面轻轨,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三是每隔五十米设一个加力站,这样就能成为高速飞车。设计的优点是造价低,爬坡轻松,有可能在较近的两个小山头之间在软轨上“飞行”,比人力爬山越岭省力省时,比开山打隧道要省大笔经费。
朱维衡带着自己的设想向电机系主任请教。系主任没有给予肯定和否定的意见,只是说了句:“你可以继续试!”
一天下课后,朱维衡见到学校墙报上贴出了一篇“征稿启事”是校刊《大同电机》创刊征稿。于是朱维衡就夜以继日将几年来所做的实验进行总结,附上图表、计算数据以及前景设想,撰写了一篇题为“飞车梦”的论文,结果被1940年校刊《大同电机》创刊号上第一篇发表,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誉为创刊号最具份量的创见性论文。
论文的发表和引来的赞誉,更加激励了朱维衡,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努力实践下去的决心。
大学三年级结束后。樊爔培发起办暑期学校,专门为准备进大学的学生辅导进大学的知识。他联系好一个中学做校址,请来教育界知名人士为校董,他自己任校长,邀朱维衡为副校长。大家联系自己熟悉的各大学的同班同学作教员,集合了二三十位。印发数百份传单,分发到各个学校高中部,还在《新民晚报》登了一个小广告,讲明只是帮助有志于上大学的同学了解情况,解答问题,不以盈利为目的,收取很少一点学费以付开支。没想到反应不错,居然招收到近二百名学生。一个月结束后,把剩余的学费全部拿出来,办了一个师生联欢会。
1941年秋天,学校内的各种学生组织活动日渐频繁,学生之间明显地表现出亲共产党和*产党的两种立场,双方针锋相对,都以自方是爱国行动。矛盾逐渐激烈。
朱维衡决意不卷入这场战争。
突然有一天,朱维衡收到一封匿名信,说知道朱维衡不是共产党,但已被共产党人包围了,利用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热心公益,实际是在为共产党工作。还说为了保护他,叫他当心。这分明是在警告。想到确实自己课外的活动太多。于是一气之下,朱维衡辞掉了课外活动的一切兼职,专心上课。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租界,上海这个地位特殊的“孤岛”不复存在,学校全部停课。
沦陷的上海,到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大街上不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行人惶恐不安。往日川流不息的苏州河桥头,在高悬的膏药旗下,日本兵满脸杀气。不时经过的路人若不向站岗的日本兵九十度鞠躬,立刻一个耳光。稍有反抗之意,立刻被刺刀刺死。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周日的中午,父亲朱光焘去一位朋友家吃喜酒,突然一队日本兵闯入喜宴,用刺刀将来宾分成两边,一边人无事,另一边人统统被抓走,包括那天的新郎,说是搜捕抗日分子。父亲曾在日本留学,说得一口日本话,最后还是被关了两个礼拜才放回家来。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开始复课,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可是同学们盼望中的庄严的毕业典礼、漂亮的毕业纪念册全都化为乌有。朱维衡他们充满激情充满幻想的期待,一瞬间烟消云散。 txt小说上传分享
(13)重庆来信
(13)重庆来信
毕业就是失业。朱维衡同班毕业七十五人,只有九人幸运找到工作,进了上海电力公司,其余全都要自找门路。
正在朱维衡一筹莫展的时候,失业的几个同学蕴酿生产自行车摩电灯,邀朱维衡做经理。朱维衡想,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做自行车摩电灯好歹学有所用。于是他同意加入,但不当经理。这样五个同学成立了“大同电机公司”。几个同学紧张努力,设计出不同于市面上的灯形,订做模具,找来铜皮、磁铁、矽钢片,铜线和碳刷等材料,很快做成了漂亮的摩电灯。只可惜卖不出去只好散摊。
一天,同学马家驯和高爽秋约朱维衡到他们高中时的同学杜庆萱家里串门。杜庆萱此时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赋闲在家。杜父见到一帮电机系大学生没工作,建议说,现在上海很难找到本行工作,不如想法做些人们天天需要的产品,还有可能生存。他说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做酱油的技师,你们不妨搞个酱油厂试试?同学们听后也觉得有道理,一致同意办酱油厂。
办酱油厂的资金要大家筹,朱维衡和马家驯的父亲都支持这个建议,愿出一笔钱。但是高爽秋父亲刚去世,家庭经济困难。高爽秋是一个非常诚实可靠,有实干能力的老同学,朱维衡存心帮他,但又不想再给父亲增加负担。于是想到向小姐姐朱绮开口。小姐姐朱绮最富同情心,此时的经济情况还不错。向她说明后,小姐姐立刻答应,拿出钱来作为赠款,以高爽秋的名义入股。自己不要一分回报。
六个风华正茂的电机系毕业的大学生,在南市租来的一所老房子里办起了酱油厂。
杜庆萱为总经理,他同系的大学同学田炳耕和朱维衡任副总经理,马家驯和他的一个同学为工程师,高爽秋驻厂管内务,田炳耕兼会计,朱维衡负责进货、销售,请了那位技师来做酱油。
大学生们做的是“化学酱油”,是用豆饼、盐酸、食盐饴糖,酱色加水调制而成,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酱油,不需要用黄豆发酵、太阳暴晒,因而生产期短,生产成本低。
酱油厂还取了个好名字,叫“天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叫“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想先生产酱油,以后还要生产电机呢!
不多久,南市的大街小巷里,就看见推销员推着三轮车,敲着与众不同音调的小敲琴,不时加上一句“天生酱油天生好,天生酱油呱呱叫!”的叫卖声,果然效果不错。
口号是马家驯想出来的,他还找来酱油生产的专业书籍,认真阅读,改进配方,提高酱油鲜度,降低生产成本,生意愈做愈好。
此时的朱维衡,不再是身着整齐的学生装,心中充满幻想,立志工业救国的热血青年,而是身穿油腻的工作服,为生计走街串巷疲于奔波的市井小民。
每当朱维衡往返于酱油厂的路上,在一个拐角处,隔三差五都能看见死人蜷缩在那里。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有多少同胞流离失所,贫困交加,暴尸街头,又有多少仁人智士空怀壮志,报国无门,以至颓废堕落。一想到这些,朱维衡心中充满了义愤,同时也深感作为亡国奴的无限悲哀。
1942年冬天,上海格外地寒冷。刚刚下完一场大雪,寒风吹在脸上就好像小刀在刮的一样。傍晚,朱维衡回到家里。家人已吃完了晚饭,正在客厅里听广播。朱维衡草草地吃了口饭,就到房间里去琢磨他的“计算尺”,一边计算,一边翻书查资料。
忽然,一张照片从书中滑落出来。朱维衡拿起照片专注地端详起来。那是同学蔡明芝一家离沪去昆明时,朱维衡给他们拍的全家福。给蔡家寄去了一张,自己也留下一张保存着,为了纪念,也为了……。每次拿出来看的时候,朱维衡心里总是充满了遐想。照片中亭亭玉立的少女,好像她的笑容是专门对着自己的,这笑容意味着什么?是在说什么吗?她现在怎么样了?
这些年,由于常去她大姑妈那里,关心一下大姑妈,传达两边的信息,朱维衡还想方设法与N小姐直接通上了信。不过总是只谈他们家的事,从未表达过别的意思。书信也是大姑妈收转的。然而朱维衡却十分满足。
想到这里,朱维衡站起身,他要去看望一下大姑妈。他走到后面的杂物间,取了一些堂哥不久前送过来取暖的木炭。经过客厅时,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天气预报:未来48小时,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