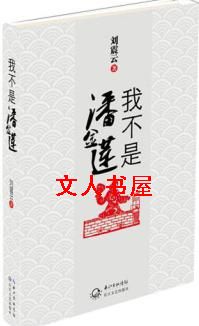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身子,这个小动作比以往频繁了许多。
在法扎巴德和哥哥家之间往返的时候,至少我还能迎着微风骑马赶路,而此刻我却和家人以及几十名其他乘客挤在一辆令人窒息的公交车里前往喀布尔,这还不算,蒙面长袍内的温度叫我无法忍受。昆都士与喀布尔之间的公路是阿富汗最危险的一段,这几年来,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如今在上面行走依然很伤神。公路狭窄,车子经过,留下一条条车辙。沿着凹凸不平的群山,车子盘了一个又一个弯,有时一侧通向碧蓝的天空,另一侧陡然向下,经过峡谷上方突出的岩石。许多不幸的人们就是在峡谷中丧命的。周围并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每当卡车或者更大的车子,比如我们的公交车,会车时,几乎是擦身而过,中间顶多剩下几厘米,轮子都要从悬崖峭壁的边缘经过。
我坐在上下跳跃、左右颠簸的座位上,听着车子的引擎在咆哮。司机用力换挡,偶尔按下喇叭,以发泄对路过的司机的不满。好在我要复习物理方程和公式,根本没心思去理会那么多。因为沉浸在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也没心思去理会汗流如注的后背,也无暇顾及笼罩在蒙面长袍之下的头发。
当热浪渐渐退去,群山开始呈现淡紫色,景色变得柔和起来。你时不时还能看到牧羊人蹲在河床边和阴凉处,看着羊群吃着肥美的牧草,驴子围着野生的罂粟花嗅了又嗅。每隔几英里,就能看到苏联坦克或卡车的残骸被丢弃在路边。
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的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入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队员持枪站在哨卡口。我们来到了米尔沙卡伊公寓所在的马克洛里安街区。这是一个苏联人修建的公寓街区,米尔沙卡伊住在五楼。
米尔沙卡伊这时已经是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协助管理警务。我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客厅里全是客人,大多数是男士,在等候他的接见。有些人是来办警务事项的,有些是给在狱中的朋友或亲戚求情的,许多人是从巴达赫尚省来拜访他的,场面还真有点混乱。
我哥哥到三楼来接我们,我一见到他,泪水就夺眶而出。喀布尔比我离开时改变了许多,我真担心这对我的家庭和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穆基姆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他的不在场印证了我最大的担心,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准备承认他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他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他去了巴基斯坦,还计划去欧洲。“什么时候?”我问。大约40天前,他们回答,但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接着我看到了客厅书架上有他的一张照片,相框上装饰了丝绸花。这是个不祥的征兆,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穆基姆的命运。
“你为什么用花装饰相框?”我问嫂子。她身子不自在地动了一下,回答道:“因为,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我思念他思念得厉害。”我知道她也在撒谎。在阿富汗,用花装饰相框是悼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人一直想保护我,但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需要的是真相。我母亲根本还不知道实情,完全相信他去了巴基斯坦。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公寓里随便看看,无意中拿起客厅摆着的几本书和照片。我看到一本日记本,不是出于对穆基姆的怀疑,而是出于无聊与好奇心。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首诗,一首透露残酷事实的诗。这首诗由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阿明所写,是一首挽歌,里面描述了穆基姆遇害的过程。我一看前三行就失声尖叫。与其说那是愤怒的狂叫还不如说是痛心的哭喊。这是穆基姆遇害的最有力的证明。母亲和哥哥冲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已经哭得情不自禁,几乎没办法说话,只能站在那里,手里朝母亲挥舞着日记本。她颤巍巍的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盯着诗歌,并不理解,但哥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无论谎言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刻,都该结束了。当母亲听到了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回荡在混凝土墙壁上,像一把钢钻,钻进我们的心。关于哥哥之死的证据无可辩驳,像一把锤子,深深地敲进我的心。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大得难以承受。全家人挤在客厅,见证穆基姆的死讯。
那一晚,悲痛将全家人再次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母亲、姐姐、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三个姨母一同放声大哭。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健康的年轻人无端地被夺去生命?这公平吗?为什么?我家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字,但或许是一个孩子学到的最重要的字。家是孩子出生的场所,是一个让他觉得安全、温暖、受保护的地方。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火箭、子弹,家应该永远保护着一个孩子。在家里,孩子可以在母亲的臂膀里睡得安稳,父亲站在一旁幸福地看着。
很遗憾的是,许多孩子,包括你们俩,没有双亲。但至少你们还有一个母亲,她爱你们,尽力弥补你们因失去父亲所失去的一切。有些孩子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呢!有多少的阿富汗孩子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没有人抚养呢!兄弟姐妹之情也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有多少兄弟姐妹连我自己都数不过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存在竞争和妒忌,尤其是在我父亲的那么多妻子中间,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孩子觉得自己缺乏爱。每一位母亲都平等地爱着所有孩子,被那么多母亲爱着,我真觉得幸福。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爷爷去世时,我母亲挑起重担,将所有的孩子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和兄弟姐妹们会打架、吵架,互相踢来踢去,用拳头打来打去,甚至互相揪头发,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相爱,也从不会对彼此漠不关心。我还跟哥哥们作斗争,为的是能够上学,能够学会独立。尽管他们并不喜欢我这样,但还是同意我这么做。当然,他们如今都为有我这个政治家妹妹而骄傲。他们也为曾经思想够开放,帮助我实现梦想而自豪。如此一来,我们保住了家族的地位,也保持了我们家的政治名声。
我多么希望能给你们生个弟弟,一个品行良好、谈吐得体的弟弟一定会非常爱你们这两个姐姐。我敢肯定你们还会和他吵架,甚至打架,但是,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他。如果真的有这么个弟弟,我会以我那已经牺牲的哥哥的名字给他命名——穆基姆。
挚爱你们的妈妈
正义何处寻?
1992年5月
先给舒拉和莎哈扎德讲个故事: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从兴都库什山脉刮来了一阵狂风,还带来了暴雨。喀布尔灰尘满地的道路很快全是泥浆,踩上去又湿又滑。露天排水沟暴涨,褐色污水四溢,形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水池。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阴影在移动。那是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里大声呼吸。雨水打湿了他的胡须,像一条小溪,顺着他的身子流下去,流进了脚踝深陷的水坑里。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突击步枪,这把苏联产的枪又重又滑,他松了松手,慢慢地前进。他故意往黑魆魆的泥沼里走,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在完全踩下去之前先用脚轻轻试探。
接着,他转身朝向6英尺高的大院围墙,轻轻地举起枪,放了上去。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件武器没拿好掉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也能传得很远。他平衡了一下身子,停了下来,双臂举过肩部,接着双手一把抓住院墙,然后像猫一样弹了上去。他把脚指头塞进砖缝,在湿漉漉的墙面寻找支撑点。由于用力控制体重,他的手臂和背部肌肉紧绷了起来。接着,他把右手肘甩到墙头,脸贴着粗糙冰冷的水泥墙面,左腿弯成弧形一甩,勾住了墙壁的边缘。等整个身体上了墙头,他轻轻地固定好位置,扫视了一下院子,看有没有警卫。见没有卫兵,他跳了进去,脚一触地,发出了一阵溅水声。他用拇指推了一下AK…47上的保险杠,做好开火的准备。
他弯下腰,借着果树的阴影朝着正房走去。院子内一片漆黑,大雨阻碍了他的视线,他就着门上铜把手一阵乱摸。随着门闩的一声刮擦,门开了。他屏住气,轻轻地打开一条缝,然后慢慢推开,眼睛朝漆黑的房间张望。房内一片寂静,因为瓦片厚,大雨的声音在房间内听起来轻了许多,但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他依旧弯腰穿过客厅,手里的枪随时准备发射。凉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在大厅里,密闭的砖墙越发反衬出其响亮。他一找到卧室的门,便停下了脚步,准备好步枪,用右手拿着,像是在握一把手枪,左手去转门把手。锁开了,门露出了一条缝。
就这样,这个男子残忍地将我哥哥谋杀了。
杀手打光了枪膛里的子弹,将正在睡觉的穆基姆射死。卡拉什尼科夫枪的弹夹可以装30颗子弹,枪手打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然后逃离现场。
我的另一个嫂子听到枪声后醒了,她和我的另一个哥哥住在另一侧的楼上。我那个哥哥想安慰妻子,对她说,枪声可能是有人朝空中开枪,用来庆祝婚礼或者庆祝赶走了苏联人的。而就在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邻居突然从院子外面大声呼喊——穆基姆被人枪杀了。
穆基姆遇害时年仅23岁。他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高大、英俊、聪明,获得过空手道黑带,在那个时代,就算在喀布尔也是很罕见的。他是我最喜欢的兄弟之一,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玩过、吵过,也打过,但彼此相爱。只要他说一句好话,我就可以笑上好几个小时;而他一句严厉的话立马会让我大哭。他、恩内亚特和我一直以来都是铁三角玩伴,还很小的时候,穆基姆就是在一名妇女的裙子底下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一回,再也没有人能够藏他、保护他了。
这真是沉痛的一击,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上的肉被割走了一部分。自从父亲死后,所有的兄长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穆基姆喜欢用他家长式的权威命令我做这做那,比如叫我洗他的袜子,要不就是洗衣服。身为小妹妹的我非常崇拜他,所以并不介意他那副家长作风,我只想得到他的赞同与关注。
大多数时候,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齐娅,我希望你能成为医生。”每每得知他对我怀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心里就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但在生气或是沮丧的时候,他就不准我第二天去学校,还会用手指着我,严厉地宣布:“明天你待在家里。你是个女孩,对女孩来说,做好家务就够了。”可见穆基姆哥哥的观点还是很传统的。不过,我还是能体谅他,因为这是他缓解压力的独特方式,在这点上他有点像我父亲。通常,在跟我说不许去学校的第二天,他回家时总会给我带礼物—— 一个新书包或者是一个新文具盒。然后他又会叫我回学校,夸我是多么聪明,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如果我的其他兄长叫我别去学校,那绝对是他们的真心话。但是,我知道,穆基姆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
无论是从他穿的衣服还是吃的食物来看,穆基姆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