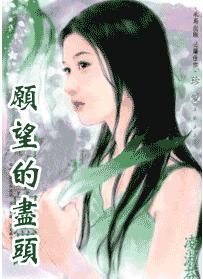大空头-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怀疑是“扮演埃斯·格林伯格的演员”的那个人没能解决他们认为自己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是小规模的私人投资者。华尔街公司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都还是个谜。“我从来没有过走在一家银行里面的实实在在的感觉,”查理说,“我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做他们想做的那种类型的交易,他们需要被华尔街大公司认为是熟知华尔街大公司路数的投资人。“作为私人投资者,你是二等公民,”加米说,“你获得的报价不好,服务不好,一切都是不好的。”
意外的资本家 金融灾难的概率
金融灾难的概率
在加米的新邻居本·霍克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如愿了。霍克特也刚满30岁的人,在东京为德意志银行做了9年的衍生品买卖交易。与加米和查理类似,他也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有些疏离的人。“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还是单身,24岁,”他说,“现在我有了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条狗。我对生意很头疼。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像一个父亲那样盼望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想,我得找机会离开这里。”当他鼓起勇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在德意志银行老板的坚持要他列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走进办公室。我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他们说'很好'。”他们告诉他,他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住在他喜欢的地方,在他想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可以在仍然是德意志银行员工的前提下做到。
本从东京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德意志银行1亿美元的资金,由他在伯克利山自己舒适的新家里进行交易。他怀疑,他或许是伯克利唯一一个在信贷衍生品中寻找套利机会的人。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心怀世界,希望购买那些金融戏剧中令人惊艳的远期期权的人,走在一条静谧的街上。本和加米相约一起去遛狗。加米引导本关注那些华尔街大公司和神秘的金融市场怎样运作的信息,并最终促使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在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子里3年之后,我认为跟别人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棒。”本说。他离开德意志银行,加入对事故和灾难的快乐追逐之中,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再次独自工作了。查理很快搬到了曼哈顿,而加米在与女朋友分手后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过去。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志同道合者的团结。本认同查理和加米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市场一样,倾向于低估极端变化出现的概率,但是他的想法又更进了一步。查理和加米只是对金融市场灾难的概率感兴趣,本却时刻在心里对现实生活中灾难出现的概率保持着一份警惕。他相信,人们也会低估这类因素,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不希望想到这些问题。在市场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趋势,因为人们应对极端事件的方式有两种:回避或者斗争。“斗争是'我要拿起我的枪杆子',”他说,“逃避是'我们都是注定要毁灭的,所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查理和加米属于逃避的类型。比如,如果他对他们说起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20英尺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或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不想再以任何方式苟且偷生。”
“他们是住在曼哈顿的两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本说,“他们两人好像都在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曼哈顿生活,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他惊奇地发现,查理和加米,这两个对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如此敏感的人,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警惕,也没有防备。“我一直试图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环境作些准备。”本说。
查理和加米希望本把他的这些“乌鸦嘴”式的说法保留在自己的心里。这些话让人听了不是滋味。比如,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知道,本在圣弗朗西斯科北部的乡间购买了一座小农场,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公路,种植了足够他的家人吃的水果和蔬菜,以备那个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来临的时之需。然而,让本把自己的世界观埋在心底是件艰难的事情,何况这与他们的投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事故和灾难的可能性距离他们的谈话永远都不会太远。有一天,在与本的通话中,查理说:“你痛恨冒任何微小的风险,但是你住在一所建在一座处于断层之上的山顶的房子里,而且是在一个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住房市场中”“他只是说,'我得走了',就挂了电话,”查理回忆道,“后来大概有两个月我们都很难找到他。”
“我挂了电话,”本说,“我意识到,我必须卖掉我的房子。马上。”他的房子值100万美元,甚至更多,然而如果出租,一个月的租金连2500美元都不到。“年租售比超过30倍,”本说,“凭经验,在年租售比为10倍的时候买入,20倍的时候卖出。”2005年10月,他把家搬到了租来的//house。ifeng。/loupan/gongyu/list_0/0。shtml
公寓里,远离断层。
在本看来,查理和加米是不太职业的理财经理,并不比半路出家的人强,或者,用他的话说,“几个在市场上打游击的聪明人”。但是,他们购买某些有望在金融市场上演大戏的廉价筹码的战略,让他产生了共鸣。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它成功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失败的可能性。有时候,期待中的大戏始终没有上演;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一次,查理在汽油期货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价格差异,并且很快买入了一份汽油合约,卖出了另外一份,用加米的话说,“一份是无铅汽油,而另外一份则是柴油”。另外一次,前提是对的,但是结论是错误的。“一天,本打电话给我说,'兄弟,我认为泰国要发生一次政变'。”加米说。报纸上没有任何泰国政变的消息,这是一次天才的抢跑。“我说,'拜托,本,你疯了,不会有什么政变的。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蹲在伯克利啊!'”本发誓,他跟一个他过去在新加坡工作时的同事聊过,这位同事的手指把着泰国的脉搏。本对此坚信不疑,他进入泰国的货币市场,买入了便宜得让人咋舌的三个月期泰铢卖出期权(卖出货币的选择权)。一周之后,泰国军方推翻了民选的总理。泰铢没有波动。“我们预言对了政变,却亏掉了钱。”加米说。
按照设计,亏损不是大问题,亏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亏损的次数比赚钱的次数多,但是他们的亏损,即期权的成本,与他们的收益比起来小得可以忽略。对他们的成功,可能的一种解释是:金融期权被系统地错误定价了。对于这个说法,查理和加米只是凭直觉,但是本曾经为华尔街的大公司做过期权定价工作,应该有足够的能力作出这个解释。市场常常低估价格极端变动的可能性,期权市场也倾向于把遥远的未来预计为会与当下的情况想似。最后,期权的价格是其基础股票、货币或者商品价格波动的函数,而期权市场倾向于根据最近的记录预测股票、货币或者商品的价格波动。在IBM股票价格达到每股34美元,并且在过去一年中疯狂波动的情况下,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在任何时候行权的期权就很少会被低估。当黄金在过去两年中以每盎司650美元的价格交易的时候,以每盎司2000美元的价格在未来的10年内的任何时候行权的期权就会被极大地低估。期权的行权期越长,由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所得出来的结果就越愚蠢,因此不采用这一模型的那些人的机会也就更大。
奇怪的是,三人当中,本这个最不传统的人反而最具有面子意识,他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外形象变得更像传统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他熟知怎么玩转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因而也知道查理和加米会被华尔街大公司看成是不十分严肃的投资者,或者,用本的话说,“车库对冲基金”,也知道他们会为此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个人投资者在公开交易中所能够得到的最长的期权是大期股票期权,即在2。5年内购买普通股票的选择权。“本对查理和加米说,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将自己打造成严肃的机构投资者,你们就可以给雷曼兄弟或者摩根士丹利打电话,并且购买任何你们想要的东西的8年期权。你们希望这样吗?”
他们当然想!他们发疯似的想直接与他们认为被低得最严重的期权来源进行交易:在高盛、德意志银行、贝尔斯登以及其他那些最成熟的大规模的交易席位。“狩猎证”,他们这样称呼它。“狩猎证”拥有一个名字: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这是由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编撰的格式协议,也就是迈克尔·巴里在买入他的第一份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时弄到手的那份东西。如果你获得了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协议,理论上你就可以与华尔街的大公司进行交易,就算不能说是棋逢对手,至少也算是初生牛犊。问题在于,尽管他们成功地管理着资金,他们所拥有的资金仍然不是太多。更严重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华尔街内部,他们被列为“高净值个人”,这是最好的说法了。有钱人。有钱人从华尔街得到的服务要好于中产阶级人士,然而与机构资产管理人相比,他们仍然是二等公民。更关键的是,有钱人一般不会被邀请去交易复杂的证券,比如信用违约掉期等不会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产品。而证券正在逐渐成为华尔街的脉动。
意外的资本家 攻克德意志银行
攻克德意志银行
到2006年年初,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自有资金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万美元,尽管如此,对于销售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华尔街公司席位来说,这还是个拿不出手的小数目。“我们给高盛打电话,”加米说,“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对我们的生意没兴趣。雷曼兄弟则嘲笑我们。面对这些坚不可摧的堡垒,你要么爬过去,要么从地下打个洞钻过去。”“J·P·摩根事实上开除了我们作为他们客户的资格,”查理说,“他们说,我们的麻烦事太多了。”他们确实麻烦!就像领零花钱的孩子老是希望被当成大人样。“我们想从德意志银行购买铂金期权,”查理说,“而他们的回答却都如出一辙,'对不起,我们不能跟您做这个交易'。”华尔街让你为管理你自己的钱付钱,而不是向华尔街的某个人付钱,让他为你管理。“没有人愿意接收我们,”加米说,“我们打了一圈电话,最少要有1亿美元,才是他们认为可信赖的人。”
到他们给瑞银集团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因此当电话另一端的人问他们有多少钱的时候,他们不作正面回答。“我们学会了转移这个话题,”加米说,“问题应该是'你做空多少',”查理回忆道,“我们说不太多。然后他们问,'你们交易的频率呢?'我们说,不太频繁。然后就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冷场。然后,'等我问问老板。'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回信。”
他们在摩根士丹利和美林以及其他地方也没有碰到什么好运气。“他们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市场材料',”查理说,“而我们会说,'嗯,我们没有那些东西'。他们会说,'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报价文件'。我们没有任何报价文件,因为这些钱不是别人的钱。所以他们说,'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的钱'。我们会说,'嗯,我们也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会说,'好吧,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履历'。”如果查理和加米与资产管理界有任何联系——比如说曾经在这个行业干过,可能会对他们的申请有帮助,但是他们也没有。“最后总是在他们这样的问话中结束:'那么,你们有什么?'”
胆大妄为。加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的3000万美元。再加上一位深谙华尔街大公司运转情况,具有悲天悯人特质的前衍生产品交易员。“加米和查理曾经为申请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资格花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基实并不知道怎么去申请,”本说,“他们甚至不知道'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的含义。”
查理永远都不会弄懂本是怎么做的,本设法说服了德意志银行,接受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进入他们的“机构投资平台”,而按照德意志银行的标准,要进入这个平台,至少需要20亿美元。本声称,其实只要找到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