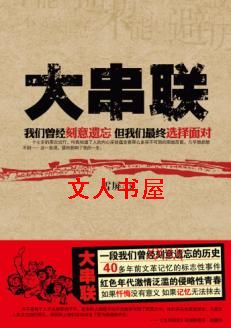暴富年代-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大学,家里不断从信用社贷款,背了一屁股债。
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为,考上大学就像是古人中了状元,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吃香的喝辣的。没曾想,欧阳成读的电子工程专业,跟经国济世做官发财一点也沾不上边。
老父亲一听说欧阳成大学毕业后,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以为是欧阳成被大上海那花花世界迷了魂,没有好好读书,才被留级回炉,直骂欧阳成是不肖子孙。老父亲写信告诉欧阳成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靠从海边往全国各地贩走私摩托车都发了财,家家都盖了新房。老父亲一再催促欧阳成赶紧完成学业,多挣点钱给家里盖栋房子,欧阳成也年纪不小该娶妻生子了。
这一切使得欧阳成心事重重。
一九八九年是个多事之秋。那年秋天显得特别萧索。没完没了的时政教育压得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三个年轻人一点也喘不过气来。
转眼到了冬天。冬天是上海最难熬的季节。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一遇到太平洋的暖湿气团,就演化成连绵不断的冬雨。
吴淞口吹来的凄冽的海风像细密的银针刺骨寒冷。
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阻挡了本来就遥远的无力冲破云层的冬日阳光。
大学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阴冷和潮湿无孔不入地渗进来,沁人肌骨,见不到阳光的日子让人从身上凉到心里,心情都是灰暗的。
寒流第二次袭击上海的时候,肖恩教授逝世了。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单身公寓的,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狂风吹烂了公寓的一块窗玻璃。
肖恩教授的死状非常痛苦,临终前一定有一番艰难的挣扎。
在为肖恩教授整理遗物的时候,何家全只发现了八千元的存款和珍藏得很好的一本日记,扉页上题着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何家全不忍心打开一代宗师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把这本日记随同肖教授的遗体一同火化了。
从龙华殡仪馆送别完教授回来,何家全一路上心里沉甸甸的。
从导师清贫的一生,何家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一个苦雨霏霏的夜晚,何家全、孙洋、欧阳成在校门口的小酒馆里喝酒。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
三个人心里都很郁闷。
由于美国冻结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孙洋的公派赴美留学的梦也暂时成了泡影。
酒后吐真言。那天晚上,三个人都掏心掏肺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焦灼和苦闷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白天在《文汇报》看到的一则广告:
广东鹿港市龙口电子厂以五十万高薪招聘主管市场营销的总经理,要求研究生学历……
五十万是足以使何家全这群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娃心惊肉跳的数字。
在大学里按部就班地做学问,搞科研,终其一生,也积累不起这么大一笔财富。
小酒馆打烊的时候,三个人集体做出决定:退学不读了,到广东打工去。
那份豪情,仿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青年痛下决心要去红色圣地延安一样。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都是系里的高才生。何家全还是江南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三个大有培养前途的硕士集体退学要去广东打工挣钱,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象牙塔里的书生们开始审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
一时间,议论纷纷。
一位老教授热泪盈眶地感叹:人心不古,坐冷板凳专心研究学问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江南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就此事给国家教委打了报告,主管此事的高教司不置可否,未做任何批复。
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退学到广东打工的申请得到了校方的批准。
历史上的广东曾是一片蛮荒之地。
连绵的南岭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阻挡了和中原文明的交流。
“岭南”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一道文化屏障。
古代触怒龙颜的一种下场便是南贬。
苏东坡南迁时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不过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我安慰,完全没有文人雅士离别江南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那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依依不舍。
俗语说:“老不入川,少不入广。”
因为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年老入川是进得去出不来的,要客死他乡。
广东则一直是不毛之地,瘴气丛生,民风淫邪,少年入广,很难全身而退。
情多累美人(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最早进行市场经济试验的地方,也是中国唯一一块与资本主义世界接壤的地方。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和“东方赌城”之称的澳门与珠江三角洲水相通,地相连。
天时、地利、人和使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保持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最快的纪录。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致决定直奔鹿港,去龙口电子厂应聘。
鹿港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久前鹿港还对贡献巨大的科技专家发放了高达一百万人民币的重奖,第一次用巨额奖金的方式隆重承认知识的价值。
鹿港市还在依山傍水的海滨斥巨资盖起了欧陆风格的“科学家村”,奖给来鹿创业的科学家每人一幢别墅。
这条消息成为国内外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也让何家全他们热血沸腾,知识分子也能发大财。
鹿港成了何家全他们心目中的新乌托邦。
海上英雄会(1)
离开学校的时候,何家全把这些年来省吃俭用攒钱购买的数百本书籍统统送给了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他要告别书本,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从上海到广东有很多条路可走:宽大的喷气式客机只需飞一个多小时,可这对囊中羞涩的穷书生来说简直太奢侈了。
火车的卧铺票异常紧张,要从票贩子手里去买,花高于正常票价好几倍的大价钱。
何家全他们三人一合计,索性乘海轮从上海到广东,再转乘汽车去鹿港,坐海轮四等舱可以省一半的钱。
一九八九年的最后一天,何家全一行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登船,开始了南下的航程。
梅舒也是同一天乘“申星”号海轮,经广州到鹿港去报到。
人到了船上,才会发现用金钱分出来的等级是如此的森严,差别是如此巨大,头等舱和二等舱占据了船上最好的位置:包厢式的格局,洁白的床单,干干净净的盥洗室……还可以一边航行,一边透过舷窗饱览大海的风光。
何家全他们乘坐的四等舱在甲板下面,整个舱是一个大通铺,横七竖八躺着的大多是南下谋生的民工,他们从家乡来到上海滩找工作,却发现这座秩序井然的大都市并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只好转赴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广东。
船舱里弥漫着浓烈的劣质烟草味,湿腻腻的汗味,和成年累月没有冲洗干净的卫生间的腥臊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强烈地刺激着人的嗅觉。
轮船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个接一个地跑到甲板上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西沉的夕阳给甲板涂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
轮船开满舵向大海驶去,长江水澎湃汹涌而来,立即汇入浩渺的东海,江海交汇处,生成了一条黄蓝分明的界线。
孙洋一眼就看到了倚着船舷远眺的梅舒。
海风轻拂起梅舒的长发,晚霞让她挺拔的背影愈加生动。
梅舒一身彩黄色的长裙微微飘起,青春的气息在海风中流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成了甲板上一个令人炫目的亮点。
梅舒眺望着东方,思绪纷飞,舟山群岛应该就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天深处。
小时候,每天这个时刻,梅舒都会挎起竹篮,和外婆一起到海边去赶海。
家里没有出海的男人,赶海拾贝成了她们一老一少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细密柔软的沙滩上映下一大一小的歪歪斜斜的两行脚印。
海水退潮了,海风越来越猛,幼小的海蟹横排成行仓皇地向大海中逃跑,可终归逃不过梅舒的追捕……
大海是慷慨的,在她的呼啸而去的时候还忘不了遗留下一些礼物。
梅舒沉浸在自己遐思的世界里。
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那美丽脱俗的容颜和飘逸动人的背影互为印证,让人为之一惊。
何家全第一次感到美的力量,并被这充盈着激情的美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太美了。”
孙洋轻轻慨叹了一声,不知是在赞赏海景,还是在夸奖梅舒。
晚上,船上的大餐厅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全船旅客将在滔滔碧波之上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缕阳光,这是一个值得十分珍视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船上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一进会场,何家全他们三双眼睛都在人群中搜寻。他们在寻找梅舒——虽然尚未知晓她的芳名。
红男绿女中,不见梅舒的踪影。当船长宣布“一九九迎新晚会”开始的时候,喧哗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安静。
随即飘来悠扬的钢琴声。
是梅舒在弹琴。
她乌黑的长发用一条白纱巾随意地扎在脑后,纤美颀长的手指在琴键上滑过。
江南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熟悉的旋律欢快地飞出来,在大厅里流淌。
随着手指的起落,梅舒韵律起伏的胸脯微微颤动,好似凝固的音乐释放出充满激情的张力。一切都是那么流畅自然。
梅舒飞扬的神采、高雅的气质让人心驰神往。
孙洋溜出了会场,回来的时候手捧着一束艳丽的鲜花,近了才发现那是一束栩栩如生的塑料绢花,花上似乎还沾着滚动的露水。
孙洋匆匆写了一张字条,让服务员把字条和花束一起给梅舒送过去。
不知孙洋在字条上写了些什么。当钢琴声换成电子音乐的时候,梅舒笑盈盈地来到了何家全、孙洋、欧阳成的桌前:
“很高兴和你们认识。我叫梅舒,松竹梅的梅,舒展的舒。”
男人在匆匆忙忙的旅途中,偶尔会邂逅让自己心驰神往的异性,仿佛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一种想与之攀谈结识的欲望搅得自己一路上心神不宁。
可怎么去接近她呢。第一句话该怎么搭讪呢。如果碰一鼻子灰岂不是很尴尬。
在这种犹犹豫豫之中,终点站到了,机会也不知不觉溜走了。
何家全很佩服孙洋的胆大和细心,在海上是很难找到鲜花的,腥咸的海风会让一切鲜活的的东西迅速枯萎。可孙洋居然能在船上找来一束塑料花用来表情达意,是他为大家创造了结识梅舒的机会。
海上英雄会(2)
以至于后来,当何家全和梅舒结为百年之好,孙洋称自己是月老红娘时,何家全也只是笑而不语。
梅舒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四个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百年修得同船渡。
人跟人能找到一个共同点都会激动不已,而梅舒与何家全、孙洋、欧阳成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上海读大学,都经过了一些曲折和风雨,落脚的地方都是广东鹿港……
海上的旅途是漫长的。刚刚登船时的好奇激动会迅速被单调重复带来的寂寞所代替。
轮船被浩瀚的海水包围着,仿佛是一叶扁舟,漂来荡去,无可依托。一天到晚,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看不到一丝生命的痕迹,在航线上偶尔遇到一艘航船也会令双方激动不已,鸣响汽笛互致问候。
经过这次海上航行,何家全理解了为什么海员总是热爱陆地而恐惧大海。
整个航程中,四个年轻人有太多的话题可以倾谈,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向往……
在梅舒的印象里:何家全言语不多,但显得稳重可靠,很有主心骨,仿佛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欧阳成则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总是静静地谛听,又似乎永远是在想自己的心事,让人捉摸不透。
唯独孙洋是最让人喜欢的旅伴,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梅舒至今还记得孙洋在船上讲的一个故事:
在巴黎最后一班地铁的一节空荡荡的车厢里,坐着一对奔波了一天疲倦至极的男女。对望之下,俩人互相攀谈起来,谁知越谈越近乎:他们都是法国人,生活得都很艰辛;俩人都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叫海伦;俩人都住在香榭里榭大街23号B座……说到最后,俩人吃惊得跳了起来,俩人今晚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原来他们是夫妻。
经过了这么多年,梅舒都记着这个故事,而且时间越长,越能让人有更多的体味,历久弥新。
孙洋说这是出法国的荒诞派戏剧。梅舒曾专门去图书馆查过也没找到出处。到现在梅舒也不敢肯定,这故事是不是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