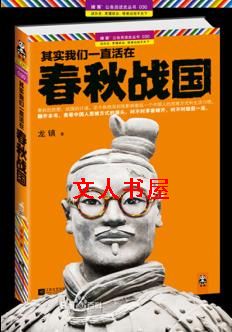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解放后强调劳动光荣,苏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与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这时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提到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对买温州船票的要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让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得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过;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们厂生产的提花丝带是通过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经常去上海,那时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队登记住旅馆,星期三办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队购船票,星期五上轮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温州。一个星期的时间,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时间倒还好,还有那种屈辱感,排队买船票已经提到过,住旅馆也是很令人气愤不平的。规定温州人只能住“国光旅馆”、“安东旅馆”等几个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低等的旅馆,这几个旅馆都在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这些旅馆所有房间的电灯开关都在门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瓯语》那章中所说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温州人就是会干坏事的,这样可以随时开灯检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书店、文具店、电脑软件店林立,解放前却叫四马路。提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四马路上的“流萤”。男人过来了,只要你东张西望,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给我们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过去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 (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